赏菊的习俗,为重阳节增加了高逸之趣。采菊、佩菊、不雅观菊等等活动都在后世重阳节俗中备受重视,乃至有了“无菊不重阳”的俗谚。图为清代陈枚《月曼清游图》之玄月重阳赏菊。
吴心怡
秋意浓,九九至,又是一年重阳节。登高望远、赏菊吟秋、饮酒食糕,这些传统习俗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文化寓意?簪菊花、佩茱萸,古人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如何又变成今人津津乐道的风尚?让我们穿越时空,一起探索重阳节的渊源,领略古人重阳行事背后的诗情画意。
重阳节的起源:由恶日到佳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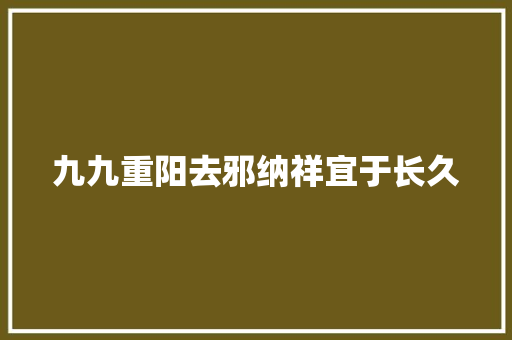
玄月九日之节的成立,与古人趋吉避凶的生理有关。
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中记载:汝南桓景追随东汉著名的羽士费长房学道,费长房曾告诫他说“玄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而应对办法也很大略,只要百口以绛囊盛放茱萸,系在臂上,登高,饮菊花酒,就可以躲避。桓景照做了,回家看到家中畜生全数倒毙。
这是玄月九日习俗起源最主要的一条记载,本日我们过重阳节,也总是少不了这个故事中的登高、茱萸、菊花这些元素。故事中,玄月九日是一个有灾的恶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桓景家中畜生的大量去世亡?无从知晓。这是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带来的灭顶之灾,从中可以感到古人面对瘟疫一类的灾害的不安与敬畏。
古人认为,奇数比较偶数更随意马虎招致灾害,形容一个人命运不好,就叫做“数奇”。比如《史记》中就记载老将李广被迷信的汉武帝认为“数奇”,不准他与单于对敌,导致难以立功。三月三日、五月五日和玄月九日一样是奇数相重的节日,也有驱邪纳祥的行事,如修禊、浴兰、躲午。九是十以内最大的奇数,在《易》学中称为“老阳”,古人相信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数字九蕴含着变动、衰落的征象。汉代谶纬之学兴盛,有“百六阳九”之说,认为逢“阳九”之年有灾异,《汉书·律历志》引《易九厄谶》:“初入元,百六阳九。”“阳九”是灾年,那么在玄月九日发生一些不可理喻的祸事也是可以想象的。桓景和费长房的传说见告人们,这些灭顶之灾可以用大略的方法化解掉,这些方法便理所应该地流传开来。
随着节日的流传,恶日的阴影淡去了。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记载了对付玄月九日之节的另一种理解:“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由于九与久谐音,大众授予了玄月九日“宜于长久”的寓意,在这天设宴欢聚,祈愿龟龄。这就让玄月九日有了佳节的色彩。史籍记载,刘宋开国天子刘裕还只是宋公的时候,北伐时途经彭城,恰逢玄月九日,就在彭城外项羽戏马台讲武、练习射箭。他称帝往后,射箭成为朝廷玄月九日主要行事,在后面几个朝代得到延续。在南朝梁的宫廷,每逢重阳节就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献寿、宴饮、骑射、集体赋诗等。到了这时,玄月九日之节早已从最初的恶日,变为国家级的佳节。
从先秦到汉魏,人们常日称这个节日为“九日”,而不是“重阳”。从屈原《远游》里“集重阳入帝宫兮”,到王粲《大暑赋》“重阳积而上升”,都是指亢盛的阳气,跟玄月九日的节日没有关系。用“重阳节”大约始于南朝。梁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明确将九日称为重阳节。古人以数字配阴阳,将一、三、五、七、九这些奇数称为阳数,二、四、六、八这些偶数称为阴数,九是最大的阳数,用“重阳”作为这个节日的美称,显示出对这个节日的喜好。
菊花与酒,重阳的最佳拍档
传说里费长房传授给桓景的重阳“三件套”——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本日看来,都属于“反抗巫术”的范畴。所谓反抗巫术,便是用明显具有反抗性子的物品或行为,追求驱邪的效果。灾害盛行于地上,那么就往相反的方向——高处往返避;茱萸的气味辛辣,可以遮去不好的气味;菊花的反抗性子,则在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中有所阐述。
在这年的玄月九日,曹丕顺手札送了一束菊花给钟繇。他说:玄月属于季秋,对应十二律吕中的“无射”,他将“无射”阐明为“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但菊花不一样,“纷然独荣”,这是“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导致的,以是它可以“辅体延年”,使人龟龄。从中可知,曹丕送给钟繇的这束菊花,紧张是当做补品来用的。
这种对付菊花的认识,见于《神农本草经》,个中说“菊服之轻身耐老”,证明在服食求仙成风的汉代,菊花是主要的药材。费长房要桓景饮菊花酒,恐怕便是利用菊花在此时节“纷然独荣”的物性来达成这个“反抗巫术”。葛洪《西京杂记》中传说汉高祖期间,戚夫人曾有一侍女贾佩兰,出宫后讲述汉宫节俗,个中玄月九日,是“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龟龄”,其行事与桓景费长房传说险些相同。
葛洪是东晋人,间隔戚夫人的时期已将近五百年,这一故事或许是晋代人的附会。但也可以证明在晋代,重阳节饮菊花酒求龟龄的风尚已经成型。这种菊花酒,不是大略的菊花泡酒,而是在酿造时就加入了菊花的花、茎、叶:“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玄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著名西晋美女文学家潘岳的《秋菊赋》切实其实是一篇菊花酒的“广告文案”,说这菊花是“真人采实在,王母接其葩”,是深受神仙钟爱的奇花;酿成的酒“泛流英于清醴,似浮萍之随波”,悦人眼目;喝下去之后,“或充虚而养气,或增妖而扬娥。既延期以永寿,又蠲疾而弭疴”——能补气、美容、延寿乃至治病。古代没有广告法,也不知道饮酒有害康健的道理,便由得潘岳写了这许多溢美之词。
说到跟菊花和酒干系的墨客,陶渊明排在第一,恐怕无人有异议。重阳节故事中最美好的一个,恰与陶渊明有关。这个故事记载在《续晋阳秋》中,说是在某一个玄月初九,陶渊明家里没有酒,只有家附近还有些菊花成长,他便来到菊花丛中,采摘盈把,在旁闲坐。忽然看见一个白衣人携酒而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给他送酒。陶渊明便就地喝了起来,直至喝醉才回去。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序中说自己在重阳节没有酒,借赏菊来排解,这一写作背景和白衣送酒的故事非常相似。
白衣送酒的故事中有三重喜:贫中无酒而得酒,是一喜;对花思酒而得酒,又是一喜;酒是他人赠予,心意恰好相通,更是一喜。陶渊明当场痛饮大醉,洒脱不羁的风姿也令人憧憬。所往后来的重阳节诗词,都很喜好引用这个典故。有些是自比白衣人,如“白衣今送酒,若个是陶家”(王勃《九日》),“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有些则因此陶渊明自比,比如李白的诗“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九日登山》),“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宅》)。杜甫晚年经历战乱,颠沛流离,诗中说“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复愁十二首其十一》),比较喜得白衣送酒,得以尽兴痛饮的陶渊明,还是那个困窘无钱,只能与菊花相对的陶渊明,更使杜甫共情。
在白衣送酒的故事里,陶渊明试图用菊花代替菊花酒来度过重九,本为一体的“菊花酒”在此分离,赏菊代替服食,为这个节日增加了高逸之趣,采菊、佩菊、不雅观菊等等活动都在后世重阳节俗中备受重视,乃至有了“无菊不重阳”的俗谚。
唐人过重阳节,有簪菊的风尚。本日留存的非遗簪花,多是女子的装饰,但在唐代,重阳簪菊是不分性别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不仅要戴,还要戴得满头都是,才算尽兴,个中蕴藏着珍惜流年的心情。白居易的诗中将这种心情写得极为恰切:“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觉惜重阳。”(《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由于重阳节有求龟龄的寓意,步入老年往后,随着年事的增长,加倍以为重阳节簪花的名贵,以是也不以为将残酷的黄菊簪在白发上有什么难为情之处了。唐人又习气把玄月旬日称作小重阳,与重阳节行事相同。李白《玄月旬日即事》说“昨日登高罢,目前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经由重阳节与小重阳,菊花被接连采摘,遭了大罪,让诗仙也不禁心生怜惜。
大词人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写于重阳,下阕“东篱把酒薄暮后,有暗香盈袖。莫道赓续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菊花不是簪在头上,而是在四周散发暗香,显出自然之美。重阳节的老例因此菊祝人寿,她这首词却写菊与人俱瘦,意境清新而冷隽。
茱萸为何成了重阳的象征
菊花与茱萸是重阳节的两大象征,菊花平日也受人咏叹,茱萸却是在重阳节外很少被提及,仿佛重阳节所专属。随着城市的发展,茱萸变得少见,以至于本日在阐明“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句家喻户晓的唐诗时,都很难说清这是一种若何的植物了。
《风土记》说“茱萸,榝也,玄月九日熟”,将茱萸等同于榝。榝是一种《离骚》中提到的植物:“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可知这栽种物气味明显,与椒近似。《风土记》中还说“茱萸到此日(玄月九日)气烈色赤,可折茱萸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本日中国常见的名为茱萸的植物,有山茱萸、吴茱萸,两者都会在秋季九十月间结出赤色成串的小果实,吴茱萸的气味更浓厚,是花椒的近亲,以是一样平常认为古人在重阳节佩戴的茱萸便是吴茱萸。曾有人持茱萸让郭璞射覆,郭璞说“子如赤铃含玄珠”,形容茱萸果实为赤色,种子为玄色,又给人以蕴藏神力的遐想。《建康记》又说“建康出茱萸”,看来六朝期间人们能在重阳节利用茱萸,也是有地理缘故原由的。
茱萸的气味刺激,并不是大家都喜好。至少屈原可能不是特殊喜好,以为樧这样一栽种物用来添补随身携带的喷鼻香囊是不得当的,以是才在《离骚》里用它来比喻近幸小人。人不喜好,便设想鬼怪也不喜好。志怪小说《异苑》记载:湘东郡的主座庾绍去世后,亲戚宗协正在喝茱萸酒,忽然瞥见庾绍就在面前,向自己讨酒喝。但是他拿到羽觞之后,没喝一口,就还了回来,说:“有茱萸气。”宗协问:“恶之耶?”他回答说:“上官皆畏之,况我乎?”可见当时认为茱萸气味极能辟邪。也正是因此,佩戴茱萸以辟邪成为玄月九日主要习俗,唐代张说《九日进茱萸山诗》其三自云重阳节进山时看到“菊酒携山客,萸囊系牧童”,这是将茱萸放入喷鼻香囊佩戴;王昌龄《九日登高》说“茱萸插鬓花宜寿”,则是将茱萸簪在头上。
茱萸和菊花一样,既可以佩戴,又可以酿酒,又都是秋季的代表性植物,从功效上说,两者一可祛邪、一可延年,恰好搭配无间,因此双双成为重阳节的象征。上官婉儿《玄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屠群臣上菊花寿酒》就用“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描述玄月九日宫廷聚会时佩茱萸、饮菊酒的场面。《梦粱录》记载宋人称茱萸“辟邪翁”,称菊“延寿客”,将两栽种物拟人化,更表示出对这两栽种物的亲切之感。茱萸对付重阳节主要而独特,因而成为重阳的象征,有时重阳节又称茱萸节。王维在长安时所作名篇《玄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以“遍插茱萸少一人”感叹重阳家人团圆而自己独在异域的寂寞。杜甫则在《九日蓝田崔氏庄》中则感叹“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借助细看茱萸,表达珍惜相聚之意。
重阳登高,不可无诗
玄月九日登高,最初是为了阔别灾害盛行的大地,但是随着重阳节变为佳节,登高望远就成了一件赏心乐事,可以登山,也可以登台、登楼。
前文已提到刘宋开国之君刘裕当年登项羽戏马台,《南齐书》记载齐武帝庆祝重阳节是在商飚馆,是依钟山而建的楼阁。李白《忆秦娥》词云“乐游原上清秋节”,长安城附近的乐游原,只是一块相对平旷的高地,却由于靠近都城,成为唐代身在长安者九日登高的首选。《荆楚岁时记》说“玄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只说是在野外,不一定是高处。大概只假如个可以游目骋怀的地方,就可以用来完成“登高”这件事,如果还能野餐,就更好了。
上古就有“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之说,重阳节登高,士人免不了吟诗作文,显露各自的才情。东晋期间充满文采风骚的“孟嘉落帽”典故,便与此有关。据《晋书》记载:孟嘉在桓温幕府担当参军时,为人温和端正,深受桓温看重。玄月九日这天,桓温率领僚属游览龙山,恰好一阵风吹落了孟嘉的帽子。士人看重外面,当众掉落帽子非常失落礼。桓温悄悄禁止其他人提醒孟嘉,期待他发觉时的反应。但孟嘉彷佛一贯没有发觉。直到孟嘉如厕久久不回,桓温才命人趁此时把他的帽子取回,又命令席间以博学有名的孙盛写一篇嘲戏孟嘉的笔墨,放在孟嘉的座位上,打算进一步不雅观察他的反应。孟嘉回来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帽子遗失落过,看到孙盛留下的笔墨,也知道众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他没有表现出尴尬,反而要来纸笔,不假思虑地写了一段回应笔墨,让在场众人都为之惊叹。不慎失落礼,上司捉弄,同寅嘲戏,在这样的窘境里,孟嘉始终镇静从容,还能用文才为自己解围,这正是魏晋期间受士人推许的“雅量”。只可惜那段奥妙的笔墨没能流传下来。孟嘉是陶渊明的外公,不知陶渊明的才华气度是否出自遗传。祖孙二人都有与玄月九日干系的风雅趣事,是个有趣的巧合。
在南朝,献诗贺九日,是登高时的常见任务。刘裕登戏马台,在场众人便纷纭作诗,个中谢灵运与谢瞻撰写的诗作被收入《文选》中。在南朝梁的宫廷重阳节诗题里,有“应令”“为某某侯作”这样的字眼,可以看出由于天子喜好文学,文武官员都要献诗,谁也逃不掉,文采不敷的人,便如《颜氏家训》所批驳的那样,“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请人代写。天监十六年,萧子显去参加九日朝宴,浩瀚臣子在席,只有他接到诏书,说“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写成之后,天子又降旨说“可谓才子”。他非常得意,将此事写在《自序》这篇自传中。看来,座中谁最有才,谁是代笔,天子心里也是有数的。
重阳登高属文赋诗的风气,在唐代大放异彩。千古名篇王勃《滕王阁序》,据《新唐书》所载,便是在一次为庆祝重阳节而组织的登高活动上写成的,宴会主人洪州都督本意是让自己的半子趁此机会显露才华,却被王勃抢先。文中有“时维玄月,序属三秋”之句,与重阳节韶光相符合。唐代每逢重阳节士大夫都有假期,可以尽情出游,登高聚会。本日的唐诗中,有不少以“九日”为题的名篇佳什,如《玄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九日齐山登高》等等,这些作品的出身,与唐代的重阳假期不无关系。
从九日饵到重阳糕
“高”与“糕”谐音,民间认为,老人体力弱,登高对付他们来说太辛劳,则可以食重阳糕作为替代。
重阳糕这一风尚大约是南北朝至隋唐期间涌现,最早盛行于民间。唐代墨客刘禹锡某次写重阳节诗,想提及重阳糕,但是遍索六经,没有“糕”字,他认为诗歌中用字不能没有出处,就放弃了。但是后人创造在《周礼疏》中郑玄已经用“今之糍糕”来阐明“糗饵粉糍”,证明东汉已有“糕”字了(《野客丛书》)。
北宋史学家宋祁由于这件事写了一首《九日食糕》诗:“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餈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家一代豪。”诗中不但引用了前述南齐宫廷在商飈馆过重阳的典故,还特意点出《周礼》中被阐明为“糕”的“糗”字,和这位几百年前称为“诗豪”的墨客开开玩笑。这首诗也证明,到了宋代,食用重阳糕已经非常普遍了。北宋崔鶠《和吕居仁九日诗》说“买糕沽酒作重阳”,不仅用了糕字,还写得很有情味,把买重阳糕当作过节的主要准备。
根据郑玄对《周礼》的阐明,“糗饵”和“糍糕”同义,以是在唐代以前,重阳糕也常称为“饵”。《玉烛宝典》载“九日食饵,其时黍、稌并收,因以黏米加味尝新”,制九日饵,会添入黍子,增加季候特色。这看起来和本日西北地区的黄米凉糕很相似。《西京杂记》中则记载了江南地区的“蓬饵”,由白蓬、米粉、白糖蒸制成,在九日这天食用,号称有御乱辟邪的功效。
九日饵因南北不同而有黄米饵、白蓬饵,重阳糕也是如此,总是就地取材,没有成规。《岁时杂记》记载东京开封的重阳糕常日由枣糕充当,也有添加栗子,乃至肉馅的。《金门岁节记》记载唐代洛阳人家重阳节食用迎凉脯、羊肝饼。前者,在高濂《高阳台·重九》词中有“糗糕菊酒迎凉脯”句,详细做法不详。羊肝饼据周作人考证便是羊羹本名,由豆沙与糖制成,颜色与羊肝附近,故名。
重阳糕有时被装饰得非常俊秀。《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重阳糕上插有彩旗装饰。俗以为五色有辟邪浸染,这种小彩旗可能不仅是为了增长都雅,也有消灾纳吉的寓意。陆游诗中说“彩猫糕上菊花黄”(《壬子九日登山小酌》),这个用黄菊装饰了的“彩猫糕”,据孟晖女士考证,可能是受佛教影响,所制糕上有狮子造型,陆游称它为“彩猫糕”,可能是爱猫的缘故。
对付明代的女性而言,重阳糕更意味着团圆,重阳节也成了女儿节。《帝京景物略》记载:“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已经出嫁的女性,在重阳节这天可以回外家吃重阳糕,与从小相伴的女性支属们相聚。未出阁的女儿,在这天也可以见到已经嫁人的姐姐、姨妈。在女子随夫而居的时期,一个女子一旦出嫁,便意味着要长期离开自己从小共同终年夜的亲人,仿佛从根拔起,重阳糕带来的这个相聚的机会非常宝贵。
“糕”与“高”谐音,偶尔也会带来别样的意味。唐代宗德宗时,给事中袁高之子名袁师德,重阳节那天,有人拿出重阳糕,他说“某不忍吃,请诸公食”,低头良久。这是由于唐人十分重视避讳,他去世的父亲以“高”为名,他这辈子就别想再吃重阳糕了,见到重阳糕还必须表示哀悼。当然,绝大多数的时候,人们借助“糕”和“高”的谐音,授予重阳糕许多美好欲望,除了遐龄,还有高升、高中,这可能是历尽千年重阳糕还受人欢迎的缘故原由。
就这样,随着传统的变迁,玄月九日从一个预示灾厄的恶日,逐渐演化为一个家庭团圆的佳节,人们在这一天搜集亲友,登高远眺,畅享秋天景色,佩茱萸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扫清疾病和邪祟,相互祝福康健与龟龄。中国文化里积极向上、敬老乐群,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特质,也将随着重阳节习俗的流传,永久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本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央、中文系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