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
从古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像陶渊明那样豁得出,事情干得不愉快说辞就辞,然后归园田居,东篱采菊,过着清贫而清闲的日子。
大千天下,有参差不齐的人,就有千姿百态的生活。
生活办法没有好坏之分,差异在于是违心而活,还是随心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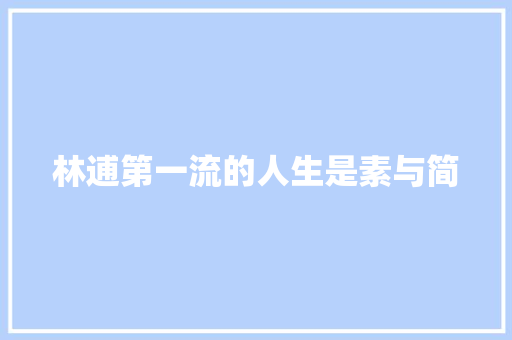
北宋的林逋是一个异数。
他屈服内心召唤,选择自己喜好的生活办法,隐居山林,梅妻鹤子,活成了一句陶渊明。
就像他在诗里自喻:
“北窗人在羲皇上,时为渊明一起予。”
脾气恬淡,隐居山泉
大概由于隐居之故,林逋的平生资料能够查到的不多。
他姓林名逋,字君复,浙江奉化人,小小年纪就沦为孤儿。
他从小发奋读书,通达经史子集、诸子百家。
学而优则仕,这是古代文人的出路。
一个读书人,既然博学多识,就应该考取功名,钻营官职,以此养家糊口。
如果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说不定能挣一番锦绣出路。
朋友劝林逋入仕做官,却被他否定。
由于,他最理解自己“恬淡好古、弗趋荣利”的心性,也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的志趣:
“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以为青山绿水与我情合适。”
他见告朋侪,我的志向不在家庭生活,我也不想追求功名富贵。
青山绿水与我相契相投,只有走进自然才会感到快乐。
时期发展至今,爱谁谁,想啥啥,生活办法已经容许多元化。
作为一千年前的古人,就明白娶妻生子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成家立业也并非唯一的道路,人该当按照自己脾气去走得当的生活办法,实在是非常独立,也非常前卫。
年轻时期的林逋,曾穷游江淮,浪迹四海。
四十岁开始,他阔别尘凡,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
鹤闲临水久,蜂
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
尝怜古图画,多数写樵渔。
这首《小隐自题》,是他描述隐居生活的简笔画。
一间茅屋,一片竹林,宁静而显清趣。
一对仙鹤在河边踱步,看起来悠然自得,一群蜜蜂闲散
林逋自己呢,他喜好饮酒,常常酒至微醺,抛下书,打个盹。
阴天,太阳不晒,那就背上锄头下地干活。
闲来欣赏古画,画上渔樵耕读的生活情态,令民气神往之。
心神往之的画境,实在也是林逋真实生活的样子。
生平未婚,梅妻鹤子
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菊以渊明为心腹,梅以和靖为心腹。”
林逋对梅花情有独钟。他在孤山开辟田地,种上三百多株梅树。
三月看花,四月卖梅,抚玩赢利两不误。
除了种梅、赏梅,林逋还画梅、写梅。
在他为梅花写下的浩瀚作品中,最有名的是《山园小梅》,这首七言律诗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薄暮。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销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一年四季,大自然百花斗艳,她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芳姿。
梅花是独特的,她不争不抢,甘守寂寞,宁肯在“众芳摇落”的冬季悄悄绽放。
在林逋眼里,梅的绝世暄妍,让白鹤、粉蝶这样的精灵感到自惭形秽,自愧不如。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薄暮”,是写梅的千古名句。
这并非林逋原创,而是化用自南唐墨客江为的句子:
“竹影横斜水清浅,桂喷鼻香浮动月薄暮。”
他发挥炼字功夫,将“竹”改为“疏”、“桂”改为“暗”,化实为虚,小小的改动,换来别样韵味。
梅花遗世独立的品质,何尝不是墨客宁静致远的高标?
林逋驯养了两只鹤,平日将它们关在笼中。
他常常乘船游览西湖,寻幽访古。如果恰逢有人登门拜访,童仆就会开笼放鹤,让它去给主人报信。
人见鹤,知客来,划船而归。
林逋生平未娶,他称自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古龙小说《欢快英雄》中,富贵山庄的庄主王动听过林和靖的故事,也爱上了梅花,他将一坛酒埋在梅树下,想沾点梅花的仙气。
郭大路打趣了一句:“把梅花当老婆已经够疯了,想不到这人居然更疯。”
红梅,花中仙品。
白鹤,鸟中仙品。
听故事的人,为故事而痴癫。
活在故事里的人,由于仙品而忘俗。
以清旷心,做云外客
人生苦短,官场险恶,很多古代文人都会萌生归隐之心。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这是苏东坡的欲望。
但他只是想想而已,始终以出世之心做着入世之事。
在任职杭州期间,苏东坡常与朋侪游览西湖,举杯饮酒。
大模糊于朝,中模糊于市,小模糊于野。
苏东坡由于来到杭州这座人间天国,他说自己是“未成小隐聊中隐”。
当他登上山顶,眺望西湖山水,难免不会想起曾经隐居于此的林逋。
林逋去世十年后,苏东坡才来到世上。
苏东坡仰慕这位随心而为的前辈,白天读他的诗,夜里就梦见了他的人。
醒来后,苏轼写下一首《书林逋诗后》,个中有这样的句子:
师长西席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
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
苏东坡认为,林逋并非属于与世隔绝之人,而是生来就有神清骨冷、超凡脱俗的气质。
梦中的林逋风神俊逸,目光炯炯有神。
而且,他还留给苏东坡一个“平生高节已难继”的印象。
林逋写诗作画随作随弃,有人建议他将诗作收拢摘录,以便留存后世。
他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
既然隐居山林,自当抛却名利,既然活着已经放下,哪里管得了身后事?
有心人将林逋所作抄录保存,我们才有幸读到他那些“澄澹高逸,如其为人”的诗作,才能借助这些诗作,欣赏那时的西湖风月。
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
这是西湖的春天。
水气并山影,苍茫已作秋。
林深喜见寺,岸静惜移舟。
这是秋日的活动。
湖水入篱山绕舍,隐居应与世相违。
闲门自掩苍苔色,来客时惊白鸟飞。
这是隐居的日常。
林逋的生活大略而丰富,种梅、养鹤、读书、品茗、饮酒、弹琴、采药、春游、乘船访僧、登高远眺、钓鱼喂猫、给远方的朋友写信……
既是梦中身,不如做个云外客,以清旷心笑傲太平,栖息山水。
十丈软红,诱惑太多,一旦迷失落自我,便会不知所向。
复苏的人,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为此作出取舍,做回自己。
孤山隐居二十多年,林逋未曾踏足城市一次。
由于他清楚,人头攒动的地方,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人生未满,由于有憾
人至晚年,林逋明白自己时日无多时,在屋子附近提前盖好宅兆,还写下一首诗: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
茂陵异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这是他对人生路的回望,也相称于墓志铭。
林逋去世后,传至朝廷,宋仁宗太息之余赐予谥号:和靖。
后世称他为和靖师长西席。
这生平,与山泉为伍,与花鸟为邻,栖息林泉,过得诗意而清闲。
按照自己的志趣,屈服内心召唤,随心而活,没有说过违心话,没有写过谄媚诗。
如此生平,是否就算圆满?
后世有盗墓者在林逋墓中创造两样物品,一只端砚、一支玉簪。
文人大多喜好砚石,这也没什么奇怪。女子佩戴的玉簪,怎会成为他随身珍藏的东西?
生平未娶的林逋,大概有一段爱而不得的故事,隐没在历史的尘凡深处?
读他留存下来的诗,让人觉得毫无尘凡气息,满是山水闲情。
实在,他还有一阙风格独特的词,字里行间,尽是款款深情: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
谁知离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
江边潮已平。
这阙《相思令》,以女性口吻写自己与爱人江边离去。
今日一别,山长水远,江水悠悠,爱恨悠悠。
林逋是在写自己,还是别人?
假若那是他自己的故事,便也是他人生的遗憾。
一支玉簪,一阙《相思令》,放在一起遐想,就很随意马虎拼接出一份鲜为人知却能理解的遗憾。
人生难免有遗憾,就像故事总会有留白。
至少,他这生平,读书弹琴,梅妻鹤子,欠妥协,不姑息,度过了美好而逍遥的旅程。
一千年后,作家张宏杰在一本书里写道:
林和靖的生命在中国人的代价坐标里是成功的,他以清寂绝尘的形象永久被历史收藏进俏丽的西湖山水,他的隐该当说隐得圆满成功。
人生未满,由于有憾。
我想,林逋不但是因隐而成功、而被书卷和山水记载,更由于他以自己喜好的办法度过了生平。
作者 | 江徐,80后女子,煮字疗饥,借笔画心
图片 | 《清平乐》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