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冬,陈亮由浙江东阳到江西上饶拜访了罢官闲居的辛弃疾,而后两人同往紫溪约见朱熹,两人等了十来天而朱熹却没有来,陈亮只得东归浙江。在这十来天里,辛弃疾与陈亮两个情投意合、意气相投之士,狂歌豪饮,纵论国事,共商规复大计,友情更加深厚。陈亮东归的越日,满怀不舍之情的辛弃疾欲追赶陈亮,再挽留他多住几天,但遇大雪景象,雪深路滑不能提高。辛弃疾心中甚是痛惜,在投宿的吴氏泉湖四望楼写下了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 - 把酒长亭说》: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骚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收拾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永夜笛,莫吹裂。
词的开篇回顾了两人在长亭饮酒话别的景象。辛弃疾推崇陈亮的品质与文采犹如陶渊明,但精彩的才干直追诸葛亮。辛弃疾陈亮皆是肚量胸襟天下的有志之士,当时两人都赋闲在家,但那不是他们主动归隐,而是政治斗争的捐躯品,他们胸中都有一颗热血的心,随时准备东山再起报效国家。而渊明表面平淡,但也是“猛志固常在”,诸葛亮更是呕心沥血为国家之人。这正是辛、陈二民气中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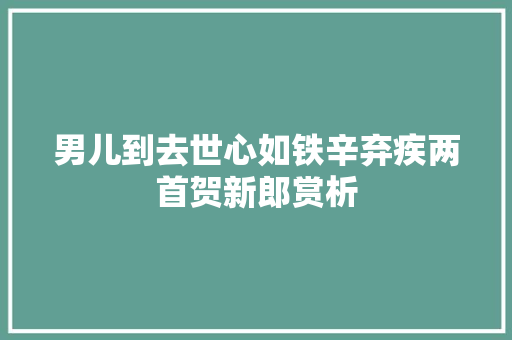
接下来几句是勾勒了一派水枯山荒,四野悲惨的冬天景致,犹如中国山水画一样写意。鹊踏松稍,枝头微雪,雪落破帽,剩水残山,几株红梅,两三飞雁,一幅水墨画面在读者心中油然而生。在这萧杀的寒冷冬日,已有几株红梅傲雪而放,为这一片肃白点缀了几点红,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点春天的希望。在这里词人表面写景,实是另有所指,这萧杀的气氛暗指南宋朝廷苟且偷安,只落得半壁江山,不但不思规复进取,反而对打击抗金志士不遗余力。“梅”指代的是能带来复兴希望的抗金志士,而“梅”已“疏”,犹如二三落单飞雁,已是难成景象,使民气生萧瑟之感。词人以景藏情,抒发着不尽的忧国情怀。
词的下片开头先是叙说离情。“佳人重约还轻别”一句赞许陈亮的践约而来,又埋怨他轻易归去。石友来见,相谈甚欢,本已快要忘怀的抗金规复之志,在这几天中升腾,而你又要溘然拜别,万丈年夜志已无人可述,留我徒呼奈何,真是相见不如不见!
随后几句写词人欲冒雪前行追回陈亮,却终因雪深泥划道路险阻而痛惜而回。由于天寒,清江冻结,行人以无法乘船渡过,积雪深厚使道路断绝,车轮像长了角似的不能迁徙改变。此时此地的行人(即词人)望着无法提高的前路,更是离愁别恨涌上心头,销魂蚀骨。继而对着不能追上的陈亮发问:“是谁让你来见我的啊?唯有带给我更深的怨愁啊!
”词人这里所写的怨愁,不仅仅是指朋友的离去之情,更是由国家的危亡形势和他们在朝廷的不平遭遇所引起的。两个即有才华也有心报效国家的人,却只能隐居山水间,空谈国事,报国无门,怎能不愁怨重生?
末了几句是词人在永夜之中的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感叹:铸就本日之大错,当初一定是费尽了人间所有的铁!
当年罗绍威为帮忙朱温击败田承嗣,花光了老底,后悔的说:“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而词人所说的错已是费尽人间铁,显然这个错更大,那不仅是朋友的离去,而是家国之错。回望六十二年前,徽宗、钦宗二帝的胆怯无能致使北宋沦亡;三十八年前,高宗秦桧召回继而冤杀岳飞,使得十年功废;二十五年前,前哨主将反面,张俊节制不力,落得符离之败。这些错才是词民气中费尽人间铁铸就的大错。而在这无尽的永夜中,英雄豪迈如辛弃疾、陈亮直流,又怎能不发出撕裂竹笛的高亢之音呢?
这首词感情浓郁,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对辛词的评论:“有脾气,有境界。即以气候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慨。”
陈亮读此词之后,以同韵和之,辛弃疾又用同韵作了一首回答陈亮,这便是《贺新郎 - 老大那堪说》: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民气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去世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满怀抗战空想的辛弃疾落笔便是直抒胸臆:“老大那堪说。”年近五十的词人,感叹光阴虚度,来日无多,却是一事无成,真是无言可说!
然而在这背后是“义士晚年,壮心不已”,以收复中原为己任的辛弃疾怎能因此而沉沦?
下面词人回述了和陈亮的交情。他以陈登(元龙)、陈遵(孟工)比作陈亮,说自己和陈亮臭味相投,感情极深。词人在病中,一见好友来访,即是高歌痛饮,匆匆膝长谈,他们的豪放之情都已惊散了楼顶的积雪。辛、陈二人都是心无俗念的仁人志士,笑众人视富贵如千钧,而在他们看来则是轻如毛发。他们议论之事、所发之言都是盘空硬语,又有几人能听懂理解他们呢?陪伴他们的只有西窗外的一轮明月。虽然夜已经很深了,哪有何妨?“重进酒,换鸣瑟”,兴致不减。当时距“隆兴制定条约”已过去二十四年,克意进取以图规复的孝宗天子对北伐也已是意兴阑珊了,在这儿辛弃疾以“只有西窗月”来比喻志同道合之人已经是寥落无几了。
词的下片紧张是抒怀,直泄胸臆。“事无两样民气别。”展望时势,面对一样的山河破碎,爱国志士咬牙切齿,而偷安者偏居一隅,醉生梦去世。词人禁不住义愤,向偏安者质问:神州大地自古山河一统,而你们却借制定条约之名默认国土沦丧,是何用心?此问正气凛然,足以使偏安者无地自容。
规复中原是必须要重用抗金人才的,而当时朝廷是嘴上每天喊着广求人才,实际上却对有志士长期压抑。正如汗血宝马在负重拉车无人理会,却在购置骏马的尸骸,喊着天下无良马,这又有什么用!
此时词人遐想到通往中原的道路已经断绝,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想起了闻鸡起舞的祖逖,炼石补天的女娲,胸中只道是“男儿到去世心如铁”,抗金收复中原的空想矢志不渝,待来日机遇成熟,也要一试技艺,以补天裂。辛弃疾在这首词的结尾处把全词的意境推向了高潮,极大的艺术传染力勃然而出。
这两首词是辛弃疾在即将进入知定命之年所写。其回望半生,纵有经略之才,规复之志,却不能为朝廷所用,反遭同寅打击,落职赋闲,寓居江南。词人将自己的不满和牢骚通盘托出,实为“稼轩不平之鸣”。但贰心中的年夜志壮志未曾消耗!
史上很多词评家都诟病稼轩词用典多且僻,这有失落偏颇。从这两首词可以看出,其用典故如糖化水中,浑然无形,毫无突兀之感。反而是意境高远、笔力苍劲、格调高扬、感情浓郁,是仁人志士发出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