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一个书家的法帖,理应理解其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家学师承、个人气质、艺术造诣及历史评价,单独就临摹而谈临摹如取无皮之毛,过于冒昧虚幻。现就张旭的《古诗四帖》,笔者针对临摹简要地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张旭,字伯高,吴郡昆隐士,初唐精彩书家。善诗词,好交友,性嗜酒。唐文宗曾将其草书、李白诗同斐旻剑并称“三绝”,其草书气势以狂、颠称雄于书史。
从风格看,《古诗四帖》极具豪放的浪漫色彩。“往时张旭善草书……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不雅观于物……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表现其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同时也将“颠狂”流露在张旭的书法运行轨迹之中。贰心存万象,思考尤丰,加之酒后兴浓,远至诸物,星辰日月,雷霆风雨;近至于诸身,思涌意起,情激性酣。时静时动,时实时虚;动则飞蛇,静若处子;又如锵锵鸣玉,落落群松,场面恢弘,字里行间透露着无限活气,令后学者击掌叫绝,心随手摹。
从节奏看,该法帖线条绵绵不断,前浪未止,后浪又袭。急则惊涛拍岸,浊世崩云;缓则渔舟晚唱,怨妇泣别。一行之间节奏时慢时急,节拍时永劫短,提按幅度很大,干净利落,左冲右突,势如破竹。迁移转变分明,转则如虫蚀木,曲尤如筋;折则角度凌厉,斩钉截铁。提笔处一样平常较快,如燕掠梁,虚幻而不浮弱,按笔处沉稳有力,节奏稍慢。淋漓畅快,落落大方。通篇之内,有实有虚,实处构造紧密,线条厚重,虚处空间疏朗,大有曲高和寡之势。后习者只有深刻理会该法帖的节奏,并能够掌握好节奏,犹如与古人舞蹈,一招一式,融入个中,方可进入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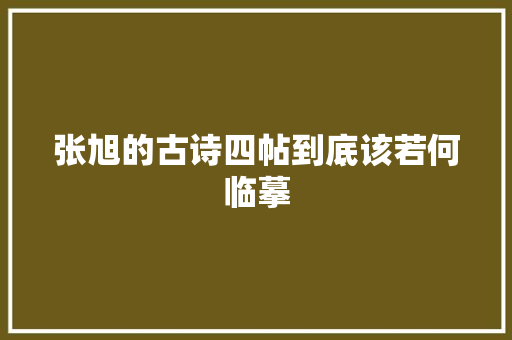
从笔法上看,张旭曾答颜真卿,“笔法得之于陆彦远,而陆彦远笔法得之其父陆柬之和褚遂良,而陆柬之得之于虞世南,虞世南又得之于智永”(方传鑫《张旭法书集》)。解释张旭笔法之源还是直承二王,只是“时出新奇”。以是临摹张旭法帖前,多临摹魏晋法帖不失落为一种好的方法。无论临摹哪一种法帖,关注起笔、运笔与收笔都是很主要的,如起笔时下笔的方向,是露锋还是藏锋?是侧锋入纸还是空中起势,顺势入纸?还是逆锋切入?入纸后也要把稳蓄力点,为后来的运笔积蓄力量,也是为节奏的启动而作蓄势准备,后面线条的运行就在这股力量的浸染下延伸,当然还少不了手的掌握。运笔的提按也不是单独的观点,是伴随着韶光的推移而完成的。《古诗四帖》中提按很强烈,抑扬有度,增强了线条的力量感与厚度,折笔有顺折有逆折,转笔弧线紧绷。张旭也谈到运笔应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实际还是强调中锋用笔,使线条厚实,入木三分。与怀素的《自叙帖》比较,怀素的线条较为空灵,提按幅度不大,通篇以提笔为主,折笔少,转笔较多,弧度较圆转流畅,以手肘的运动为主;而张旭以手腕的提按为主,摆动、迁移转变的角度较丰富,弧度较急匆匆。
以上是笔者对张旭《古诗四帖》的一些粗略理解,先从范本整体上纵不雅观其精神风格,再以行笔的节奏为切入点,领悟线条的内在气质,在探究古人用笔的根本上对作品措辞形式及技法特色的物质层面加以阐发。其情绪措辞﹙艺术作品的构成包括物质措辞与情绪内涵﹚的剖析还应该放在更加详细的历史背景与平生阅历之中。当然要真正的深入这一法帖,还要对与作者干系的成分作全面深入的稽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