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源师长西席表露的这批黄鹤楼诗文为清同治八年(1869)、同治十年(1971)越南使节两次来华途经武汉登临黄鹤楼所写诗文,辑录于越南档案馆干系史料、越南使节个人诗集及清代官员护送贡使的日记中。
诗文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汉口开埠后,东西方文化在黄鹤楼“脚下”碰撞、交融的细节。
1868年年底,越使阮思僴在《燕轺笔录》一段名为“汉阳府”的日记笔墨中记录,当时进驻汉口下街的洋商有三百余家(包括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一千多名洋人居住在当地。江岸边常日有六七艘火船停泊,各国均设有一领事馆,“通事”一职常以广东或上海人担当。清廷严禁外国使节与泰西贩子打仗,与洋商有直接打仗的当地小吏对西方贩子的评价却不差,普通市民对西方贩子的态度也开放而欢迎,这些民情与朝廷的主见、策略形成强烈比拟。
此外,阮思僴诗作中有对黄鹤楼及汉阳城周边房舍颓毁的描写,还有对“泰西屋”、穿着“北口裘”的洋贩子,及江上行驶的由蒸汽机驱动的“火轮船”等“奇不雅观”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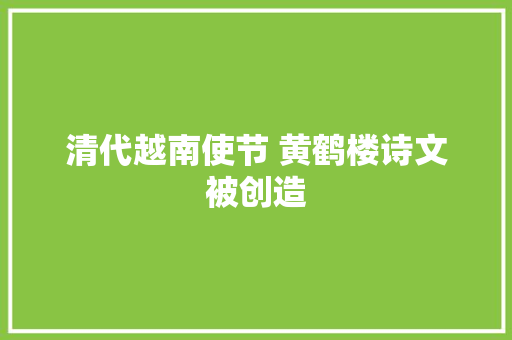
阮有立的《登黄鹤楼记》则详细描述了“北岸汉口下街洋店数百,屋两层插玻璃窗”,“火津烟火舟”、“新大街往来如织”等繁荣景象,指出这些“洋事物”为以前黄鹤楼附近所没有。
“这些西风东进的新事物,在同期中国士人所留下的黄鹤楼诗文中,险些看不到。”陈益源认为,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一定也能看到这些征象,但长久以来,以中国为天下中央的思维模式,制约了他们对这些新生事物的接管和不雅观察。
他举例说,清人刘国喷鼻香曾写过一篇《重修黄鹤楼记》,陈述重修黄鹤楼的情由,有一条是:近年来,汉口与英法德等“外夷通市”,“华言与鸟语相乱”,他国使节相继而来来朝,重修黄鹤楼可以“柔怀亦资威远”。陈益源说,大概是根深蒂固的不雅观念在作祟,当时中国人对异族,皆以戎狄视之,所谓“柔怀”和“威远”都是这种中央主义的产物。反不雅观越南使节面对这些特有景象的态度,则显得客不雅观而中性,或者好奇的身分家多。
陈益源说,这一征象值得研究,特殊是对黄鹤楼文化的进一步挖掘有着分外代价。
链接>>>
越南文学专家陈益源:我也情牵黄鹤楼
陈益源师长西席从事越南文学研究30年,近日他在电话里见告,自己曾数次来汉登临过黄鹤楼,印象深刻。女儿去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交流学习半年,对武汉和武汉的黄鹤楼也念念不忘。数年前,他在越南档案馆查阅干系史料,创造古代越南使节与黄鹤楼的分外情缘,匆匆使他开始专注这方面的研究,之后在越南和中国查阅了大量与此干系的史料和文献。
黄鹤楼是文化名楼,早已蜚声中外,凡来中国的外籍人士,都会有一睹其风采的渴望。与汉文化关系很深的越南,自元明两代起,就有青鸟使肩负岁贡等义务来到中国。他们行经黄鹤楼时,写下许多抒发个人情怀或家国愁思的诗文,记录下当时的所见所闻。陈益源说,目前他已搜集到四十余位作者所写的百余篇黄鹤楼诗文,个中最具研究代价的应是清代同治年间,越南使节临登黄鹤楼所写的这批诗文。
陈益源说,越南使团“清同治八年”的那次来华,事实上1868年底就已成行。使节从广西入境,经武汉北上。其时,黄鹤楼正在进行经历1856年大火后的重修。由于黄鹤楼正在建筑之中,无缘登楼,“甲副使”阮思僴感叹不已,写下《武昌感怀》诗。次年7月返程再次过汉时,阮思僴终于登上刚落成的黄鹤楼,写下《黄鹤楼》一文,并赋诗《偕黄云亭登黄鹤楼》。诗题中的黄云亭为使团的“乙副使”。这些诗文收录在越南藏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里。
“清同治十年”的那次访华,“正使”阮有立在完成朝贡任务后,返越途中登临黄鹤楼,写下《登黄鹤楼记》一文。这篇黄鹤楼文收录在清同治、光绪刊本的清人马先登所著《再送越南贡使日记》中。
黄鹤楼公园干系卖力人表示,这是首次创造外国使节登临古黄鹤楼所著诗文。
(蒋太旭 通讯员王红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