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戏一家”之说,仔细考虑起来,实则难以站稳脚跟。譬如,“八个样板戏”究竟涵盖哪些剧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在“十年”间,先后推出了多达17部样板戏,而所谓“八个样板戏”,仅仅是1967年推出的第一批而已。正由于“八个”无法涵盖全部,以是在详细剧目的指认上,难免会涌现各类不合。
至于“一个作家”,其本意或许是指小说家浩然,这一点看似明确无误,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又涌现了姚雪垠、张永枚、鲁迅等多种说法,乃至还有将“一个评论家”李希凡也纳入个中的情形。或许有些对“八戏一家”说情有独钟的人也会以为它所涵盖的内容过于狭隘,无法知足实际需求,于是便对它进行改造,于是在“八戏一家”说的根本上,衍生出了“八个样板戏和两部小说”、“一个作家和一个文艺评论家”、“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等各种说法。
由于“八戏一家”说本身涵义的不愿定性,它在实际利用中便成了一个可以被引用者随意改造、各取所需的躯壳。
1957年春,宣告结束大规模的封禁,戏曲剧目因此得以大胆开放。同年5月,《发出通令禁演戏曲节目全部解禁》的通令发布,这次的解禁确实起到了开放剧本、繁荣戏院的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批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戏曲作品也再次浮出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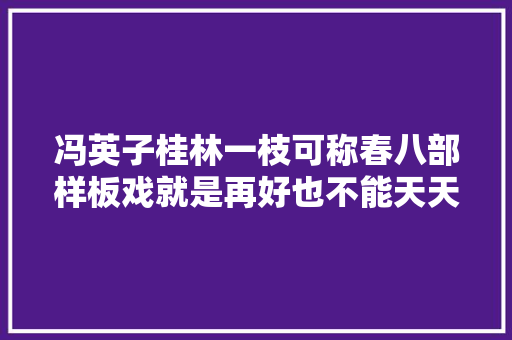
在6月13日至7月14日文化部召开的“戏曲表现当代生活漫谈会”中,提出了“以当代剧目为纲”的口号,戏曲界犹如工业、农业及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也掀起了“戏曲大跃进”运动,推动了当代戏的创作和编演的热潮。京剧名家李少春率先将歌剧《白毛女》移植为京剧,成为建国以来首次用京剧的艺术形式展现当代生活的考试测验,而这出戏仅用了半个月就搬上了舞台。
据史料记载,“上海公民沪剧团在两个月内编出了32个当代戏,南京市越剧团全团63人,从团长到炊事员大家动手,半年内创作了289个当代戏,改编了121个当代戏,等等。”
此时的戏曲界在创作数量上已经呈现出了浮夸风,创作目的也趋于功利化。针对之前戏曲改革中涌现的“粗暴”与“守旧”问题,戏曲界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谈论,并指出了“优先发展当代戏,并不偏废传统戏”的导向。
“样板戏”终极选择京剧作为其艺术形式,这紧张归功于京剧的民间性与大众性使其拥有了广泛的受众根本。与在士大夫阶层盛行、过于雅化的昆曲比较,京剧既能饰演皇权贵族、大家闺秀,又能饰演穷酸门第、落魄诗人;在行当中既能展现性情端庄的青衣,又能表现活泼俏皮的花旦;在衣饰中既有展现身份崇高的黄蟒,还有具有讽刺意味、穷酸气质的“富贵衣”。
因此,它虽源于民间,却又能直通庙堂,不同阶层的受众都能从京剧中找到代表本阶级的形式象征,这使京剧具有高度和谐的雅俗共赏性。在形成过程中,京剧的措辞汲取了当时的主流戏偏言话——中州音韵的传统,徽班进京后又受北京方言的影响,因此语音理解阻力较小。
同时,不同于昆曲的节奏延缓、缠绵婉转与秦腔一向的高亢冲动大方、粗犷豪放,京剧的风格特点介于两者之间,实现了中和,因此更随意马虎贯通南北。对付地方戏曲而言,地域文化既使它们独具特色,同时又限定了它们进一步“开疆扩土”。与诗词歌赋、小说等文艺形态比较,戏剧在现场性与传染性上更具上风,不雅观众欣赏时受文学水平的限定较小,意识形态在通报过程中具有吹糠见米之效,更具大众性。
于是,京剧便成了“中国本土受众面最普泛的、影响力最大的艺术,超越了社会阶层的限定,险些妇孺皆知。”终极,京剧自身的审美代价、成熟的艺术形式与受众根本使其成了“样板戏”承载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紧张艺术形式。
八部样板戏中,《沙家浜》的前身是《芦荡火种》,因此地下交通员阿庆嫂为核心展开的故事。其情节环绕着地下斗争的内在逻辑和戏剧性进行演进。然而,由于它未能符合毛泽东关于地下斗争应为武装斗争做事的思想,因此在修正过程中,必须突出武装斗争的元素。
这就意味着须要加入大量代表武装斗争的郭建光的戏份,并强行将他塑造成“一号人物”。但郭建光这个角色本身并没有太多故事可挖掘,于是只能通过增加他的唱腔和武打场面来凑戏。此外,为了表现军民之间的深厚情意,还生硬地插入了一场军民互助的戏。这些新增的内容并非原剧情内在逻辑所必需,也不具备戏剧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剧情的生动性和完全性。类似的环境在其他剧本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戏剧中,情节的演进紧张依赖于内在的戏剧冲突来推动。情节最基本的哀求是通情达理,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我们说“十年”期间的戏剧情节不合逻辑,紧张是指它为了图解政治,塑造“高、大、全”的形象,从而违背了基本的生活真实,造成了戏剧冲突的虚假性。比较范例的例子是《海港》和《龙江颂》。原来,如果只写公民内部抵牾,这两个根据生活原型提炼出来的故事还具有一定的完全性和真实性,只管抵牾的办理办法比较左倾。
但在修正过程中,为了表现“千万不要忘却斗争”的精确性,两剧都在原剧情的根本上增加并突出了阶级仇敌暗中毁坏这条表现敌我抵牾的线索。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实政治。虽然表面上看,戏剧的抵牾冲突彷佛更繁芜尖锐了,该当更有戏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虚假的戏剧冲突不仅扭曲了生活的真实,也使剧情的发展显得牵强无力。
比较之下,同样包含这两条抵牾线索的《杜鹃山》,由于表现的是大革命失落败往后,中国革命重新从低谷走向高潮的大背景,因此敌我抵牾线的存在具有相称的真实性,也自然地给该剧带来了应有的戏剧性。
在从个人创作转向集体创作的过程中,剧中人物因非人格化而失落去了真实性。在歌剧中,喜儿的革命性是在一系列的遭遇后方才逐渐觉醒的,但在舞剧中,喜儿的形象却始终如一,没有性情上的发展和革命性的觉悟——她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
不仅人物如此,情节安排上也同样经历了非真实化的处理。歌剧的开场设在杨白劳家,从喜儿盼爹躲债回家过年开始娓娓道来,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推进达到高潮;而舞剧则增加了一个序幕,以一曲冲动大方的合唱控诉地主汉奸对农人的奴役和剥削,表达了农人的满腔仇恨和要奋起反抗的决心。这种处理办法人为地在开场就掀起了高潮,试图引发不雅观众的情绪共鸣。
显然,歌剧的开场更方向于“个人意志”,按照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路径展开一个完全的叙事;而舞剧开场则凸显了“集体意志”,不看重故事的完全性,而是追求故事的震荡效果,通过持续的感情飞腾来达到强烈的情绪共鸣,从而勾引不雅观众将自己代入到故事情节中去,固化这种反抗性的精神。
以“集体创作”取代个人署名,本色上因此“集体”的创作模式消去作品中个人的、真实的元素。一个人格化的作者,其个人性的元素会不可避免地在极其隐私而细微的人物生理活动和行为描写中表示出来。但样板戏不许可个中的人物指向现实天下中任何一个实存之人,因此人物和作者都不能以真实而详细的人来界定。
正如1966年的部队文艺事情漫谈会纪要上所说:“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去世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实在,活着的英雄要比去世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须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范例人物来。”
然而,这种集中概括而得的“范例”已然失落去了真实性。舞剧《白毛女》完备抹煞了喜儿性情发展变革的真实部分,又以不完全的叙事构造消解了情节的真实性;《智取威虎山》则消解了《林海雪原》的传记性,抹去了少剑波与白茹间男女之情的萌动。这便是捐躯了真实性的非作者性所带来的后果。
前期的京剧“样板戏”在唱腔设计上,已经明确根据人物的思想性情和剧情发展的表现脉络,故意识地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总体布局。在唱腔布局中,确立了既统一又多样的唱段组合,积极完成唱腔塑造人物任务的理念,这在《红灯记》中表示得尤为明显。
如《红灯记》中的紧张人物李玉和,是一个成熟的地下事情者。环绕着他的唱腔总体设计,因此多侧面展现他的精良革命品质为根本的。他开始的唱段“穷汉的孩子早当家”,表示的是他对铁梅这个革命后代的舐犊之情;与磨刀人对唱的“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表达的则是他对饱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同胞悲惨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由此激发起的革命斗志;他送别交通员时唱的“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展现了他对革命同道的朴拙关爱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当他接到鸠山的“赴宴约请”,告别李奶奶和铁梅所唱的“浑身是胆雄赳赳”,显示了他临危不惧的神色和机警、沉着的斗争履历,以及对亲人炽热的拳拳亲情;在鸠山宴席上他唱的“从容对敌巍然如山”,表明了他的沉稳镇静,并已对仇敌的阴谋和严厉的斗争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而他在刑场上所唱“年夜志壮志冲云天”和对李奶奶唱的“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更是综合展示了这位受尽严刑之后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前景的热切展望和武断的胜利信念,以及面对去世亡舍身殉难、大义凛然的钢铁意志;从与李奶奶和铁梅的诀别中,在表达与她们无比深厚的感情的同时,也坚信革命奇迹后继有人。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唱段多侧面的刻画,使得一个对仇敌充满民族恨,对亲人和公民满含阶级情,年夜胆、机警且革命意志倔强如钢的共产党员形象,活生生地凸现在不雅观众的面前。
自1990年代以来,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随之而来的思想不雅观念的深刻转变,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关于文学的想象与研究视野。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和文学不雅观念的改造,更为新的研究路径的形成供应了无限可能。
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和新型研究范式的积极引进,“样板戏”研究展现出了超越传统“代价”评判的多元共生研究格局。这一多元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后期西方文化理论的“东渐”,它不仅表示在研究视野的显著延展,更表示在理论“工具”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的日益宽容、新型理论工具的获取,以及人们对文学理解视野的深刻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样板戏”研究的“繁荣”。
“样板戏”的创作逐渐倾向于政治性,而忽略了艺术性。只管第二批“样板戏”在艺术造诣上有所发展,但不雅观众的激情亲切却已逐渐消退。这一征象实际上反响了“十年”期间文学生产难以为继的内在危急。在“十年”结束前,仍处于试验修正阶段的京剧“样板戏”包括《红云岗》(山东省京剧团演出)、《审椅子》(上海京剧团演出)、《战海浪》(上海京剧团演出)、《津江渡》(上海京剧团演出)、《草原兄妹》(中国京剧团演出)、《夜渡》(中国京剧团演出),以及舞剧《杜鹃山》(中国舞剧团演出),合计七部。
这些作品仍在打磨完善之中。然而,随着“十年”后期“地下文学”与手抄本的盛行,“样板戏”的新鲜感与吸引力逐渐受到了寻衅。在“十年”即将结束时,还有一批“样板戏”正处于创作与定型之中。第三批操持中的“样板戏”包括京剧《破碎》《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警钟长鸣》,歌剧《抗寒的种子》,话剧《樟树泉》。
然而,这一批“样板戏”还仅处于操持之中,“四人帮”的方案目的正好是要挽救“样板戏”业已造成的百花凋零、一枝独秀的残局。遗憾的是,它们并未成熟,还未得到旗手的“钦准”便因“四人帮”的垮台而胎去世腹中。文艺评论家冯英子也说:一枝独秀可称春?八部样板戏便是再好,也不能每天看呀!
“样板戏”的版本变迁经历了一个极为繁芜的过程。通过比较其差异,我们可以评判其得失落,以及背后的政治与美学依据。《“样板戏”的版本与改编》一书紧张聚焦于《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赤色娘子军》《白毛女》《杜鹃山》《龙江颂》《海港》《平原作战》这十个最主要的文本。这些作品经由了精益求精,那么详细是如何修正的呢?通过深入稽核每一个版本的修正过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揭示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繁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