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皎然,清辉泻地,走不尽的山川旧路,写不完的笔底烟云,都如心中的旧时家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高下五千年,得道高僧很多,但能够将佛法与诗词融为一炉自成一家的,也屈指可数。僧皎然便是其一,他是谢灵运的第十世孙,也是唐代文名最高的僧人,在世韶光为730-799,字清昼,湖州人。
皎然喜好与同时期的文人雅士交往,还与灵澈、陆羽等修道吴兴杼山妙喜寺。他的诗以山水、宗教为紧张题材,还有些描写边塞和男女恋情的作品。论诗《诗式》在古典诗论中颇具影响。
《寻陆鸿渐不遇》,很能表示贰心志的诗。“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宣布山中去,归来逐日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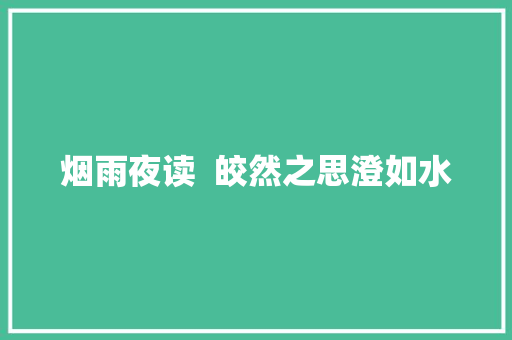
探友不遇,古时极为平凡。当时的人们,随心去留,日子本来就过得很慢,再说也没有手机网络之类束缚,寻访不遇也就非常普遍,由此也催生了无数名篇佳作,“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即为此例。
这首诗写出了隐士闲适寂静的境界。陆鸿渐便是茶圣陆羽,此人终生不仕,品性高洁。在一个萧瑟的秋日,微风带来凉意,皎然走在去寻访陆羽的路上。
陆羽的新居离城不远,却处处透着宁静,只能沿着野外的小路,穿过桑麻才能见到。篱边有菊,枝叶繁盛,但不知何因还未著花。轻叩柴扉,无人应答,连犬吠声都没有,问其西邻,说去山中了,可能薄暮才回。
诗如白描,清新如画,恍若一脉澄澈的山泉,就那么缓缓得穿过山涧,任山风摇荡,日影西斜,自是只向前路,未曾少焉消歇。有人评价说:“此诗之萧洒出尘,有在章句外者,非务为高调也。”
这首诗刻画的人物形象,也是皎然自己的人生写照,一如魏晋人物,风骚自然,胸有丘壑。
皎然清远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从未萦怀。生平爱好山林,志同道合者,方才与其定交。他著有《儒释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四十卷,《号呶子》十卷,一时纸贵。
对付笔墨与佛法,皎然曾有过一段分外的心途经程。
德宗贞元初,皎然居于东溪草堂,决心摒弃诗道,专心禅理,他认为:“假使有孔子的博识,胥臣的多闻,整天只把稳面前的事,矜道侈义,那也只能足以扰乱我的真性。这怎么能比得上孤松片云,禅座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同呢?我打算到杼山去,与青松白云为伍。”
于是,他把所著的《诗式》及一些诗文篇札,都封存起来,对笔砚说:“我疲尔役,尔困我愚,数十年间,了无所得。何况你是外物,为什么累于人呢?我既无心,去亦无我,我将放你各物化性,使物自物,与我无关,这不是很快乐的事吗?”
说完,皎然就命弟子废弃笔砚,打点行囊,前往杼山隐居。贞无五年五月,前御使中丞李洪自河北遭贬,谪为湖州太宗,特来拜访。初相见时,两人一言未发,恍如神合。皎然知道李洪精于佛理,就屈节向他求教。李洪逐一作答。
有一天,他们谈到《诗式》,皎然把自己的宿志跟李洪说了。李洪听了不以为然:“你的想法并不对。”
李洪坚持让皎然命弟子找出《诗式》一书的稿本。细读一遍往后,他感叹地说:“从前曾经读进沈约的《品藻》、慧休的《翰林》、庾信的《诗箴》,这三个人论诗的见地,都无法跟此书比较。皎然大师,你为什么受小乘偏见的约束,以宿志为辞,埋没了这部好书呢?”
李洪不由分辨,把《诗式》稿本带走,《诗式》一书得以流传天下。
皎然的困惑,并非无因。佛法修心,自不可沉溺于世间万物,以防心性蒙尘,为物所役。
然而,笔墨不同,她所记述的正好是此刻的心中所想,不过因此笔墨的形式,流传古今。最高明的佛法一定是不著笔墨的,但觉悟世间,绝大多数有情,依然须要笔墨和措辞点拨。
皎然之思澄如水。统统都如薪尽火传,尽的是物,是外在的表象,传的是道,是内心的彻悟。
皎然去世后,元和四年,大守范传正、会稽释灵澈同过皎然旧院,瞻仰遗容,悲悼良久,题诗道:“道安已返无何乡,慧远来过旧草堂。余亦当时及门客,共吟佳句一焚喷鼻香。”
斯人已逝,物是人非。只有当时的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依然穿堂入户,照在喷鼻香炉中袅袅的轻烟上,当时吟唱的佳句,也在不知不觉间,早已穿越了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