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99年,德国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带来了奥地利作曲家马勒1908年的作品—《大地之歌》。
《大地之歌》分为六个章节,用女中音 (或男中音)、男高音演唱加上乐队演奏。个中,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据马勒自己说,《大地之歌》六个章节的歌词,是由六首中国唐代的诗歌翻译而来。
一个奥地利人,对唐诗的认知能有多深呢?于是,很多喜好唐诗,乃至专门研究唐诗的爱好者和学者,跑去欣赏《大地之歌》。
然而,听完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场的很多人,一脸茫然,完备无法分辨出,这六首歌所表现的到底是哪六首唐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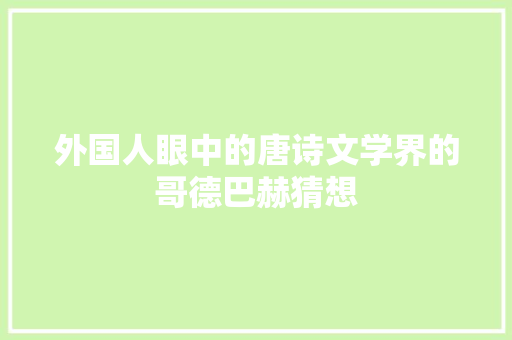
后来,这件事惊动了海内研究唐诗的浩瀚有名学者,于是他们纷纭加入了\"大众猜谜\公众大军,努力的要破译这六首歌的密码。
但是,数年韶光过去了,凑集了海内和部分旅欧、旅日乃至外籍唐诗研究名家的聪慧,《大地之歌》里,仍旧有部分章节歌词的来源,存在争议。
以至于,《大地之歌》被一部分古文学家和唐诗研究者称为\公众唐诗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公众。
《大地之歌》六个乐章根据的六首唐诗,是先由法国女作家戈谢译成法文,编入《玉书》,又由德国作家哈依曼从法文转译成德文,再由马勒谱成乐曲。
难道说,德国人和法国人故意选了不有名作家的不有名作品,故意让我们猜不着?
可是,按照马勒的说法,六首歌词有两首译自李白的诗啊!
还是说,我们被德国人和法国人套路了?
多年后,我们才创造《大地之歌》晦涩难懂的几点缘故原由:
首先,《大地之歌》的成作过程经历了三个人:戈谢、哈依曼和马勒。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三人中个中有一个人对原诗的理解有偏差,翻译就会走样。
其次,外国人翻译诗歌,或者说对诗歌的理解办法,和我们不一样。
大略地说,唐诗的特点是,以咫尺写天涯,以点写面,善于通过有限的意像发散无限的想象。但德国人和法国人翻译诗的时候,讲究的是直译。有啥说啥,没啥不说。而且他们非常计较细节,尤其喜好把生僻字的意思翻译的很透。印象派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尤其如此,比如说戈谢。
举一个大略的例子:《大地之歌》第二乐章,取自李白的名诗《客中行》。
兰陵美酒郁金喷鼻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戈谢怎么翻译琥珀二字呢?她把把\"大众琥\公众字拆成\"大众玉\"大众、\"大众虎\"大众,把\"大众珀\"大众字拆成\公众白\"大众、\"大众玉\"大众,然后再把\公众玉\公众、\"大众虎\"大众、\"大众白玉\公众的意象都译出来。
于是,《客中行》翻译过来的歌词就变成这个样子。
白瓷青亭伫在小池塘上
翠色拱桥如虎背 弓踞在亭岸之间
亭阁中有一群好友相聚
鲜著玉戴 肆酒喧哗 笔颂抑扬
他们的罗袖高挽
丝冠解脱了礼缚 盘上他们的颈领
池面宁澈如镜
清晰灼映著池畔亭间的一景一物
白瓷青亭中的欢腾鼓噪
也倒映在这水镜之中
这样一翻译,可能李太白重生,都认不出这是自己写的诗了。
同样的情形,也涌如今其他几个乐章里。
末了,还有一个缘故原由便是,我们对付翻译成法语的中国人名比较陌生,而唐代有许多墨客的名字发音十分类似,以至于,纵然马勒或戈谢见告我们作者是谁,我们还是要根据诗的内容去预测作者。
比如说,《大地之歌》的第二乐章,名为《寒秋孤影》,作者不详,只有一德语署名为\"大众Tschang Tsi\"大众。
这个人是谁呢?经由学者们的谈论,有三种可能:钱起,张继和张籍。
要根据诗的内容去推断作者,则又会落入印象派墨客的陷阱。
河上秋雾蓝,小草盖白霜。巧匠撒玉粉,花已不芬芳。北风吹花落,莲花浮水上。灯熄夜尽人将眠,心中秋夜长。满脸泪水擦不干,何时结婚见阳光。
这首诗的意境,既像张继的《枫桥夜泊》,也像钱起的《效古秋夜长》,直到今日,学术界没有完备确定详细是哪一首。
虽然《大地之歌》时至今日都让很多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以为很迷,但这不正是唐诗的魅力吗?唐诗经由印象派墨客、当代作曲家以及泰西美声的演绎,以更加直不雅观、生动和深情的办法呈现给我们,这是另一种美感,让我们更加爱上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