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从构思到表达,是一个极为繁芜的过程,作者须随物赋形,曲尽其妙。但是,“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情形时有发生。
一样平常说来,诗歌初成之时,作者尚未从所营造的情景和蔼氛中走出来,加上“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生理作怪,以是难以创造个中的问题。须经由一定韶光的“冷”处理后,问题方才暴露出来。唐子西曾深有感触地说:“诗初成时,未见可訾处,姑置之。嫡取读,则瑕疵百出,乃反复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数四,方敢示人。”这确实是深谙创作甘苦者坦诚的告白。
△袁枚
既然既成的诗歌存在问题,那么改诗就很有必要。清代才子袁枚在《续诗品·勇改》一文中说:“千招不来,仓猝忽至。十年矜宠,一朝捐弃。人贵知足,惟学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传。知一重非,进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定。”袁枚并不否定诗歌“一铸而定”、无须修正的情形存在,但是诗歌有弊病,就须勇于改正,纵然宝爱非常,也要捐弃不惜,只有不断修正,才能锻就诗歌佳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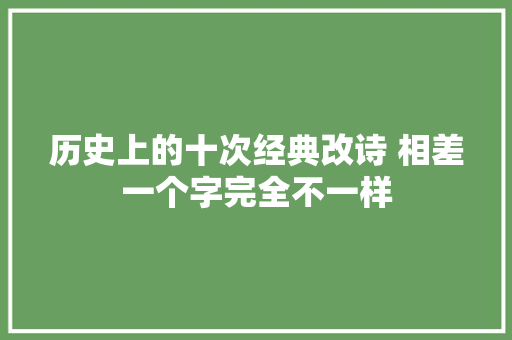
△白居易
历史上通过修正而造诣好诗的范例当算白居易。据周敦颐说:“白喷鼻香山诗似夷易,间不雅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白居易的诗歌之以是深入民气、随处颂扬,修正于有功焉。实在白居易不仅是勇于改诗,乃至以改诗为乐。他曾经役夫自道:“旧句时时改,无妨悦脾气”,从中可见一斑。
改诗,也是造诣经典的有效路子。据《唐才子传》记载:“齐己携诗卷来袁谒谷,《早梅》云:‘前村落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己不觉投拜,曰:‘我一字师也。’”郑谷把齐己《早梅》诗中的“数”字改为“一”字,充分凸显了“早”的意蕴,造诣了一篇经典作品,因此被齐己尊为“一字之师”。《随园诗话》中说,王贞白作《御沟》诗:“‘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以示皎然。皎然曰:‘波字不佳’,王贞白怒而去。皎然暗书一‘中’字在手心待之。须臾,其人狂奔而来,曰:‘已改波字为中字矣。’皎然脱手心示之,相与大笑。”“中”字之以是比“波”字好,是由于从直不雅观形式上看,“此波涵帝泽”一句五字中就有三个字含有“氵”旁,相同部首的字多了,显得没有变革;从意蕴上看,“波”为实指,“处”为虚指,使得上句和下句不相对。而改为“中”字往后,全然没有了这些问题,可见“诗改一字,界判人天。”
只管上述改诗成功的事例成了千古佳话,但是改诗也有不堪利的例子。“王仲圭‘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接风埃看画墙’句,最浑成。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以为如是乃健。刘贡父‘嫡扁舟沧海去,却从云里望蓬莱’,荆公改‘云里’为‘云气’,险些文理不通。唐刘威诗云:‘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荆公改为‘漫漫芙蓉难觅路,萧萧杨柳独知门。’苏子卿咏《梅》云:‘只应花是雪,不悟有喷鼻香来。’荆公改为‘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种修正,袁枚认为是化神奇为腐烂,“活者去世矣,灵者笨矣!
”
袁枚对王安石妄改诗歌不以为然,对自己修正的失落败也严于解剖。他曾经说:“余引泉过水西亭,作五律,起句云:‘水是悠悠者,招之入户流。’隔数年,改为‘水澹真吾友,招之入户流。’孔南溪方伯见曰:‘求工反拙,以实易虚,大不如原来矣!
’余憬然自悔,仍用前句。”袁枚不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并且进一步指出自己“四十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作为不世出的才子,袁枚这种解剖自己、绝不文饰的态度,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文学创作,最空想的境界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但是,妙若天成、不须修正的文章只是创作的愿景而已,纵然有的话,也是百里挑一。对付绝大多数作品而言,修正提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只要不讳疾忌医,“知一重非,进一重境”,便是一种进步。
经典改诗
生活中,不泛有人把古诗翻新,旧瓶装新酒,按照有影响古诗的骨架,改动部分诗句,授予了新的内容,不失落为一种创作,较原作为佳者亦不乏其例。以下罗列历史上的十次经典改诗。
莫子山改诗讽庸僧
宋代墨客莫子山有一次游寺庙,与主持僧交谈中创造其庸俗浅薄,不学无术。临别时,主持让他作诗留念,莫子山想起了一首唐人的绝句: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于是,莫子山便将此诗颠倒了一下次序,赠于主持僧。诗云:
又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终日昏昏醉梦间。
如此一来,忙中偷闲,在春尽嬉戏寺庙的闲雅趣诗,变成了一首彻里彻外庸嘲讽庸僧的讽刺诗。
陈细怪改诗讽愚蠢行为
宋代墨客高翥有诗《清明》: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当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地府!
有一年清明,陈细怪经由狮子山前,瞥见孙、吴两姓为争一处风水地。双方正在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
陈细怪对此愚蠢行为大为嗟叹,遂改高翥《清明》题在山石上:
狮子山前多墓田,孙吴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鲜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毛狗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架须当打,不打何曾到地府!
高翥是江湖派中有突出才华的墨客,他的《清明》是入了《千家诗》的名篇。而陈细怪稍作修正有感而发,讽刺意义愈甚于原作。
王安石改诗出丑
北宋期间,王安石有一次外出巡视,夜宿于一座寺庙中,见寺院墙壁之上题有一首诗:
彩蝶双起舞,蝉出树上鸣。
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
王安石看罢,问寺僧是何人所写,寺僧说题写者是山下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王安石听了说,这样的蠢材,若能及第岂不是笑话!
随即将诗改为:
彩蝶双起舞,蝉出树上鸣。
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
改罢,随从大赞“改得好”。而寺僧却说:“丞相有所不知,秀才写的是一首即景诗,诗景是一幅画,不是两幅画。明月并非玉轮,是本地的一种鸟,它能对景象的阴晴进行预报。白天如能听见它的叫声,夜里必是晴天,并能看到玉轮。黄犬并非黄狗,它是一种金黄色的小虫,习气躲在花蕊里睡觉。”
王安石听罢,非常惭愧地说,都怪我不理解情形,妄下雌黄,请恕我再改过来。
关板桥为老师改诗
郑板桥童年时,跟老师去远足。他们忽然瞥见小桥下面漂浮着一具少女的尸体,惊异之后,老师随口吟诗一首:
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
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
郑板桥听后,不由得旁边考虑,终觉欠妥。他问老师说,为何知道这位少女是16岁?如何知道她是被风吹下去的?如何瞥见她的三魂七魄随着波浪在迁徙改变呢?
这些问题,老师都不能回答,便问他可不可以修正。郑板桥想了想,把诗修正为:
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
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
老师听了,连声夸奖。
清人改诗戏惧内
宋朝程颢有七绝《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后有清人在此诗根本上改动了6个字,戏作《惧内即景》,把怕老婆的人刻画的入木三分。诗云:
云淡风轻近晚天,傍花随柳跪床前。
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拜年。
陈剑魂改诗斥汉奸
汪精卫年轻时,前去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曾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诗明志,表现的十分倔强:
年夜方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首句说他要学习战国期间的荆轲,成为年夜方侠义之士,次句写他被捕入狱时从容不迫,三四句表现出生去世不敷惜,甘为革命抛头颅。
谁料到,昔日信誓旦旦地要为革命献身的汪精卫,在中华民族死活存亡之秋,竟充当了南京伪政府的傀儡头目,出卖民族利益,做了一名大汉奸。
为此,陈剑魂做了一首《致汪精卫诗》:
当时年夜方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块,终惭不负少年头。
陈剑魂在汪原诗前,每句添加两个字,使诗意完备改变,深刻戳穿了汪精卫的可耻行为。
国人改诗控诉日寇罪过
唐朝张继《枫桥夜泊》曰: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诗随处颂扬,流传甚广,寒山寺也因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后来,日寇侵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过。他们大肆屠杀国人,淫乱掳掠,无所不为,闹得民气惶惶,鸡飞狗跳。昔日繁盛热闹繁荣的寒山寺也是门庭冷落,游人罕至。有人见此惨状,改张继诗吟道:
月落儿啼妻哭天,江南劫火不成眠。
苏州城外寒衣尽,夜半枪声到客船。
此诗生动形象,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累累罪过。
夏衍狱中改诗
明末清初,有一首传诵一时的打油诗: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
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1974年,夏衍在狱中想起此诗,便把他改为: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国人改诗嘲讽电车
宋代理学家邵康节曾写过一首五言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落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墨客奥妙利用了一至十这10个数字,寥寥几笔便描述出了一幅景致宜人的村落庄画面,堪称经典。
新中国成立前,有人有感于乘坐公共汽车的困苦,便把这首数字诗改动了几个字,以嘲讽褴褛迂腐速率也慢的电车: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
高下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谭鑫培临场应变经典改诗
京剧大师谭鑫培年轻时,由于履历不敷,演出时曾涌现过一次差错,而他随机应变,不但没露出马脚,反而使演出效果更完美。
有一天晚上演出《文昭关》,谭鑫培在剧中饰伍子胥。伍子胥应该腰挂宝剑,上场后有这样四句唱词: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腰中枉佩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但是,由于管道具的人一时轻忽,错把宝剑换成刀。谭鑫培当时也没有把稳,出场后才把稳到这一点,但又来不及改换,他急中生智,手握腰刀喝道:
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浇。
父母痛恨不能报,腰间枉挂雁翎刀。
这一改,改得天衣无缝,再加上他那竹苞松茂的唱腔,博得不雅观众的满堂彩,实在是经典之作。
你还知道哪些一字之差的美妙吗?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5月13日16版《闲话改诗》、腾讯网
文章作者:朱美禄
本期编辑:兰亚妮、张永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