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话说“西行漫画”
美国写了一本《西行漫记》,想必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有人还在延安见到了一本《西行漫画》,你可知道吗?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的画家陈叔亮有一个练习速写的画册,他随身携带着这个画册。从南方到北方,从西安到延安,陈叔亮沿途画了许多速写,真实地记录了西北解放区人们原生态的山川景物,让民气酸的生活苦难,不畏霸道的年夜胆抗争。1941年4月,陈叔亮把这本速写画册送给毛泽东欣赏,并请毛泽东在封面上题签,在扉页上题词。毛泽东对美术作品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毛泽东精通文学艺术,有很高的书法成绩,艺术总是相通的。毛泽东负责翻看了陈叔亮的画册,并振笔在画册封面上题写了“西行漫画”四个行书大字。著名书法家张铁民在《文字春秋》里对这四个字专门做了评价:“笔力雄劲,溶颜体和北魏的笔触于王羲之书风的结体之中,逆锋入笔,回锋收笔,点画圆浑,雄浑厚实,可与五六十年代的题刊书迹相媲美。”[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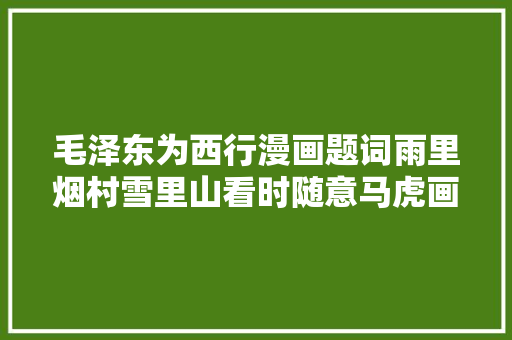
可见,毛泽东并不是随意书写,而是非常存心的。
大概人们对陈叔亮的名字不太熟习,尤其是不搞美术、书法的朋友们。实在陈叔亮在美术、书法上是成绩颇深的。他是中国当代有名书法家、美术家、美术教诲家,是原中心工艺美术学院创始人之一、副院长、党委布告,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并任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叔亮原名陈寿颐。1901年陈叔亮出生于浙江黄岩的一个农人家庭,自幼清苦贫寒的生活未曾消耗他酷爱艺术的天性,家乡民间艺术的自然熏陶及村落庄学堂先生长西席王笠斋的点拨与教授,为他的艺术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根本。
晚年陈叔亮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青年陈叔亮迅速接管新思想并积极投入时期的年夜水。1930年至1931年,陈叔亮就读于刘海粟师长西席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画家倪贻德师长西席修习泰西画技法。抗日战役爆发,他以多才多艺的创作才能,不遗余力地参加各种抗日宣扬活动,画漫画、画宣扬画,创作抗日剧本、歌曲,并先后在学生中组织“爱国剧社”(1931年)、“呼啸化妆宣扬队”(1937年),到街头和村落庄进行抗日救亡宣扬。“七七事变”爆发后,陈叔亮于1938年秋带着三个进步青年学生,一起辗转千里迢迢来到了中国公民革命和抗战的圣地延安,并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的8年当中,陈叔亮不仅创作了相称数量的木刻作品,出版过《新美术运动及其他》论文集,并做了近千幅反响延安军民生活的速写。如他本人在回顾录中所说:“在鲁艺先后8年多,我始终带着自己的速写本子,出入于广大群众之中,面对着周围的生活图景,画下了大量的速写画稿,称之为《西行漫画》”。
1942年,陈叔亮出席“延安文艺漫谈会”。翌年,他深入边区屯子、深入群众生活,在广阔的黄地皮上对皮影、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形式,特殊是西北民间剪纸艺术——窗花进行专业性的发掘、网络、整理、保护以及研究。之后,揭橥了中国第一部研究剪纸艺术的专著《窗花》(1945年3月脱稿,1947年出版)。1947年至1949年春,陈叔亮离开延安来到山东老解放区,担当山东滨海地区地委主理的《滨海画报》社社长,这段韶光他创作和揭橥了一系列合营解放战役的木刻及漫画作品。
2、“创新求变”的时期
1949年,陈叔亮出席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化艺术事情者代表大会,并担当第一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后来又调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美术事情室主任、华东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此间,在刚刚政权交割、“改天换地”的上海,作为党的美术事情领导人,他为整顿和建立美术界的新秩序、新不雅观念、新面貌作了大量深入、细致、颇见成效的事情,同时揭橥了主要的连环画作品《走向那里》。
1951年,陈叔亮被调往北京任职。先后担当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文化部艺术教诲处处长,及文化部艺术教诲司副司长。并于此间出席了第二届文代会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肩挑行政事情重担的他再无韶光进行美术创作,而是废寝忘食于一名美术事情领导者的任务。
1957年,陈叔亮调任中心工艺美术学院党支部(1961年改为党委)布告、副院长,直至1982年正式离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处在人生晚年的陈叔亮以巨大的革命激情亲切和“忘老”的事情精神,四处奔忙呼号,终于与美术界的同仁们一起建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推动中国书法得到新的繁荣发展。身为中国书协创始人和领导人,他以80岁的年纪和一个“老兵”的姿态,尽心竭力、一丝不苟地为“书协”做了许多培植性的事情。此时,他也迎来了书法创作的高峰期、丰收期。为了知足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哀求,他创作、展出、揭橥、赠予了大量精彩的书法作品。个中部分收入《叔亮字画》《陈叔亮书法集》。
陈叔亮的艺术主见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便是“创新求变”。他曾这样说:“接管古人履历,不即是盲目地重复古人,要长于用其法而不为法所用,即石涛所谓‘师古人之心’而不强调‘师古人之迹’,石涛所谓‘无法之法是为至法’,也不即是否定古人,割断历史。从无法到有法,又从有法到无法,才能达到石涛所追求的‘至法’。” “古人方法有可为我用者,必须继续发扬,古人方法有不可为我用者,必须批驳改造,不能盲目抄袭。旧方法与新内容产生抵牾时,必须服从新内容的哀求,打破成法,大胆创立新方法,寻求与新内容相适应的新形式、新技能、新风格。”
在书法创作上,“他反对‘言必称二王’、‘笔笔有出处’的教条主义,而主见广泛地向历代名家的长处学习。同时强调‘贵在师心、病在师迹’,明确提出书法“四新一变”主见:新的构造、新的笔意、新的气势、新的面孔、生平求变。并以实践光鲜地表示这种追求。一方面,客气肠拜古人为师,坚持读碑、临池的日课。另一方面,“入古出新”,追寻揣摩属于自己一家的、新鲜的艺术风格和形式,反对手腕上的“一招灵”和面孔上的“固定化”。凭借着这样的艺术主见与不懈追求,陈叔亮的书法日见出神入化,特殊是草书,在当代书坛可谓独树一帜,“多能不独张颠草,满纸云烟见性真”(赵朴初师长西席评价)。
3、雨里烟村落雪里滩
回过分来再说毛泽东欣赏“西行漫画”的过程。
毛泽东为陈叔亮的画册题写了“西行漫画”之后,乘兴在扉页上又给他题写了一首诗:
雨里烟村落雪里滩,
看时随意马虎作时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
多买朱砂画牡丹。[1]
毛泽东题写的四句诗先人是化用了宋代画家李唐的《题画》。李唐的原诗是这么写的:“云里烟村落雨里滩,看之如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个中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与毛泽东题诗各有两字不同。是毛泽东影象有误还是毛泽东故意改动,不得而知。虽有改动,但是并未改变原诗意义。李唐的《题画》仅第一句论画,别的三句都是弦外之音。李唐(约1066一约1150)字晞古,河南人,乃南宋画院“四大家”之一,宋徽宗期间就已经是画院待诏了。后因金兵攻陷汴京被俘,遂潜逃南渡,历尽颠沛流离之苦,在将近八十岁的时候,一度落泊于南宋都城临安,靠卖画度日。据明代郁逢庆《字画题跋记》载:李唐初到杭州,无人赏识,靠卖纸画糊口,生活十分艰巨。这首诗意在讥讽南宋崇尚艳丽花鸟的浮华时尚,用以抒发墨客心中的愤懑与不平。
宋代所谓的“花鸟画”与当代的国画科目划分有所不同,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花和鸟,花鸟画实则是动、植物画,以花代表植物,以鸟代表动物。畜兽、竹石、鱼虫皆另立科目(山水中,树石、木屋也是各自主科的)。而当代中国画则分为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科,而树石、村落、楼不雅观等多数归于山水。畜兽、竹石、鱼虫之类多归于花鸟。李唐的花鸟画在当时尤为突出,吴其贞《字画记》中记有李唐《梅竹禽雀图》,并云“甚剥落”,然“精彩尚在”。《严氏字画记》中也记有李唐的《古木寒鸦图》。然而他自己在诗中却感慨:“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实在那是初到临安落魄之际的感慨。后来他的山水、人物、走兽越画越精,尤以山水为最佳,并创大斧劈皴之法,所作长图大幛,气势宏伟,独步南宋画坛。其时,李唐的画不但入时人俗人之眼,而且已经入名家大家之眼,并再度被高宗重用,仍任朝廷画院旧职。
毛泽东翻看陈叔亮的画册之后,援笔立就,化用李唐的《题画》一诗,可谓恰到好处,毛泽东在诗词书法方面的艺术教化之高可见一斑。毛泽东为陈叔亮题写这首诗显然是对画家绘画艺术切实其实定。前两句是对画家绘画艺术的个中甘苦发出内心的由衷感慨;后两句,毛泽东从画家的诸多速写中看到了延安那些艺术家的革命激情亲切,他们从白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所处条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革,但是他们飞腾的革命激情亲切不减,这种激情亲切传染了毛泽东,由此而抒发了自己对画家、对画作的讴歌。
陈叔亮看了毛泽东题写的诗句非常高兴,认为毛泽东是在讴歌他的速写。但有的朋友以为画册内容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题材表现的却是公民的掉队面,认为毛泽东是借李唐之诗寄望于画家,更多地表现公民生活的革命方面,进步方面,光明方面。
当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们无法走进毛泽东的内心天下,毛泽东为陈叔亮题写李唐的《题画》诗,二心坎是如何思想的,我们无论怎么剖析,也只能是猜度了。
[1] 张铁民著:《文字春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