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在文学、诗词、音乐、艺术方面取得的造诣与他的身份完备是不相匹配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一定是宫廷音乐家,或者是附庸风雅的士大夫阶层,但实在,他只是一介布衣,而且生平过得相称清贫。
姜夔曾多次参加科举,但都名落孙山,为了坚持生存,只得在显贵之家做“傍友”,依赖吟诗作曲博得王侯将相的赏识,说白了便是依赖自己的才华领取微薄的收入。
当然,做傍友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了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之外,陪主家饮酒打牌,娱乐消遣,还要旁边逢源,看主人的神色,傍友是一种仰人鼻息的寓居生活。
正如清代人在条记中对傍友有过这样的记载的:“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醉,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吊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这样的记载虽然对傍友的生活有戏谑夸年夜,但是将傍友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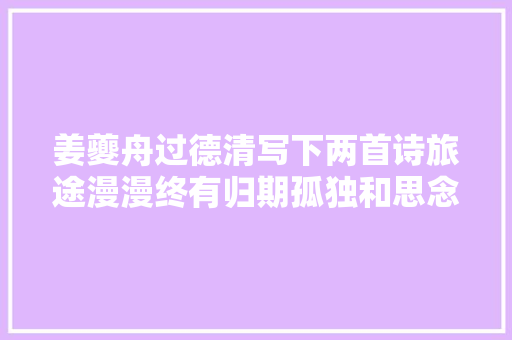
为了生存,姜夔在三十岁投靠了和父亲生前交好的墨客萧德藻。萧德藻是与范成大、杨万里、陆游、尤袤齐名的墨客,由于赏识姜夔的才华,加之情趣相投,两人一见如故。萧德藻特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姜夔。萧德藻调官湖州,第二年暮春,正式去湖州上任,姜夔也决定追随萧德藻。
途经杭州,萧德藻先容姜夔认识了赋闲在此的著名墨客杨万里。杨万里对姜夔的诗词惊叹不已,认为姜夔的诗风酷似唐代著名墨客陆龟蒙,并说“为文无所不工”,由此两人成为忘年之交的诗友。
之后,杨万里还专门写信,把他推举给另一著名墨客范成大。范成大读了姜夔的诗词,也极为喜好,认为姜夔高雅脱俗,文字人品酷似魏晋间人物。
得到杨万里、范成大两位诗坛大佬的流量加持,姜夔在诗坛声名鹊起,当时的名流士大夫都争相与他结交。连学者朱熹也对他青睐有加,不但喜好他的文章,还佩服他深通礼乐。著名词人辛弃疾对他的词也深为叹服,曾和他填词相互酬唱。
湖州弁山风景幽美,公元1190年,姜夔正式卜居湖州弁山苕溪白石洞天,遂在圈子中有了“白石道人”的雅号。在湖州,姜夔度过了人生中较为安适、惬意的十年光阴。在湖州居住期间,姜夔仍旧时时四处游历,往来于苏州、杭州、合肥、金陵、南昌等地。
某一年秋季,姜夔乘船过湖州德清,萧瑟的秋风,让墨客触景生情。姜夔回顾自己飘零寓居的岁月,又想起合肥女子,一时情难自抑,写下了两首同名诗歌《过德清》:
其一
木末谁家缥缈亭,画堂临水更虚明。
经由此处无相识,塔下秋云为我生。
第一首写的是墨客船行所见之景。姜夔的生平险些是在流落中度过的,这样的情景是墨客经历过很多次的,本来没有可写的。可是这一次,却偏偏让墨客心中升腾起些许况味来。
那不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沉浸式体验,那是满目山河空念远的觉得,墨客就这样百无聊赖地看着两岸的秋天景色。忽然,他看到远处一座亭子的一角屋檐从树梢间隐约显露出来,墨客试图用目光锁定这座亭子。
但随着船只的前行,墨客的视角也发生了位移,那亭子又被树枝粉饰起来,变得若隐若现,这无法捉摸的亭子使人产生飘忽不定的觉得,使得诗境呈现出虚幻的色彩画面。
船只渐次前行,一座临水的建筑物涌如今视线中,这让墨客面前一亮。清泠明澈的秋水映出它华美的倒影,这浮光掠影的景物只会给墨客增加惆怅与寂寞,于是产生了交情抚慰的生理需求。
这齐心专生理反应正是诗歌从写景转入叙事的契机。但是在德清,墨客没有相识的人,交情只是镜花水月般的存在,墨客是孤独的。
船只渐行渐止,两岸的风景也渐次变革着样子容貌。当船只停泊在水湾处时,墨客看到江岸两边耸立的青山,还有建在青山上的一座塔,而塔下的一片漫无目的地晃荡着的孤云,像是理解墨客的孤独一样,步履匆匆地前来陪伴墨客了。
这样的情景与诗境,组合在一起便像是一幅寂寞而苍凉的水墨画,画面中的水和天空都是大片的“留白”技法,而墨客与船只彷佛只是随意勾勒的一笔。但是,塔下的秋云没有绚丽的色调,只有清冷的气息,他能读懂墨客的孤独吗?墨客四顾茫然,心境加倍显得落寞。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两个孤独的人》中说:“他俩从没有对人讲述过的,也险些自己都没有招供过的,这两个还险些是陌生的人彼此都暴露了出来。每一声叫嚣都在他们的灵魂中得到了回响,由于两个人在痛楚上是相亲共感的。”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该当在乎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可是,在墨客姜夔的德清之行中,他做不到不在乎目的地,他没有看风景的心情,这只是江湖间的一位匆匆过客而已。
《过德清》其二
溪上佳人看客舟,舟中行客思悠悠。
烟波渐远桥东去,犹见阑干一点愁。
第二首的开头一句“溪上佳人看客舟”,很是耐人寻味。说这是墨客在船头的所见也对,由于他看到了伫立在岸边的一位佳人。佳人彷佛也向墨客所在的行船望过来。
四目相对间,他才创造,这位佳人只是一位陌生人,她或许也是在岸边等待她的心上人,她或许也是一位“误几次,天涯识归舟”的痴情女子吧,墨客心中这样想着。
墨客由佳人凝望归舟自然遐想到情人遥望自己。姜夔的爱情也是曲折而艰辛的,他客游合肥时,重逢了一位歌女,并与之坠入爱河,两人曾经度过了一段浪漫的光阴。可是美好的光阴总是这样匆匆,姜夔为了生活而怅意独行的孤单背影与他们月下花前你侬我侬形成了光鲜比拟。
可是美好的光阴总是短暂的,他们的浪漫爱情在韶光的流逝中也付诸东流。为了生存,姜夔只能在定居合肥与江湖流落之间做出决议。在纠结、无奈、彷徨的繁芜心态下,姜夔与心爱的合肥女子究竟成了天各一方的两处闲愁。
当姜夔再次来到合肥时,嫡黄花,他苦苦寻觅这位女子,可是踪影难觅。昔日的恋人或许早已有了新的生活。究竟,爱情输给了韶光,但合肥女子却成为了姜夔情绪天下里挥之不去的丁喷鼻香结。
姜夔的这种情绪纠结一如唐代墨客李商隐笔下的“芭蕉不展丁喷鼻香结,同向东风各自愁”。一次,姜夔舟过吴兴,他看到画船上一位歌女和昔日恋人颇有几分相似,这都让姜夔产生了再回顾恍然如梦的觉得。
这次吴兴之行就像姜夔生命中的又一个似曾相识的插曲一样,短暂的惊喜换来的却是墨客心中的层层荡漾。怅惘良久后,墨客才从梦境回到现实。于是,他在《琵琶行》一词中写下了“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他的恋恋条记本上又多了几行记录心途经程和情绪经历的笔墨。
麦家师长西席在《人生海海》中说,人活一世,总要经历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气,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时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落的。
这次舟过德清,墨客姜夔也并不认识岸边的佳人,但也勾起了他对前尘往事的回顾。或许,墨客是佳人眼中的一道风景,但对付一个人的旅途来说,佳人又何尝不是墨客眼中的一道风景呢?实在,在人生路上,我们又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呢?
在这孤独的旅途中,面对岸边若隐若现的一座亭子,墨客内心充满不愿定性,他的焦距无法准确捕捉它的画面;面对飘荡的白云,墨客无法与它分享内心的孤独,他找不到一丝抚慰;面对凝望的佳人,墨客感到的只有相互伶仃的飘零之感,他同样也找不到一丝抚慰。
墨客内心一片茫然,他须要一个能柔柔地托住他身心的空间,他须要一种能让他感到安适的归属感。可是,在舟过德清的旅途中,这个空间和归属感都是不存在的。
客船随着烟波渐行渐远,穿桥而过,一起向东,驶出了画面,也驶出了诗境。同时,渐远的烟波也象征着墨客思绪的绵缈不尽。渐行渐远的不但是身边的人和事,或许还有曾经的自己。
有人说,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可是,对付姜夔来说,该当在这句话上再加上一个后缀语,才能完全地表述墨客的人生足迹和心途经程,那便是:在一个人的旅途上,孤独和思念,总有一个萦绕在心头。
或许,是墨客姜夔接管了这样的生活,才让他在踽踽独行的人生旅途上多了一份自洽。曾经的科举失落利、曾经的生活失落意、曾经的情绪困惑,也都会像行船划开的水波一样,随着船只的远去,水波依旧会归于沉着。
是啊,对墨客姜夔来说,接管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调度自己的状态,找到连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
旅途漫漫终有归期,甜蜜苦涩都有尽头。要接管世事无常,接管飘零寓居,接管平淡如水,接管阴差阳错,接管跬步不离的孤独和思念,接管自己的不完美,接管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
一个人的旅途,孤独和思念,总有一个萦绕在心头。姜夔的这两首诗,将旅途中的孤独和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南宋张炎评价姜夔的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读姜夔的这两首诗,确实能给人带来空灵唯美、清空高远的极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