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延巳的思念和愁绪,无处言说。在那个春将即暮的时节,他独自守着心中的那份执着,在寂寞中等待,在等待中煎熬。他的词,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将他的思念与愁绪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孤独的身影,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守望。
如今吟诵这句词时,依然能感想熏染到冯延巳那份深奥深厚的思念和无法排解的愁绪。它穿越时空,触动着我们内心最优柔的地方。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无法言说的思念,犹如冯延巳一样平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一句话或一个场景勾起,让我们深深奥深厚浸在回顾与惆怅之中。
《鹊踏枝·几日行云何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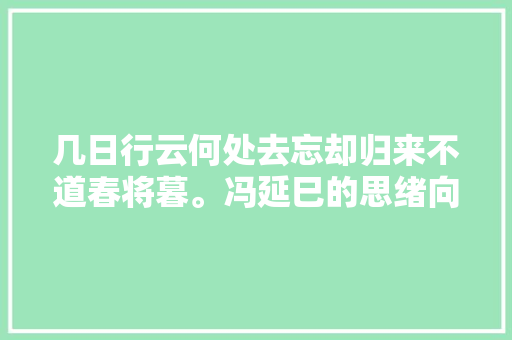
南唐·冯延巳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怀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喷鼻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缭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
冯延巳(903 年—960 年),又称冯延嗣、冯延己,字正中,五代江都府(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他是五代十国期间南唐著名词人,仕于南唐烈祖、中主二朝,三度入相,官终太子太傅,卒谥忠肃。
冯延巳在南唐朝廷任丞相,在政治上未见有什么建树,在词的创作方面却取得了令人晕眩的造诣,与李后主的作为很相似。冯延巳对词的贡献在于将词的境界更深化了,由于深化,他的词不限于对某一时某一人的详细摹描刻画,而是把它们引领进入“纯文学”的境界,使之具有广泛性。以是,冯延巳词的感伤忧郁是一样平常意义上,可以指代任何目的物,由于它们本身就没有“目的物”。
从这层关系上说,冯词的精神内涵近似李商隐的无题诗,还可以上溯至《诗经》,如《秦风·蒹葭》便是这样的境界。人们可以明确地陈说《蒹葭》的主题在于追求,追求那位“伊人”,但伊人详细所指,则无法确定,是爱情?是交情?是空想?彷佛都是,但任何一项都不敷以涵盖“追求”的全部。李、冯的作品都达到了这种“形而上”的艺术境界。这是许许多多的文学家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境界。
这首词以“行云”起兴,次第引出“百草”“千花”“双燕”以及“喷鼻香车”“柳絮”“春愁”。这些形象或意象在诗词中司空见惯,但在这里经由特殊的组合,就产生了朦胧曼妙的艺术之美。一首普通的怀人词抽象为广义的追素抒怀诗,内涵丰硕了,境界开阔了,对情节和感情则作了虚化处理。
行云,依《诗经》的六义说,是“比而兴”。浮云飘忽不定,谁也不能确定它从何处来,飘向何方,或者随时消散于虚空之中。而那位意中人,也正如浮云一样平常,已记不起回到他的出发点,全不管春暮时分。
百草繁茂,千花盛开,清明时节,路上人熙熙攘攘,车如流水马如龙,可是外子之车在哪里?一定是被某株树挂住了,使他流连不返。这位女子因此进入半虚半实的天下。她泪眼婆娑,倚楼纵目春山之外,追随流云消散。春山无语,流云无情,她满腔哀怨无处倾诉。
声音响起,却是燕子呢喃。它们来自远方,抑或城的东西南北,飞行所过,或许曾见他的车马?她殷勤讯问燕子,燕子虽则有声,但无语。它们大概是“有语”的,向她细叙与他路上相逢情景,而且明确指示他淹留何方。可是鸟语不能解,空自增烦忧。与燕子对话,既无果,她把希望寄挂在夜空下的梦。她身居闺阁,无法追随他随处为家,难以如燕子一样平常与他在路上相逢。
在梦中她是自由的,可以任意逍遥,上穷碧落下黄泉,天上人间会相见。可是,她又很不自傲,又有几分担心,她不敢担保确实能在梦中找到他。纵然找到他,他是否肯与她共诉别情?悠悠人生,悠悠春梦,人生如春梦,春梦即人生,都是那么不可靠。
人与“双燕”对话,是本词最有创意的句子,燕与雁,墨客词人很乐于取入作品,该当是比较熟习的题材,但他们总能别开生面。这首词中她问燕子是否路遇他,为旧题注入了新生。
冯延巳的另一首《鹊踏枝》同样精彩,词云:“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边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月牙人归后。”它相称于前词的应答篇,原来她埋怨不已的那位“外子”与她心情、处境相同,也在期盼相见,只是因世事难以把握,不能成行,只等月牙照耀下,两人重聚,两情相悦,离愁别绪才会闭幕。词史上这类应答词很多,如韦庄的《女冠子》两首,柳永的《雨霖铃》和《八声甘州》,是应答之作中的精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