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午桥(1)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2)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3)。古今多少事,渔唱(4)起三更。
注释
(1)午桥:即午桥庄。唐朝时斐度曾退居于此,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把酒论文,不问世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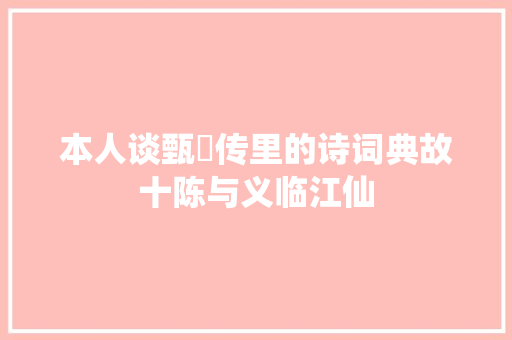
(2)长沟流月:同杜甫《旅夜书怀》一诗中“月涌大江流”之意,形容岁月滔滔流转而与会不歇。
(3)新晴:初晴之意。
(4)渔唱:渔歌之意。
译文
回顾起从前在午桥上宴饮,在座的都是豪杰贤士,月辉煌映在水里,随着流水无声无息地消散。在疏淡朦胧的杏花影里吹着笛子,笛声悠扬至天明。
这二十多年的颠沛流离,像一场梦一样平常,在登楼远眺时,回顾涌上心头,人虽尚在,但仍如此惊心伤感。古往今来发生多少事,就全交付与三更时响起的渔歌吧。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是宋朝期间著名的文人,他醉心于作诗,词作所传不多,一样平常皆认为他的词风近似于苏东坡,语意超绝,豁达明快。
实在,陈苏两家可算得上是世交,陈与义的曾祖父陈希亮与苏轼的父亲苏洵是旧交,苏轼初入仕途时,陈希亮乃是他的上司,对苏轼十分严厉,让年少气盛的苏轼十分不满。可是陈希亮司法严明,嫉恶如仇,向为平民百姓所爱戴。后来苏轼十分感佩他的为人,在他过世后,还为其作《陈公弼传》,以期将他公道严明的业绩流传后世。至于陈希亮的四子陈慥,更是苏轼的莫逆之交,常和苏轼彻夜谈佛论道,苏轼曾写诗调侃他“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位以惧内而有名后世的陈慥,便是陈与义的叔祖。至于陈与义自己,又与苏轼的徒弟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交好,耳濡目染之下,词风近似苏轼,倒也就十分合理了。
宋朝重文轻武,积弱不振,许多文人亲历靖康之难,颠沛流离。南渡之后,将国破家亡之悲、世事沧桑之感发而为词,情真意切,造诣多少千古名篇,陈与义的《临江仙》便是一例。这一首《临江仙》前半阙怀想当年在洛阳时与其他文人雅士交往的环境,在杏花疏影里,演奏笛音至天明,是何等的浪漫散逸。可自北宋灭亡,仓皇南渡,那些往事仿佛梦一样平常不真实,昔日的流金岁月比拟于目前的落魄苍茫,又怎能不惊心惶恐呢?
甄嬛甫入宫时,装病避宠,即便难免要被势利眼的寺人宫女们讥讽看轻,可外有受宠的眉庄护着她,内有忠心的贴身丫鬟流朱、同父异母的妹妹浣碧、崔槿夕以及寺人小允子伺候,日子仍勉强算得上是沉着安乐。有天春暖花开,忠心的小允子为她在御花园里扎好了秋千,甄嬛神往着“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的情致,带着箫前往御花园,谁知却在那里遇见了皇上,从此开始了她的后宫斗争之路。
甄嬛性喜散逸安适,可惜这样的日子究竟犹如昙花一梦,她很快就卷进了后宫争斗中,十多年来数次在受宠和失落宠之间苦苦挣扎。末了,她的对手一个一个倒下,可她的嫡亲至交亦一个一个逝去,即便末了当上了太后,可若回忆起那一年杏花疏影中的秋千与箫声,恐怕亦是难逃“此身虽在堪惊”的悲惨吧。
(这个系列内容涉及《甄嬛传》的,我只针对剧情,不扯雍正朝真实的历史,历史粉勿扰,在硬套雍正朝背景的架空小说改编剧里评论辩论历史我也不会干这么NC的事儿;服化道、演技等等也不会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