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去详细统计,单只看《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程度,便能感想熏染到传统诗词的受众群体有多么弘大。
并且,当代由于人口基数大,加上教诲的遍及,当代的传统诗词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像唐朝近三百年国祚,一部《全唐诗》险些席卷了大部分流传下来的唐诗,然而其数量仅四万八千九百余首。
笔者曾在某图书馆看到一部名为《二十世纪诗词选》(大概是这个名字)的书本,上面所录当代旧体墨客不过百余人,但诗词数量已达数千篇。而这部书本上的墨客,相较于当代诗词创作者,不过沧海一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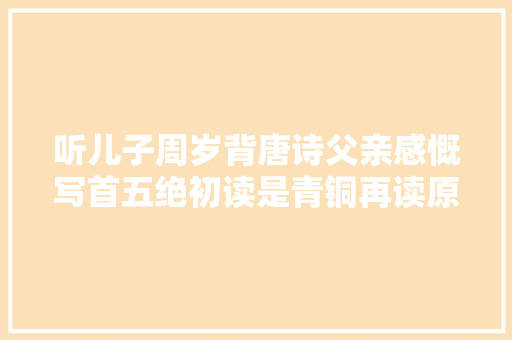
由此可见,当代诗词数量,定然是令人惊叹的。可是,这么多的当代诗词,却没有几首作品,能够像唐诗宋词那般流传于世。
其缘故原由大概有三:
第一,当代诗词良莠不齐,大部分诗词作品的不具备可读性、思想性,更遑论流传。
如今教诲虽然遍及,但大部分诗词创作者,只摸到了门槛。搞懂了格律,便以为自己懂诗,于是开始写诗。乃至还有很多人,连门槛都没摸到。这些人乐此不疲写出的诗,质量可想而知。
第二,如今的环境,诗词发展的空间土壤比较少。
中国古代,诗歌在文学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先秦期间,孔子编撰的《诗三百》一贯是儒家经典,是古代读书人必读书目。不读诗无以言。
唐宋很长一段韶光,科举都因此诗赋为主。李白没有科举资格,却由于诗写得好,被高层欣赏,被唐玄宗任为翰林学士。
到了明清期间,只管科举不考诗歌,但能够写得一手好诗,绝对不会混得太差。
而且,古代的文人,一旦写出一首好诗,文坛便会相互诵读,民间百姓以为好的,也会谱曲传唱。
如今的传统诗歌,不过是一种茶余饭后的爱好,并不会受到社会知识分子(相称于古代文人)的关注。即便是有好诗,也无法普罗大众。
第三,则是当代诗词,还没经由韶光的沉淀。
很多人都想著书立传,想在历史中留下些许作品,能够不朽于世。但随着韶光的流逝,大浪淘沙之下,许多当时认为好的作品,脱销作品,终极泯没在历史的车轮之下。有些作品,当时不被看好的,反而成为了经典。
民国期间,西学东渐,传统诗词的生存空间比如今更为狭小。或许当时的人,也认为他们那个时期的诗词作品,无法流传。但鲁迅、郁达夫、程坚甫、聂绀弩等人,依旧有不少诗词作品流传于今。
等到几十年、一百年后后,会有一批当代的墨客与诗词作品,流传于世。
而在流传后世的墨客当中,彭莫应有一席之地。
彭莫笔名金鱼,80、90后的诗词爱好者,该当对他不会陌生,在网络诗坛十分有名,拿过多次诗词赛事的奖项。其余,一些专业的诗词研究的学者,也对彭莫十分钦佩。高校的教授若要给学生讲当代诗词作品,多数不会漏过金鱼(笔名)。
金鱼的诗词作品,以细节动人。他总是能够捉住生活中那不经意、而含有各种情绪的细节,来打动人心。而且,他的诗词作品,没有那种佶屈聱牙分开现实生活的意象,也没有晦涩难懂的典故。
正如他自己所说,追求古典主义中的当代。
金鱼有一可爱帅气的儿子。孩子满了周岁不久,牙牙学语,彭莫便教背唐诗。听到儿子背唐诗,彭莫感慨之下,写了一首五绝《金小鱼周岁背唐诗》:
红柚生盐国,黄河遇海牛。我闻心盛喜,李杜莫深愁。
细读这首诗,我深受感触,便转发给一位诗友欣赏。诗友学诗多年,功底深厚,初次看到这首诗时,他不禁迷惑:前两句是什么意思?错别字吗?
写四句诗,两句都是错别字,诗友以为金鱼是个青铜,但当我提醒诗友看题目时,他再读一遍,才知金鱼是王者。
前两句,实在便是“红豆生南国”与“黄河入海流”,看似是错别字,实在这是墨客在写儿子背唐诗的读音。
周岁的儿子,吐字不清,以是把“红豆”读成“红柚”,把“海流”读成“海牛”。
任何人,都会经历这段过长,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任何人,都是数十亿人口中的一员。但在父母的心中,孩子便是自己的天下,当看到孩子从出生,到发展,学会说话,学会走路,每一个阶段,都会令父母无比欣慰激动。
以是,听到儿子背唐诗,虽然口齿不清,但金鱼心中依旧十分欣慰,那一刻,他感想熏染到了儿子的发展,感想熏染到了作为父亲的快乐。虽然只是几句发音不准的唐诗,但在金鱼耳中,这无疑是天籁之音。
这首诗虽然大略,但自然流畅,个中蕴含的父爱,是金鱼的,也是天下父母的。这首诗传达的情绪,或许是个人的,但险些所有的父母,都有共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首诗呈现的,又是人类普遍的情绪。
一首五绝不过瘾,文章的末了,再录金鱼几首作品:
《看马戏》魔术讶遁地,秋千惊入天。无心笑小丑,我亦扮多年。
《秋》忽然秋意深,独坐久沉吟。黄叶红砖地,西风北客心。多情怜旧往,一梦到如今。此夜潇潇雨,天涯各自闻。
《深巷》深巷光阴入羽觞,阳台小坐树成围。晚风吹落槐花雨,隔壁阿婆缓缓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