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好书、好片和有趣的文史知识。
♥喜好就关注一下吧♥
几年来,很多环绕“古诗词”的电视节目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都备受关注,“古诗词”一下子变得热门了起来。
通过传媒的推动,“古诗词”的魅力有一次在我们面前展现。关注度是有了,可在创作上却仍旧无人问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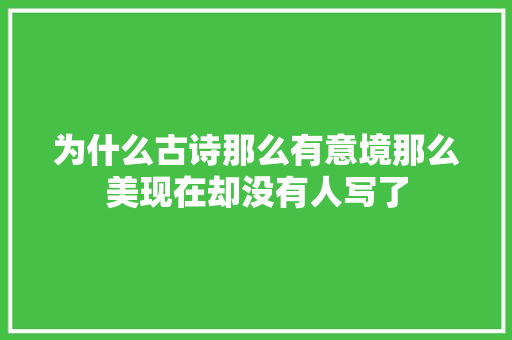
令人不禁发问:为什么古诗那么故意境那么美,现在却没有人写了?
实在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繁芜的问题,既有历史的成分,又有时期的成分,但我们通过个人的视角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梳理,把它放在“当代人为什么不写古诗”这个问题中去思考,答案还是比较一览无余。
当然,当代人为什么不写古诗?
这问题乍一听有点奇怪,当代人当然写当代诗了,为什么要写古诗?就彷佛鸡当然生鸡蛋,肯定不会生鸭蛋啊。
但小文要这么回答,大家肯定以为我敷衍,由于没有辩证思考,也没有逻辑推理,只是用结论办理问题,而没有对深层缘故原由进行思考。
以是,小文决定好好和大家剖析一下。经由我负责的思考,总结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缘故原由:不会写、不用写、不想写。
不会写
虽然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被哀求背诵默写古诗文,从诗词大意到情绪赏析,语文考卷早就逼迫着我们磨炼这些能力,在心里头数得上数的墨客名,没有千八百的,也得有数十个吧。可就现在问你会不会写古诗,我想十个里有八个都得说不会吧。
按理说我们对古诗文该当很熟习才对,这么多年的学习,怎么就写不出一篇精良的古诗来呢?
这直接点看,紧张是我们学习内容和办法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紧张的知识来源还是教诲,而古诗词写作在现在的教诲中根本没有被重视。
首先,我们对古诗的学习都是零散的,皮毛的,一个学期可能也就学那么几首吧,比起古墨客给我们遗留下的名诗佳作来说不过沧海一粟。
其次,我们学的是怎么赏析诗歌,而不是怎么写诗歌。我们从来只是作为读者来对待一首诗歌,从这首诗里读到了什么?这首诗有什么过人之处?而从来没有传授教化生以创作者的姿态来看待古诗,墨客是怎么写出这首诗歌的?
末了,我们的传授教化中也短缺干系的演习,考试从来没见过考古诗写作吧?平常的作业也不会支配古诗写作的任务,说实话,即便支配了,大部分语文老师也不知道如何给同学们指示,毕竟他们就没学过古诗词写作。
当然,这种教诲现状的产生是有源远的历史成分的。这就要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系列文学领域的变革。
个中与古诗词关系最紧密确当属“诗界革命”,这是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的。
认为想要挽救中国诗歌日益衰落的命运,必须使诗歌创造出全新的境界来。
在腐烂凋敝的旧社会里,墨客们深刻感到古诗的颓败之势,企图通过“诗界革命”冲击诗歌长久以来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方向,想要通过诗歌来反响新事物、新时期和新思想。
代表作有黄遵宪的《今别离》: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央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去,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从这首诗歌中可以看到,虽然有新事物的描写,但形式上还是没有分开古体诗词的束缚。
让古诗词走的更远的革命是口语文运动,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提倡用口语文取代文言文,这一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从文体特色上来看,最难实现这一转化的要数诗歌。古代诗歌有严格的规则限定,字数、对仗、押韵等等,为了更好的让反对派心折口服,口语文运动首先就拿诗歌开刀。
最早的口语文诗歌创作是胡适的《考试测验集》(1920年),放上个中一首大家感想熏染一下:
《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可以看到,脱胎于古诗词的口语文诗歌,“还带着裹足时期的血腥气”(胡适语),但这些考试测验对付文学史的意义是重大的,胡适之后一大批新诗作家呈现,他们有的从民歌民谣中汲取营养,如刘半农、刘大白;有的从西方资源中获取灵感,如周作人。
此后随着一批墨客在诗歌文体探索上的不断努力,才实现了古诗词的真正“放足”。
在这里附上我挺喜好的徐志摩的一首小诗《有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袭的波心——/你不必惊异,/更无须欢畅——/在转瞬间消灭了度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交知会时互放的光亮。
新诗新的传统确立之后,旧体诗就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了。当然,还是有人在创作古诗的,比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都是很精良的古体诗词。
但当新诗发展越来越成熟,这个自由的形式彷佛更适宜表现我们当下繁芜的生活,而古体诗离我们太远,我们也很少打仗专门的培训,以是它只能落到无人问津的尴尬田地了。
不用写
在口语文运动中,陈独秀提出了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培植夷易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培植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培植明了的、普通的社会文学。
这段标语实际上解释了悛改文学以来,我们的文学一个大的趋势,也便是向大众、向民间靠拢。这个趋势沿着左翼运动、《延安漫谈会上的讲话》不断深化,在市场化中走向媚俗,终极造成了我们现在的文学局势。
从平民,到公民,再到公民。“民”始终被不断推入文学活动的参与之中,艰涩的、难懂的古诗词、文言文早就没有了上风。
从内容表现来看,古体诗有严格的格律限定,并不适宜表现我们这个纷繁繁芜的时期,文言文透露出的文雅也与平实民间生活扞格难入。
古诗能描写出《小二黑结婚》里的辛辣诙谐的故事吗?古诗能表现出《创业史》、《红旗谱》中繁芜的阶级斗争吗?
古诗侧重抒怀,但大众每每更期待生动的叙事。而这些明明白话小说能带给我们更好的体验,那还写什么古诗呢?
王国维说,一代又一代之文学。实在严格意义上的“古诗”真正的黄金年代离我们已经良长远了,唐朝之后,“词”兴起,宋之后,“曲”又盛行起来,明清则是小说盛行。
可见“古诗”这一文体形式的衰落并不是由此时始的,乃至也不是由新文学始的,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逐步开始从顶峰滑落了。
我们这个时期,严格来说,是“古诗”由衰落走向消亡的时期,这很大一部分缘故原由是口语文的兴起。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伴随着口语文兴起,口语小说在上一世纪取得了很大的造诣。
而后,随着传媒的兴起,影视行业开始大展宏图,别说用文言文写的古诗了,就连口语文写的当代诗很多人都不一定读的下去。
不想写
小文所说的“不想写”,是与古人的“想写”相对的。对付大多数学生来说,古诗、文言文是令人头疼的存在,前一段韶光很火的《清平乐》,每次范仲淹、欧阳修一出场就有无数求他们少写古诗文的弹幕刷过,可见古诗文在广大学子面前的不讨喜。
但对付古人来说,“写诗”却是一件乐趣无穷的事情。一方面,写诗可以借机展露才华,另一方面,写诗对付他们来说本身便是一种娱乐活动。
古人的写诗可和我们现在的学生写作文不一样,并不是为了搪塞考试,以是在积极性主动性上胜了百倍。
《兰亭集序》里描写到集会写诗的场面:
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一群文人雅士坐在溪流旁,放一只羽觞让它顺着水流而下,在谁面前停下谁就饮酒作诗。在美景之中,与心腹们欢坐一堂,个中的惬意可想而知。
《红楼梦》中也提到,大不雅观园里的孩子们结诗社,他们可是兴致很高的,并不以此为愁,反而常常盼着集会作诗。
宝玉他们在外饮酒,娱乐活动也是行酒令,纯是为着玩乐。而且不仅宝玉黛玉这些少爷小姐会,就连那些丫鬟们也都能拟说一二。
想象着古人们那些风花雪月的场景,恐怕也是很有趣的。这种意见意义性便引发了他们的“想写”。而比拟我们现在,谁集会时还饮酒作诗?有什么娱乐活动便是饮酒聊黄段子,或者拿脱手机来开黑,吃完饭去KTV唱歌。
没有那样的文化环境了,当然也是由于现在的娱乐活动太丰富了,作诗便就由有趣变尴尬堪了。
当然,古人乐意写诗也是有实际意义的,文采好,名声旺,对仕途也是有所助益。兴许哪位达官显贵愿作伯乐,保不齐就飞黄腾达了。
可现在人写古诗,估计也没什么人看,诗歌的受众本来就小,何况古诗,读者估计没有几个。文学创作总是期待着被读者瞥见,没人看自然也就没什么动力了。
综上所述,古诗词虽然意境很美,但现在和往后都基本上不会再有复兴的可能了。新的文学传统已经确立,旧的文学传统如何卷土重来呢?
如果你喜好这篇笔墨,可以点赞和收藏哟!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小文互换!
~还可以关注作者,创造更多干系内容!
~小文在这里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