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
深夜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
故宅无此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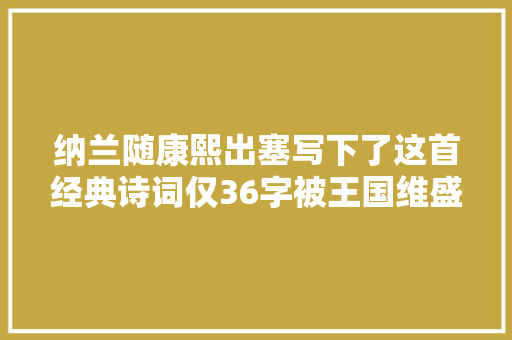
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对付这样一个男子,厚交若心腹,又浅淡如路人。分别的日子久了,莫说边幅,就连名字都已模糊不清。写一个人,便是在窥伺他的尘事,我们可以轻松的进入,却未必能够无缺归来。当你看过梦幻泡影,亲眼目睹繁华落幕、岁月倾覆,会恍然,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万物皆有期限,而这仓促流年,又留与你我期盼和追求,希望我们替它忍受世味尘沙。半闹事后,它舍不得收回,我们更不愿离开。
某个寒风霜雨的日子,为赋新词强说愁,填下一阙《长相思》。风儿吹,雨儿吹,岁月千番催又催。人老魂梦归。心灵一贯在流落,超越万里蓬山,阔别故土,无数至美的风景,遗落在身后,前方急着赶去的竟是故土不是新城。远方虽有青山溪水,渔樵老树,古城旧陌,酒肆离舍,终难敌过故乡的一尘一土。那些画航楼宇,古老雕窗,已有主人,去往的皆是客,待饭冷茶凉,终要转身。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苦处几人知?他是孤独的,自北宋往后,再无人如他这般登科极第,将词送至轻云端。他虽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可纵不雅观流水人间,浮云日暮,忙于跋涉的芸芸众生,也唯有纳兰的《饮水词》能够入枕长眠。我愿化作山脚的溪流,顺势而下,不去仰望山峰的高大巍峨,只守着几道至简的风景,循环遗世。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途中遇见的皆为过客,转身便是无期,无需提前拜别。清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纳兰随从康熙帝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二十三日出山海关。塞上风雪凄迷,景象苦寒,黄沙漫漫,不似京师的灵山秀水,琼楼玉宇。京师街道向晚里有那个秋水佳人,有昔日推杯饮酒的故人故友,而塞上却只见灯光煜煜,风雪呼啸。他多愁善感的心又怎禁得起狂风的席卷?
更令纳兰心痛的是,他不是那个身披盔甲,颠倒黑白,疆场点兵的将军,他纵有无上荣光也只能跟随在康熙身边,看莺歌燕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心杂则尘喧,犹如沼泽,让人泥足深陷,拼尽全力换来的,不是新的开始,而是剧终。他随康熙东巡,他希望他是康熙的有缘人,某一天转变主张,让他披甲上阵,亦或穿梭于朝堂,替他打理朝政。哪知,康熙盛世缺的不是忠良贤臣,而是消匿已久的那一半江南才华。唐有李白,七分月光,三分剑气,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宋有苏轼,大江东去,三国周郎,秀笔轻挥,便成千古风骚。沉寂数百年的光阴,须要一人将其惊艳,温顺岁月,规复昔日光芒,他是三生石选定的南国才子,他的笔下,充满了人间韵味,如鱼人水,心里有数。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
塞上荒凉,大漠孤烟,西风古道,留下的早已永恒,归去的尚无音讯。他的心系着天下苍生,也系着京师的家人。他想归去,可他不能,他是那个僧,他要渡的人还未觉醒,倘若离开,他将离楞伽隐士越来越远,离佛越来越远。塞上风景,透着一份粗狂和豪迈,它大气而不失落温润,它不幕人间富贵,却生来为众人争夺,让那些原来美满的家庭,从此分散东西。它本无错,众人亦无错,落于人间,策马扬尘,不过是各取所需,荣辱兴衰,善凶相守,才是凡尘。
冬日的小城,万物冷落,草木寂静,给曾经苍绿的岁月添了几分荒凉。喜极这样的烟雨日子、缠绵不休,它不嫌我容颜鬓老,只陪着我穿街弄巷,送往迎来。城中岁月,恰如青山不老,踏入明清烟雨,直抵秦时风霜。常说,我是为这世间的山水而流转尘凡;实在,我更是为琴音箫笛而不愿前往灵山。一曲终,聚散有时,深浅离合,心神浮荡。是静是动,如尘如幻,我自尘来,应向尘归。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次闻,大抵便是如此。贪念的,不过情深缘浅而已。
佛说,你是吉人,自有天相;你是善人,自有天助。梦幻人生,不管真实与否,都应努力活出自己的那一点阳光,不用回馈天下,留与每一段相遇,便是慈悲。交往来交往去,你能瞥见他人的天下,路人亦可以得见你的悲喜,我们本是心照不宣,又何须掩蔽,留与后人挖掘。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各有各的死活判词,你我亦不过是按照规定、过尽余生。只管如此,我们依旧在陌上相遇,当时只道是平凡。
“立时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安然。”
人生一世,白云苍狗,花月本无常,终是离多聚少,倘若故人还在,请牵住故人的手,不要轻易松开。花可以重开,人却不会再来。他离开了,没有消逝在塞上风雪,而是长眠在南国的病榻。他是人间愁肠客,他的孤独与寂寞,来自于苦病人生,更来自于高处不胜寒。他以惊才绝艳之姿横空出世,点亮了北宋往后的词坛,末了只留下一道孤影,镌刻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