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闲心去踏青赏花,有两个人,一是介子推,一是苏东坡,他们的“清明小长假”可就没那么好过。
介子推与寒食节
春秋期间,晋国公子重耳为了避骊姬之乱,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你这流亡的日子,有上顿没下顿,多难啊!
可是,所谓患难见真情,介子推老师便是个不离不弃的年夜大好人,他始终陪伴在重耳身边,乃至在快要冻饿而去世的时候,介子推“割股啖君”,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吃,才勉强活下来。
后来晋海内争平息,重耳同学在秦穆公的扶持下,成了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他肯定要重赏介子推啊,谁知道介子推却表示:说什么王权富贵,一点都不局气,您也甭劝,我啥也不要,只求带着老母亲归隐山林。说完也不管晋文公赞许不同意,拉着老娘告辞了。
晋文公不干啊,说你这么个人才,不为国效力,便是罪过罪过,于是他敕令烧山逼介子推出来。谁知道介子推便是头牛,犟得很,甘心被烧也不出山,然后就……嗝屁了。晋文公既惭愧又冲动,就敕令全国在介子推去世这天禁火、寒食,以表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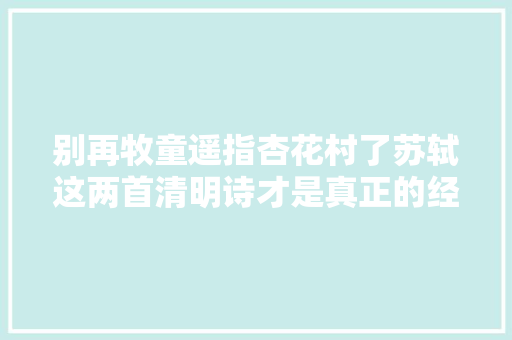
切实其实玄色诙谐!
后来,寒食节正式被确立,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以是在古代,寒食节和清明节,险些是并提的两个节日,说清明节,每每包含着寒食节,说寒食节,也一定包括了清明节。
苏轼的“天下第二行书”
书法爱好者都知道,天下有三大行书,老大毫无疑问是东晋王羲之老师的《兰亭集序》,二哥则是唐朝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三弟便是北宋苏轼的《寒食帖》。
元丰三年,苏轼从乌台诗案中捡回一条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用苏轼自己的话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啥意思呢,便是说从黄州开始,苏东坡的人生正式开挂。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我更乐意称之为“苏东坡年”,在这一年,苏东坡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下了《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下了前后《赤壁赋》,以及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
《寒食帖》在书法上的成绩我也谈不了,毕竟我一手字跟狗啃过似的,但作品内容我还是可以大言不惭一下的,由于《寒食帖》的内容是一组诗——《寒食雨二首》。
《寒食雨二首·其一》
这两首诗的感情都很悲观,第一首写寒食清明节前后的景象,是阴雨绵绵,非常萧瑟:
其一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开始已白。
被贬到黄州已经三年,生活处境依然困难,写到了惜春、苦雨,最有力的两个字是“萧瑟”,你知道,萧瑟都是用来形容秋日的,肃杀没有活气,而春天,特殊是清明节前后,是春天最有活力的时节,但苏东坡当时的心境,能看到的却只有“两月秋萧瑟”。
接下来“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苏东坡以海棠自喻,纵然掉进了泥污中,但依然保持着少年一样的小儿百姓之心。实在,如果足够理解苏轼就会知道,这位老哥对海棠是情有独钟的。
有一次在宴会上他写诗称颂一个小姐姐就有两句诗“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宛如彷佛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说这位叫李琪(一说李宜)的小姐姐虽然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她写过诗,就好比成都的杜甫老师,海棠虽然好,但他也从来没有在诗中写过海棠。这是把李琪比作海棠花,也因这一首即兴之作,让一个原来注定默默无闻的女孩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
苏轼刚到黄州时,寓居在定惠院,也写了许多随处颂扬的诗词,比如那句“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还有一首提到海棠的诗《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他这首诗极力赞颂海棠的品质,好家伙,把海棠夸得真是天上不生地上不长的,个中有句值得反复琢磨:“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他对海棠花产生了一种“同是天涯沉沦腐化人”的惺惺相惜之感,由于他苏东坡是一个壮志凌云的翩翩少年,当年第一次进京考试说自己和弟弟苏辙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沁园春》),何等斗志昂扬,可如今呢,从京官被贬到蛮荒之地,找谁说理去。而海棠呢,本来也不属于黄州的花,面前这几株花,也不知道是谁给移植过来的:“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你看吧,黄州是陋邦,成长海棠的西蜀是天府之国,把海棠这种清高的花,移植到黄州这样的陋邦,做这事儿的人,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这就差指着身份证号码骂了。
以是,苏轼说“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是对海棠花的感叹,你好端真个却被好事者移过来,和我一起沉沦腐化天涯,还要遭受风吹雨打,一夜之间就凋零殆尽,彷佛是被某个有力的人搬走了一样,这两句用了《庄子》的典故,不提。
末了“何殊病少年,病开始已白”,雨中的海棠花,就彷如一个病重的少年,等到病愈时,头发已经花白,老去。
这是苏东坡与海棠惺惺相惜,更是绝妙的自喻。
《寒食雨二首·其二》
其二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宅兆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去世灰吹不起。
第一首苏东坡还比较蕴藉,用海棠自喻,发发牢骚,可以想象,苏东坡当时在风雨中,趁着酒意,拿着羊毫,挥毫泼墨,越写心里越委曲,越写感情越激动,写到末了,他在蕴藉中爆发,终于发泄出了三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苦闷。
这首诗同样先写雨,这雨势就大了,挡也挡不住,所住的小屋在狂风暴雨中,就像一叶飘零的小舟,而屋里也是“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全体家里就没点好东西,厨房都是空的,柴火都是湿的,这是饥寒交迫,极度困窘。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被贬黄州之前的苏东坡,哪里过过这样的日子啊?你看他往年的清明节是咋样的,“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蝶恋花》),哪怕是客居他乡,也是风风光光的;或者就算心情不太俏丽,至少也有朋友相伴“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徐使君分新火》)。
两相比拟,切实其实要了亲命了。更要命的却还在后面,他“那知是寒食”,过得连日子都忘了,若何才会把日子都忘了呢,你要每天有事儿做,要上班上学,肯定不会忘了星期几,只有当你无所事事,身边又无人关心,只有孤零零一个人摧残浪费蹂躏生命的时候,才会把日子都忘了,苏东坡看着自己面前的生活,这才发出了“那知是寒食”的悲鸣。
直到“但见乌衔纸”,瞥见乌鸦衔着烧过的纸钱,才恍然大悟,由于前面说了,古代的寒食、清明节险些可以等同于一个节日,前后也只相差一天,以是虽然只是寒食,还没有正式到清明节当天,人们已经开始烧纸扫墓,敬拜先人了。
看到别人家祭祖,再看看自己,想要辅佐君王吧,“君门深九重”,天子老爷子在九重天上,自己何德何能?想要祭祖吧,“宅兆在万里”,先人的坟茔都在万里之外,有心无力。
想到这里,苏东坡也不由得一边写一边哭,已经心如去世灰,再也燃不起来了。末了两句分别用了阮籍“途穷之哭”和韩安国“去世灰复燃”的典故,不提。
这第二首诗,总体上比第一首的感情更直接,也更剧烈,内心是绝望的,以是言辞是激烈的,虽然话说是“去世灰吹不起”,但我们知道,苏轼是打不去世的小强,过几天他又蹦跶起来了,完备不用担心。
还有中间这几句,不仅表现了苏轼在当下的境遇和心境,同时在故意无意中,也向后人展现了北宋期间人们寒食、清明节的节日风尚,还是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