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麟州城有一座标志性建筑——红楼,随着麟州故城升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杨业故里即是麟州被学术界所确认,麟州红楼以及文彦博(1006—1097)的红楼诗自然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对此作一番深入的磋商。
最早提及红楼的就数文彦博的红楼诗了,它刊载于道光《神木县志》中,内容如下:
文彦博 麟州知郡作坊以彦博昔年所题红楼拙诗刻石,复以墨本见寄,辄成五十六字致谢,且寄怀旧之意云尔
昔年持斧按边州,闲上高城久驻留。曾见兵锋逾白草,偶题诗句在红楼(原注:楼在城上,对白草坪)。控弦挽粟成陈事,缓带投壶忆旧游。狂斐更烦金石刻,腼颜多谢镇西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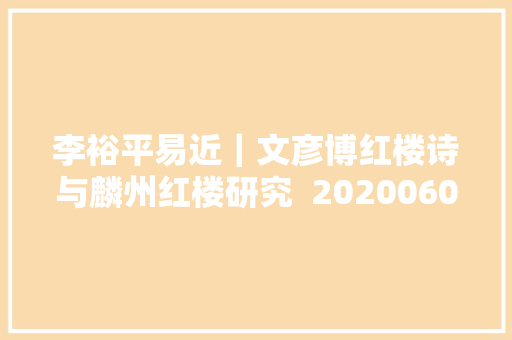
在这里,须要研究几个问题:一、道光上距文彦博800来年,怎么证明这首诗是真实的而不是假造的?二、文彦博何以对麟州红楼情有独钟?三、红楼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的,是谁为他刻到石头上去的?四、红楼的建筑韶光及详细方位。
一、文彦博的红楼诗来源于宋代石刻
我在读到此诗时,曾查检现存的《文潞公函集》,创造集中未收,于是对它的内容作了一番稽核。2首先,诗的内容与文彦博的行踪符合,诗称“昔年持斧按边州”,他确实到过麟州,康定元年(1040),文彦博出任河东路转运副使,曾前往麟州,开通运粮之路,补救了被西夏包围一月多的麟州。其次,诗中提及的白草、红楼符合当时的地理名称。三、麟州知郡作坊符合北宋职官制度。如果是人为造假,一定有其造假的缘故原由,如为地方人士锦上添花,但文彦博并非麟州人。也有的是为祖上增长光环,尤其在家谱中,而此诗并无吹捧家属之处。作假一定会露出漏洞,如把别人的诗偷梁换柱,而此诗没有与其他诗内容相同之处。后人作假常常会违背历史,官名、地名与历史不符,而本诗完备符合。基于上述情由,我把它收到《全宋诗补》中,在《文史》2001年第57辑上揭橥,以填补北京大学出版的《全宋诗》之不敷。
虽然通过上述考证,可以基本认定,但此诗的来历未能弄清,究竟不能放心引用。我遍查宋、元、明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这首诗,《道光县志》究竟是从哪里得到此诗的?
最近,我从比道光本早的清代抄本《神木县志》3中找到了答案。它所收的内容要比道光本详细,兹录于下。(道光本所无之字,用粗黑体表示)
丞相潞公诗
彦博丞(按应作承)知郡作坊以彦博往年所题红楼拙诗刻石,复以墨本见寄,辄成五十六言致谢,且寄怀旧之意尔:
昔年持斧按边州,闲上高城久驻留。曾见兵锋逾白草,偶题诗句在红楼(原注:楼在城上,俯窟野川,正对白草坪)。(按强)[控弦]挽粟成陈事,缓带投壶忆旧游(原注:皆昔日新秦事也)。狂斐更烦金石刻,腼颜多谢镇西侯。
嘉祐六年十月十三日立。
道光本县志序中提到过这个抄本,显然,道光本是抄自这个更早的抄本的,可惜的是,传抄时它把最关键的内容删除了。这便是末了一句话,它解释诗刻于嘉祐六年(1061)十月十三日立的石碑上,县志所收之诗是从当时保存的碑上抄来的,是日然是最可靠的。
这个清抄本抄于什么年代?它所根据的原稿纂修于何时?
从内容看,四卷各目基本上都记载到康熙为止。从避讳角度看,书中未避雍正之祯及乾隆天子弘历之讳,应抄于康熙时。唯卷二“东协副将”条额外增加了三人:
雷世杰,厢白旗人,康熙五十五年任。
傅泽深,厢黄旗人,康熙五十七年任。
周起凤,陕西长安人,雍正四年任。劝政洁己,恤兵爱民,抚绥边方,宽严并济,历升延绥镇总兵。
但周起凤之前还有一人,却漏录了:“孙继宗,固远人,雍正二年任。”显然这是全书抄成后,至雍正四、五年间又随意添补的,而其他各卷各条都没有再添雍正时的人和事。
之以是说它是抄本而不是原稿本,还由于书中常常有抄错的地方,有些是低级缺点,如范仲淹的“范”,写成“花”,“沧州”误写成“仓州”,“或者”的“或”写成“域”,若是编者的原稿,决不会涌现此类失落误。
卷二“邑侯(即县令)”条最晚记到“贺有章,贵州黔西州人,由举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任,命题课士,振兴学校,省刑薄敛,抚恤穷黎,行取户部主事,历升山东粮道。”未记康熙五十九年(1720)任知县的刘荫枢。
“广文”条记到:“赵巨,西安府三原人,由岁贡康熙四十九年任。优礼斯文,重修学署。”未记康熙五十五年任的胡继昌。
卷二“职官·不雅观察”条最晚记到:“罗景,字星瞻,襄平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修文庙以兴学,开边地以利民,严捕盗贼,禁止赌钱,宣讲圣谕,设置关厢,教民树植,凡有益于地方者,无不加意立行,各类善政,不胜指屈,将来政治,未有涯云。”
凡此,可以看出,县志修撰的韶光应在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间。它比道光本县志要早130年。此抄本应命名为“康熙《神木县志》”,今存清抄本是根据原稿本抄的,抄手水平不高,故时有抄错处,抄的韶光应在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间,此后,抄者在雍正四年时又补充了3条内容。
卷四“艺文篇”引言说:“邑久文献无征,隋、唐而上,远不可稽,晚世遗文付诸石刻者,亦皆藓剥弗全,间有所作,亦多出于方家之手,今录其仅存者多少篇”。据此,唐以前的石刻当时已无法看到,宋往后尚有所保存,文彦博红楼诗当录自石刻,康熙时此石刻尚在世。至于现在是否尚在,就得靠考古发掘去证明了。
以上解释这首诗来源于宋代的石刻,是完备可靠的。
从文彦博诗中,知王庆民在刻此诗前已经刻了文彦博第一次题红楼的诗,按理说,康熙时也能见到,不知为何没有收录?大概由于该碑已残、字迹不清而未录?但愿有朝一日能重见天日,纵然已残,也能供应一些新的信息,供大家研究。
二、文彦博何以对麟州红楼情有独钟?
文彦博何以对麟州红楼情有独钟?由于他与父亲文洎都曾对这座计策重镇作出过贡献。
麟州在北宋时有着分外的地位。它的西边70里以外即是西夏的领地,以南今绥德县也归西夏统领,它的北边今鄂尔都斯一带则属契丹领地。北宋霸占的麟州和府州,属河东路统领,首府为太原。西夏竭力想盘踞它,这样就可直接威胁太原,进而入侵中原。北宋保有它,则可以与延州(今延安)两路夹攻西夏,使之腹背受敌。但代价很大,北宋必须在麟州驻扎大量军队,并且必须常常从太原运输大量的物资,而道路十分难走,尤其是府州到麟州中间有一百几十里山路,随时会受到夏兵的打击,甚至有些朝廷要员主见放弃麟州,而有识之士则主见坚守。
文彦博的父亲文洎(?—1037),介休人,很有计策头脑。景祐四年(1037)出任河东转运使,这一职务在当时是河东路的最高主座,不但有运输粮草等任务,还有权监察一起官员。他一上任,就十分关心麟州,他知道麟州城易守难攻,但必须担保有充足的物资,否则就难以坚守了,而原有的道路迂回曲折,常常被西夏拦截。文洎经由调查,理解到唐代的道路比本日更方便,便决定重开唐代故道,可惜,刚动手就因操劳过度而于同年玄月去世了4。
文彦博字寛夫,进士出身。曾先后三次出任宰相,第一次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至皇祐三年(1051)十月。第二次至和二年(1055)六月至嘉祐三年(1058)六月。第三次元祐元年(1086)四月至五年仲春。享年九十二岁,是北宋的元老重臣。《宋史》卷313有传。
文彦博在父亲去世三年后,即康定元年(1040)夏,出任河东路转运副使。他可以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了,心情十分高兴,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某天圣四年(1026)叨充乡赋,明道二年(1033)夏假副车于本郡,今年夏沗外计于本道,实嗣世职(前此三年,先大夫为河东转运使)。八月行部,率遵故常,乡老欢迎,邀留累日,徘徊旧地,追惟畴曩,因成拙诗二章,题于行署。
鄙人惟侍髙门庆,奕世皆为外计臣。乡老相逢频教我,效忠思孝报君亲。
昔年乡赋议兴贤,曾接诸君砚席间。屈指岁华逾一纪,锦衣怀绶过稽山5。
他在八月到麟州一带察看,以最快速率完成父亲未竟之业,打通了运送粮草的道路,给麟州运去了充足的粮草。第二年,西夏主元昊亲自统帅数万大军围攻麟州,整整十天,劳而无功,只好解围而去,转攻府州,又损兵折将而退。次年,文彦博晋升为河东路都转运使6。
《宋会要》方域21之6对其父子的作为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庆历元年八月,麟州言,元昊攻围州城逾月。麟、府皆在河外,因山险。初,转运使文洎以麟州饷道回远,军食不敷,乃按唐张说尝领并州兵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党项于银城,大破之,遂奏置麟州,此为河外之直道。自折德扆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舟楫邮商,以便府人,遂为麟之别路。故河关路废而弗治,洎将复之而卒。其后子彦博为副使7,遂通道银城,而州有积粟可守。故元昊知城中有备,解围而去。复兵攻府州,城中官军六千一百余人,居民亦习兵善战。城东、南各有水门,崖壁峭绝,下临大河。崖腹有微径,贼攀缘石壁,鱼贯而前,城上矢石乱下,贼去世伤殆尽。攻城北,而士卒力战,伤者一千余人,贼乃引退。”
《宋史》卷313 、页10258《文彦博传》:“以直史馆为河东转运副使。麟州饷道回远,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废弗治,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将复之,未及而卒。彦博嗣成父志,益储粟。元昊来寇,围城旬日,知有备,解去。迁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
文彦博红楼诗中提到“昔年持斧按边州,闲上高城久驻留。”解释他在麟州待过相称长的韶光,为防守事宜费过不少心血。又说“缓带投壶忆旧游”,原注:“皆昔日新秦事也。”“投壶”是古代军中的一种竞赛性的运动,每人手持箭,把它投到壶中,谁投进的多谁得胜。解释在事情之余,文氏在此交了不少朋友,时时一起上红楼饮酒欢聚游戏。
三、红楼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的 ,是谁为他刻到石头上去的?
文彦博的红楼诗写于何时?,从诗刻石的韶光,可知应在嘉祐六年十月前不久。而该诗又明确提到在此前曾作题红楼诗,由此可知,文彦博实际上前后作了两首红楼诗,第一首红楼诗是直接题写在楼上的,一定是他赴麟州之时所作,韶光应在康定元年(1040)。两首诗前后相隔了21年。作两诗时的身份地位则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前者仅是河东转运副使,后者已是出任过两任宰相的元老重臣了。在红楼上题诗的数量一定不少,但后来升为宰相的只有文彦博一人。把它从浩瀚的红楼诗中挑选出刻在石碑上,有助于提高红楼的身价,这大概便是麟州知州刻石并把拓本寄赠给文彦博的缘故原由。
为文彦博诗刻石的是谁?从他的诗题可以知道,是“知郡作坊”,所谓“知郡”便是麟州知州,作坊即作坊使,是这位知州附带的官衔,正七品。历任麟州知州中带这一官衔的只有王庆民。
嘉祐四年(1059)十仲春乙亥(14日),知麟州王庆民奏上麟府二州图8。得到天子褒奖,十仲春十七日,欧阳修起草了《赐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庆民奖谕敕书》,全文如下:
敕王庆民:省所奏准密院札子节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绢图一壁并序目二册诣阙上进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畧,然后可以策胜败之筭,运奇正之谋,尔以材武之资,有明敏之识,自膺简寄出守边封,而能周知山川险易之形,历览亭障屯防之要,列为凡目,粲尔(一作可)条陈,不惟指掌于披图,足以因时而制变,遽兹来上,深体乃忠,省阅以还,叹嘉曷已,故兹奬谕,想宜知悉9。
在敕文中夸奖王庆民不仅有“材武之资”,而且有“明敏之识”,他是在嘉祐二年(1057)宋军在麟州城外被西夏打得大败,原知州武戡被罢官10后上任的,一贯担当到熙宁三年(1070)11,韶光长达14年,是任期最长的麟州知州。熙宁四年正月,又连续担当管勾麟府路军马之职12,成为麟府军队的最高统帅,往后转任知冀州13,熙宁七年后去世14。王庆民,《宋史》中并没有立传,生卒年也难以考清,但他无愧为守卫麟州的元勋,在麟州史上是应该有他一席之位的。
四、红楼的建筑韶光及详细方位
红楼建于何时?至迟在康定元年(1040)文彦博登上红楼题诗前已经存在,离今至少有970余年了。其最初建筑韶光可能早到唐朝。麟州,初置于开元十二年(724),仅二年就废了,此时不太可能建楼。天宝元年(742)复置麟州。15貞元二年(786)、十七年(801),麟州两次被吐蕃攻陷,“夷其城郭”16,建楼韶光最早也应在801年之后,详细何时,尚待创造新资料,再作进一步考证。
关于红楼的情形,文彦博在诗中有如下的记载:“曾见兵锋逾白草,偶题诗句在红楼”,自注:“楼在城上,俯窟野川,正对白草坪。”解释楼是建在城墙上的,它可以俯瞰窟野河,了望白草坪。白草坪也作白草平,在屈野河西山上,距麟州城十五里以上。17红楼应在麟州的最高点。
(来源:杨鸿勋体例的宋麟州城(杨家城)原状推测图集)
麟州城,经近年来的考古调查,有东城、西城和紫锦城,红楼在哪个城上?
历史上有三种记载:
一、西城红楼
《宋史》卷485、页14001《夏国传》:初,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红楼,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讹龎,岁东侵不已……嘉祐二年,遂团兵宿境上,逮三月増至数万人,守将敛兵弗与战。知麟州武戡筑堡于河西,以为保障。役既兴,戡率将吏往按视,遇夏人于沙鼠浪……众大溃。
按:城上短墙为睥睨。枕,紧靠之意,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紅樓,这是说在麟州西城上有紧靠短墙的建筑红楼。也便是说它是建筑在城墙上,而不是城门上的。
二、衙城紅樓
《宋史》卷326、页10522《郭恩传》:郭恩,开封人……徙并、代州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夏人岁侵屈野河西池,至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经畧使龎籍毎戒邉将,敛兵河东毋与战。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后去。通判并州司马光行邉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寇迹。是时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筑一堡为候望,又与光议曰:乘敌去,出不虞可更増二堡,以据其地。请还白经畧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过二旬,壁垒可城。然后废横戎、临砦二堡,撤其楼橹,徙其甲兵,以实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
《长编》卷186、页4477:嘉祐二年五月庚辰,崇仪使、并代钤辖、管勾麟府军马郭恩与夏人战于断道坞,去世之。……初,夏人岁侵屈野河西地,至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是岁正月,没藏讹尨领兵至境上,比及三月,稍益至数万人。又自鄜延以北发民耕牛,计欲尽耕屈野河西之田……于是籍檄通判并州司马光行边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敌迹。时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筑一堡,为候望,又与光议曰:乘敌去,出不虞更増二堡,以据其地,可使敌不复侵耕。请还白经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过二旬,壁垒可成。然后废横戎、临塞二堡,撤其楼橹,徙其甲兵,以实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
三、衙门红楼
《隆平集》卷19:郭恩……官崇仪使、并代钤辖、管句麟府军马事。初,夏人岁侵屈野河地,至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经略使庞籍戒边将勿与战,月余,食尽去,如是屡矣。是岁正月出屯,三月始去。并州通判司马光行边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寇迹,时知麟府(民按:此为衍文)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筑一堡,又与光议,乘寇之去,出其不虞,别创二堡,据其地,使不得耕,功毕则废横戎、临塞二堡,徙兵实新堡,列烽燧,自衙门红楼下视其地如指掌,堡成,三十里外田,宼必不敢耕矣。
以上二、三说,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即嘉祐二年郭恩麟州之战,差别仅在于详略不同,《隆平集》最略,《长编》较详,它们应来自麟州或太原的奏章。以写作韶光而言,《隆平集》最早,作于北宋,《长编》次之,作于南宋。按说,韶光早的可信度大些。但从版本看,《长编》最早,有宋本,《宋史》为元刻本,《隆平集》仅有明刻本和清抄本,后者缺点颇多,如这一段笔墨中,“知麟府州武戡”中的“府”字显然是衍文,古代并没有“麟府州”这一地名,如果理解为麟州和府州,也不可能,由于武戡从来没有兼任过知府州,宋代府州知州全部由折家世袭,嘉祐二年时知府州的是折继祖。再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红楼是建在城墙上,而不在城门上。因此“衙门”很可能是“衙城”之误。这样,以上三种可能实际上可归并为一、二两种。
衙城也称牙城,是州主座的住宅所在地。唐代的州城一样平常由三套城墙组成,最里面的是衙城,表面套一层内城,再表面又套一层称为罗城。这种把衙城牢牢地包在最里面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障领导的安全。如郓州、扬州城即是如此。18麟州由于建在山上,受地形的限定,无法一个套一个,只能建成相互连接的三个城,今称为东城、西城和紫锦城,史籍中只提到衙城和西城,但既然有西城,必定有东城,本日东、西城的叫法是符合实际的,而所谓紫锦城,该当根据文献的记载定名为衙城。
在唐代衙城上建楼是常见的,如閬州衙城西南角即建有碧玉楼。19以是,麟州衙城上建有红楼也是很正常的。
如何探求红楼的今址?它应该知足两个条件。一、从文献和文彦博诗可以看出,红楼应在麟州城内阵势最高处。二、位置是在衙城、西城。
目前可供选择的城墙高地有两处,一在衙城东南,二在衙城北。
按照第一个条件衡量,前者阵势最高,自然可能性最大,有人推测它便是红楼的所在地,我曾登上去了望,从气势看,也以为很像。但后者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如果真的建有红楼,其高度就可能超过前者。
按照第二个条件衡量,既可以称作衙城红楼、也可以作西城红楼,前者就不好称作西城红楼了,而后者则完备符合,对付衙城而言,是在衙城的北城墙上,可称为衙城红楼,而同一道墙对西城而言,又是西城的南城墙,因此,也可以称为西城红楼。从这一点看,后者可能性更大。
但谈论到此,还不能就此认定,红楼就属后者。这里还牵扯到如何认识东、西城与衙城之间的关系。按当时的制度,衙城和东、西城,不应视作并列关系,东、西城该当被看作内城和罗城,衙城是被套在内城中的,到底谁是内城、谁是罗城,存在以下两种可能性:
1、东城可能是包括衙城在内的内城,而西城则可能相称于罗城。如此说成立,红楼应在衙城北的高地。
2、西城实际上是内城,即它是将衙城包含在内的,则衙城的南墙也可视为西城的南墙,那么前者的可能性又超过了后者。
如何终极办理上述问题,尚须借助考古手段。其一,分清三城建筑的早晚。一样平常说,衙城最早,内城次之,罗城最晚。其二,探求红楼的基址、柱础、瓦当之类的遗物。
此外,不能打消还有第三种可能,有一个已经证明的事情,府州在被西夏盘踞后,西夏人出于折半家的痛恨,将折家墓地彻底毁掉。同样,西夏人出于对麟州的痛恨,在盘踞州城后,也会将红楼彻底革除,如果真是这样,大概红楼在这两处高地以外的某个地点了。当然,纵然摧毁,遗物还会有的,只是办理问题的难度又增加了许多。
到底哪一种可能符合事实,有待考古发掘找到更确切证据去办理。
参 考 文 献:
1 道光《神木县志》卷8《艺文志》下,1982年标点注释本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以下简称《长编》),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21之6,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3 清代抄本《神木县志》,1970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4 宋张刍《宋故奉宁军节度推官承奉郎试大理评事知乾州奉天县事文府君(彦若)墓志铭》。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98,民国十四年希古楼刻本
5 宋文彦博《文潞公函集》卷4,1986年山西公民出版社影印山右丛书本
6 《长编》卷137、页3279:庆历二年六月乙未,河北转运使、吏部员外郎、史馆修撰文彦博为天章阁待制、本路都转运使。
7 “彦博”,原作“产恃”,据《长编》卷133改。
8 宋王应麟《玉海》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
9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函集》卷88,四部丛刊本
10 《宋会要》职官65之15: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知麟州、六宅使、带御东西武戡革职,江州编管。
11 《宋会要》兵28之8:熙宁三年七月十八日,诏河东经略司已严戒知麟州王庆民,如西贼犯境,即令诸城寨相度有险可恃者,专为清夜自守之计。
12 《长编》卷219、页5324:熙宁四年春正月癸卯,诏王庆民依旧专管勾麟府路军马。
13 《长编》卷250、页6091:熈宁七年仲春丁丑,知冀州王庆民言,捕得骁捷第三指挥作过兵士八人……赐庆民敕书奨谕焉。
1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6,中华书局1986年
15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16 《資治通鑑》卷232、页7475,卷236、页7597。
17 《长编》卷133、页3163:庆历元年八月戊子,麟州言:元昊以前月戊辰,攻围州城。是月乙酉,踰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距城十五里按军。
1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1、页7764:元和十四年仲春,“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子城已洞开,惟牙城拒守。”胡三省注:“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卫节度使居宅,谓之牙城。”《资治通鉴》卷266、页8667:开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扬州杨)渥父行密之世,有亲军数千营于牙城之内。”胡三省注:“蜀注曰:古者军行有牙,尊者所在,后人因以所治为衙,曰牙城,即衙城也。”又注曰:“牙者,旗名”。
19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67、页1174阆州条,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
作者简介
李裕民,宋史学家。1940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崇德县崇福镇(今属桐乡市),曾任山西大学历史所副所长,民进中心委员、民进山西省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兼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山西省高校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现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与国学院特聘研究员,浙江省重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央兼职研究员及学术委员。
◆ 指挥部组织召开《麟州故城保护方案》报审方案申报请示会
◆ 马 语 | 千年河山,风卷云未散
◆ 指挥部召开《杨家城文化旅游区总体方案》申报请示会
作 者:李裕民
编 辑:郭少艳 折彩瑞
审 核:马乐兵 姜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