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的卷收形式和空间长度有关,和绘画背后的美学主见也有关。
-里耶秦简-
立轴形式的绘画,悬吊在墙壁上,是一个完全的绘画空间,但是,在收卷和展放时绘画空间的改变,是西方硬框式绘画所没有的。这种绘画空间的卷收与展放,一样平常人只是从收藏的方便来思考,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正好是中国韶光与空间不雅观念的反响,一种延续的、展开的、无限的、流动的时空不雅观念,处处主宰着艺术形式末了形成的面貌。
这种延续的、展开的无限流动的不雅观念,在长卷形式的绘画中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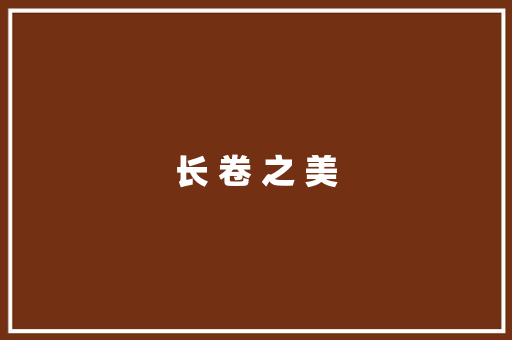
长卷的绘画形式该当成形于早期的竹简,以韦编竹,连贯成卷,是中国展开与卷收形式的较夙兴源。
-银雀山汉墓竹简-
► 东汉和林格尔墓葬中的壁画,由于描写墓葬主人的生平,有连续展开性的格局,但是由于是壁画,只是长条形的固定格式而已。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卷》,《列女传图卷》,虽然都是摹本,依然保留了当时长卷的绘画形式。
-女史箴图卷-
► 《女史箴》与《列女传图卷》是故事性的分段连环图形式,每一段旁有笔墨解释,构造上虽然有呼应,但是独立性很高。
-列女仁智图卷(宋摹)-
► 《洛神赋》的连续性非常强,山水在人物运动的关系间扮演着十分主要的角色,曹植与洛神对望,中间隔着大段的山水,比例上正好是前一组人物实体在“虚”上的对照,而背景内翔远而去的龙鸟则展开了第三度空间的辽阔性。这件宋摹本如果虔诚保留了原作的构图布局,那么在晋代,从连环图式的长卷转变为真正具有连接呼应浸染的长卷,顾恺之应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洛神赋图卷-
► 稍后于顾恺之,北方从印度传来的宗教变相图,更加强了中国长卷性绘画的发展。
敦煌二五七窟北魏的《鹿王本生变相图》是“北魏本生故事画中最早的横卷连环画之一”。这件壁画的构图形式非常特殊,“故事情节从两端向中间发展形成高潮而结束”。中国本土的长卷,险些一律是由右向左发展,视觉开始于右端,结束于左端。在这由右向左发展的空间中,画家自然必须考虑到卷轴展开的速率与方向。中国的长卷画,从来不是完备放开来陈设的。也便是说,不雅观赏者与长卷的内容,不会在同一个韶光内做完备的打仗。在画卷展开的过程中,不雅观赏者一壁展放左手的画卷,一壁收卷右手的起始部分。右手收卷着过去的视觉,左手展放着未来。在收卷与展放之间,勾留在我们视觉前的年夜约是一公尺旁边的长度,即是两手伸开的间隔罢。这大约一公尺旁边的长度,在与我们视觉打仗过程中,有千万种不同的变革,它分分秒秒在移动,和前后发生着组合上的各种新的可能。
-鹿王本生变相图-
► 韩混《五牛图》,看来各自独立,但是行进的变革颇有趣。一开始是遵照由右向左的方向缓缓进行,到了中心第三头牛,忽然成为正面,行进的方向与速率都中止了,仿佛向画面外的不雅观赏者一照面,画面独立成静止的镜框式的舞台。然后,到第四头牛,一方面保持原有行进的方向,连续由右向左发展,另一方面却利用牛的转头,造成一个迁移转变的空间,经由这一迁移转变,才又规复结尾第五头牛连续由右向左的暗示。
-五牛图-
► 以敦煌的资料来看,佛教故事画影响出来的变相图对中国长卷形式绘画的完成有莫大助力。第二九六窟,北周《五百贼归佛分缘》,长427厘米,高46厘米;北周二九O窟的《佛传图》长432.5厘米,高82厘米,而这82厘米中又横剖为三段,以是实际上的长度应是432.5厘米的三倍长。北周四二八窟的《萨堙那太子舍身饲虎》长417厘米,高64厘米。有名的晚唐一五六窟壁画《张议潮出行图》及《宋国河内郡宋氏夫人出行图》,均长达855厘米。
-五百贼归佛分缘-
-五百贼归佛分缘二-
-五百贼归佛分缘三-
-五百贼归佛分缘四-
-张议潮出行图-
-张议潮出行图二-
-张议潮出行图三-
-张议潮出行图四-
► 这些佛教的故事经变图,与中国的长卷形式是一齐发展起来的,但是,壁画受制于建筑空间,自然在时空的转换上不及纸帛类可以卷收与展放的长卷绘画。
推测为南宋人摹本的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在长卷绘画的构造上是值得把稳的精品。全卷长333.5厘米,高28.7厘米。在333.5厘米的长度中,分为五个段落,每一段落约长60厘米。
► 在第一段中,以床榻为起始。床只露一角,在画卷右上方,被褥不整,床上置一琵琶,拉开了夜宴的序幕。
由于床只露一角,不刻意把这个“开始”当一个独立的部分来看待,彷佛是一个无限韶光中有时被截出来的一个段落。
► 画卷展开,随着最右方榻上的主人韩熙载及状元郎粲,及榻边侍女,三人视线重复的暗示,使画卷有连忙展开的希望。超越摆满果点的几案,画卷下方的来宾,仍和开始的三个人保持同一视线,加强由右向左的行进方向。但是,画卷上方的教坊副使李家明,双手按拍而合,身体已转向正面,使行进的速率发生变革。经由这一停顿,左边再次涌现的是一组五个人物,险些是两条平行线,身体一律朝向右方,与卷首的韩熙载、郎粲呼应。但是,他们的面部仍旧转向左方,重复地把视线的行进方向落在这一段的焦点人物——弹琵琶的女子身上,女子背后是一壁大的立屏,立屏后露出半身的女子,在嘹看全场,第一段落在这屏后人物的嘹看中结束。
第一段,从床榻开始到立屏结束,奥妙地用了大型的物件做画面场景的分割。这一段,可以做一幅独立的绘画欣赏,但是,又必须加入到全体长卷的发展中去。独立来看,类似西方绘画的不雅观察,画面以李家明为视觉中点,视线的焦点集中在画面左下方弹琵琶的女子身上。
► 若以中国长卷的构造来剖析,在这暂时使人停滞流连的静止画面中,韶光向前的暗示仍在进行,右手要卷收,左手要展放,统统的美景、人物、声色之好,统统暂时的栖止、眷恋,都不能违反那“逝者如此”的韶光的进程。
在卷收与展放中,有对逝去的不舍留连,有对新展现事物的欣喜惊异,韶光流逝的不雅观念,繁华与幻灭的对置,便在这长卷形式中逐一深人中国人的生命之中了。
《夜宴图》的第二段,隔着立屏,是另一个场景。韩熙载换了轻便的服装,手持鼓锤,正在击打一壁红漆如桶的羯鼓,合营着左方名妓王屋山的六么舞。
► 这一段画面上的八个人物,环绕着击鼓和舞蹈的故事中央,仍旧以身体和视线的方向,暗示着行进的内在韶光。惟一的例外是僧德明,他一身和尚打扮,背向王屋山的舞蹈,视线又不在韩熙载的击鼓上,他陷入沉思冥想之中,仿佛与四周的声色无关,使画卷的行进节奏发生了阻碍,是对生命更深的冥想,忽然置身于韶光与空间之外。
在一样平常习气的二段与三段之间,并没有类似立屏隔开的做法。那面向右边拍手击节的女子彷佛是二段的结尾,用身体的朝向来间隔。
接下来,得手捧温羽觞盘的侍女涌现,进入第三段落。奥妙的是,这二段到三段之间,只是空缺。空缺成为中国长卷绘画精彩的部分,这“空缺”并不是“没有”,它是老庄思想“无用之用”一脉相承的嫡裔,它是对韶光与空间更深刻的思考,宋元往后,在中国艺术中发生了莫大的影响。
► 《夜宴图》第二段到第三段的转换,不借助任何实物的间隔,这种空缺的运用,提醒了我们,在真正的韶光之中,并没有段落,床榻与立屏都是假相,我们常用的秒、分、时、日、月、年、世纪,也都是假相。韶光本身,是一个汨汨无止境的流逝过程罢。这种韶光与空间的转换,在此后山水画中发展得更为奥妙,在中国新起的舞台艺术、园林艺术、章回小说中也在在找得到例证。
《夜宴图》第三段从捧温羽觞盘的侍女开始,弹琵琶的女子掮着琵琶由右向左行走。弹琵琶的女子在第一段是视点中央,在第三段,曲终人散,跳过第二段,接到第一段,韶光被错置了。十分具象征性的床榻再次涌现,仍旧是被褥不整,彷佛这缓缓走来的女子正准备着把琵琶横置床上,这个符号,使我们想起卷首的床榻与琵琶,当同一个形象第二次涌现,便有了象征的意义,而最有趣的是,在韶光上,是与我们逻辑的理解相颠倒的。这种韶光叠压,前后错置的感想熏染,更靠近我们真正的意识状态,是长卷绘画逐渐形成的一大特色。
► 原来,连由右向左一贯线的韶光方向,也是假设而已。在卷收的过程中,韶光在同一个轴心上竟然不断叠压重复,形成一个不断循环的无数圆。在圆形上,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或者说,在圆上,每一点都可以是开始,也可以是结束。
韩熙载坐在榻上,重新披上衣服,彷佛刚击完鼓,正在洗手,五位侍女在侧环抱。他面朝右上,与第二段正在击鼓的韩熙载面面相觑,彷佛在一霎光阴,忽然瞥见了另一个自己,时空的限定完备被毁坏了,人可以出入于任何韶光与空间之中,无有阻碍。中国的长卷绘画发展至此,连强硬的划分第二段与第三段也只是谈论上的不得已,真正长卷绘画企图达成的时空正是一个浑然不可分的时空,企图把我们从假相的、被分割的韶光与空间中救拔出来,达于真正自由逍遥之境。庄子《齐物论》中提出的“不知周之梦为胡蝶欤?胡蝶之梦为周欤?”
► 正是这种时空不雅观在中国艺术上大放异彩的先声罢!
利用床榻做间隔,进入第四段,韩熙载卸去了外衣,袒腹而坐,一手挥扇,画面正中心是五位弄笛吹箫的女子,李家明执檀板合拍。五位女子三人面朝右,二人面向左,三二错置,使画面造成扇形伸开的形式,使不雅观赏者视觉固定静止,是正面视觉的焦点。旁边两侧则由李家明与韩熙载相互呼应,构成一个可以独立的段落。
► 李家明后又张一立屏,屏侧一男子身体朝向右方,是属于第四段场景中的人物,但是他头又转向左方,预报了第五段的开始。这是长卷绘画中转换时空的手腕,这种角色十分靠近传统戏剧中的“捡场”,他们彷佛与主题无关,面无表情地走出来,又像是韶光本身,整顿残局,为下一个场景支配新的空间。
► 第五段是一个结尾,七个人物中六个朝向右边,是与长卷由右向左完备相反的行进方向。他们彷佛被屏侧的男子发布要出场,屏侧女子用手势招唤,韩熙载手执鼓锤出来,后面随着有点含羞、举袖掩口,被人力邀而出的名妓王屋山。
► 这结尾是夜宴的高潮,却又彷佛那么不愿结束,用反方向的进行,把结尾转成开始。形象上,这一段又彷佛是第二段韩熙载击鼓、王屋山舞蹈之前。
这样的结尾,便造成了一个不仅错综繁芜,而且衔接卷首的循环往来来往的韶光暗示,是周而复始的“圆”,是易经“始干而终未济”的不雅观念,是熊十力师长西席阐明《礼记·天道》时说的:“天道之运,新新而不守其故。才起便灭,方始即成终。才灭便起,方终即成始。始无端而终无尽。”
起灭终始在一点上,起灭终始也可以无限。在直线上是无法无限的,必有两端。“无端”的时空恰好是可以卷收与展放的长卷。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山水画要“铺舒为宏图而无余,消缩为小景而不少”。长卷绘画对中国韶光与空间的表现要到宋往后的山水画中更形成熟,发展到了高峰。
来自中国书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