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松风阁诗帖》 纸本 规格32.8cm×219.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庭坚是苏轼门下四学士(黄庭坚、秦不雅观、张耒、晁补之)之一,小东坡7岁。其诗文书法与东坡相颉颃,其创新的精神,大有超越其师的声势,后世多以“苏黄”并称。“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面前”句中“张侯”,即张耒。黄州、武昌(鄂州)隔江相望。由东坡想到张耒,师友或去世或贬,此地此时此景,山谷道人有低回不已中的怅惘与无奈,终极化解为对自由生活的神往。山谷诗尊老杜,多用典故,奇拗相生,诗境幽邃屈曲,开江西诗派。此诗笔势自然老健,意境宏阔,在流走中又具波峭拗折,与其书法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四家中,黄庭坚草书影响最大。我把稳到,黄氏传世的草书作品内容多是抄录古人的诗文,大草行笔的节奏感强,笔势连贯,内容必须了然于心,创作时方能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比较之下,黄庭坚行书,还没能脱去东坡的窠臼,而大字楷书,却独树一帜,是他的一种创造。用唐楷的标准来看宋人书法,险些没有楷书作品。如《松风阁诗帖》,也大多划入行书的范畴。这是由于,字形冲破了方正,而变成了欹侧之势。大小不一,也不能用方格囿之。行笔丝丝入扣的连贯,改变了唐楷板刻的面孔等。但从整体上看,笔法和构造,起行分明,字字独立,多不相连属。折笔多顿笔,方峻严整,还是楷书的基本特色,或定为行楷书,也未尝不可。
研习黄氏大字楷书,不能不提焦山的摩崖石刻《瘗鹤铭》。对此摩崖大字,黄庭坚说:“顷见京口断崖《瘗鹤铭》大字,右羽书,其胜处不可名貌。以此不雅观之,良非右军笔画也。若《瘗鹤铭》断为右羽书,端使人不疑。如欧、薛、颜、柳数公书,最为端劲,然才得《瘗鹤铭》仿佛尔。惟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黄庭坚认定《瘗鹤铭》是王羲之书,给自己的楷法定了一个崇高的名分。“大字无过《瘗鹤铭》”,山谷的评判,成为后世评此碑的威信标准,可见黄山谷对自己取法的自傲。唐人楷书,也只有颜鲁公能入其法眼。这里的信息不言自明,黄庭坚的大字远师《瘗鹤铭》,近取颜鲁公是无疑的。瘦健清拔也是黄庭坚楷法的美学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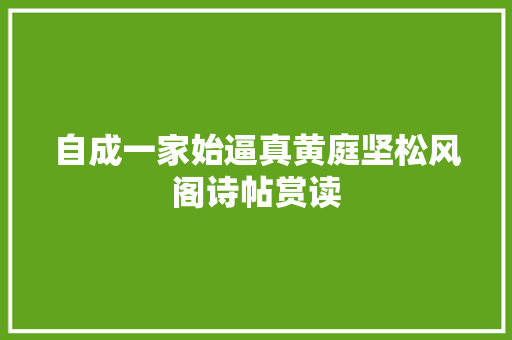
我们看,黄氏大字行楷,横、竖、撇、捺这几笔最为抢眼,更多的是夸年夜的表达。如“三”的上两横之短,与底横的超长比拟;“年”的横与竖的交插而纵向伸展;“適”字“辶”平捺的伸展而托上。长枪大戟的纵横交织,是黄字的主要符号特点。这些长笔画,可以明显看出黄氏运笔的婉曲韵致。有的长横屈曲,分段式涩进,有的长捺也措动缓步,抵纸出锋。这些用笔,便是黄庭坚对《瘗鹤铭》笔法的一种感悟,抑或是对船工荡桨的体悟,即所谓“字中有笔”,流荡而入纸,如锥画沙、屋漏痕,宋代还没有完备的碑法之说。从本日来看,黄氏用的便是借鉴篆籀笔意的写碑之法。
《松风阁诗帖》的结字大多纵长,字势多为左低右高,高下旁边把稳了穿插迎让。故整体看上去十全十美,而妙趣天成。个别的扁字,如“亭、安”,酷似苏字。东坡跋山谷书作云:“鲁直以平等不雅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可见,山谷字的奇特与其道德文章的迥异,均向异端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如其诗格的拗峭之姿,黄字多呈S状扭曲,险涩内敛,而劲力含于字中。化成详细的临写技巧,就应作逆向的思考。如“不”字,中竖的左倾与反向的弧度,“飢、能、饘、暁”几个字的撇画取势的反向弧式,皆有其独造的特点。当然,一些细节也不容忽略。黄山谷写折,如“煙”方折的重顿而多肉,“眼”的横折搭接时显然是两笔完成,“驚”字“马”部横折的提笔暗转,都有细节的变革。看似无意,却有匠心。行楷书,笔顺更应把稳,如“菩萨”两个字的“艹”,便是先写横,再写旁边两点,笔势才能贯通。“煙”字,“垔”部是先写“口”部再写两个竖,方可连贯。还要提醒的是,帖里的一些字如“张”字“长”部的竖过长;“暉”字,“軍”部的“車”左竖过长;“見”字,“目”部的左竖过长等,这是不好的习气,临写时应把稳。
黄庭坚反对在艺术上过度依傍古人,强调书家的艺术个性。其有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的行楷书,字大力足,如长枪大戟般一扫姿媚尘俗,以自家面孔个性而独具魅力,真是值得我们寻思的。
(文/曲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