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书影,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任务编辑高小凡,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近代文学史、文体史方面诸多观点的涌现,使清代与近代的界域不易分清,由此也引出了清代、近代文学史的性子、分期乃至“近代文学”观点能否成立的辩论。清代文学史的下限在何时,这一原来险些毋庸谈论的问题也进入了学术议题;而由于近代文学与清代、当代文学俱有韶光交叉,使近代文学学界更增加了某种“存在焦虑”。客不雅观来说,清代文学应保持完全性,与近代文学可以叠覆存在,共享韶光。重审近代文学史的“韶光”与“时限”,可基于对“特定时间构形”的理解进行谈论剖析和合理辩解。但应把稳,如何安顿近代文学史固然必要,如何阐述近代文学史的内涵和特点则更为主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朝代命名断代文学史彷佛是一个老例,由此便形成了一系列文学史观点。韶光是统统存在的形式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韶光总是历史的韶光、文化的韶光,度量韶光具有高度的人文意义。而以朝代命名断代文学史,从线性的韶光维度上看无疑具有逻辑性,其前后衔接对文学史的解读也不失落工具理性。正因如此,断代文学史就像“韶光银行”,将干系知识、影象存储进去,进行认知、阐释、传播的“取用”相称合理且方便。分外一些的像“南北朝”“宋金元”文学史,在韶光上涌现叠覆,但由于历史背景清楚,且仍旧符合韶光即历史、韶光即文化的认知,也无可争议。然而到了古代文学发展的末了一个时期——清代,却涌现了近代文学史、文体史方面的诸多观点,使清代与近代的界域不易分清,由此引出了清代、近代文学史的性子、分期乃至“近代文学”观点能否成立的辩论。清代文学史该当写到哪里为止,这一原来险些毋庸谈论的问题也成为学术议题。笔者认为,清代文学史是断代文学史,其完全性不应被截解,而近代文学史不是一样平常意义上的断代文学史,但同样成立;清代文学史与近代文学史构成了一种分外的韶光意义与文学史意义的重叠。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不易找到先例,但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循例而证,而是通过还原历史、磋商学理,最大限度地求其客不雅观真实,深化对繁芜征象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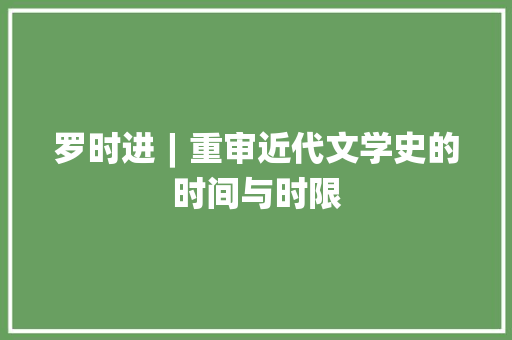
一、何须清代文学史转让韶光?
“思想无内容则空,直不雅观无观点则盲。”[1]观点是建立在直不雅观(感性材料)根本之上的,而从根本上说,对观点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对问题(工具事物)的履历剖析。根据履历剖析稽核清代或近代文学史观点,可以辨认其属性,为其存在和发展张本。
一些学者对近代文学深怀专业情绪,彷佛具有一种对近代文学作为独立学科领域地位的“存在焦虑”。郭延礼指出:“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主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代价。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2]这代表性地表达出近代文学研究者的焦虑感:古代文学史下延几十年,当代文学史上溯二十年,如此两相连接,八十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就无处安顿、有名无实了。
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确实有很直接乃至尖锐的不雅观点,如章培恒曾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是两个学科,前一个学科的终点是后一个学科的出发点。”[3]郑利华进一步申论:“晚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色的重视和磋商等方面与当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当代的中介。在晚世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桥梁。”[4]如此来看,原来置于“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近代文学”客不雅观上确乎“没有了它的时空范围,当然也就不存在了”[5]。
这里对当代文学史是否该当上溯二十年这一问题暂不加置喙,而笔者附和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包括近些年出版的一些分体文学史)以“全清”为研究工具。清代文学本来就不存在所谓下延数十年的问题,这种意识晚清人自然不会有,符葆森编纂《国朝正雅集》收录乾隆元年(1736)至咸丰八年(1858)的诗歌作品,张应昌编纂《清诗铎》起于清初而迄于其违世前的同治八年(1869),在他们所处的时期不可能意识到清诗史涌现了分割线。孙雄于光绪末年编纂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亦以清代年号标识,郑孝胥题词云:“近代诗才让达官,曾闻实甫论词坛。潜夫只有伤时泪,也作君家史料看。”[6]这里所提到的“近代诗才”建立在与己附近的年代感之上,这种年代感是与顺、康、雍、乾、嘉相衔接的。从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役爆发到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发生,这七十多年的文学史本属于清代文学史。换言之,清代文学史只有下迄至1911年方能具足,古代文学史方告终结,清代文学挤压近代文学空间之说无从谈起。
张应昌《清诗铎》书影,中华书局1960年版
孙雄编《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书影,宣统二年(1910)刻本
对一个朝代历史的叙事和阐述该当是该朝代全时段的、完全的,这一点毋庸争辩,也无可置疑。一个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新朝之初即进行对前朝历史的史籍编纂,此为国史编纂常规,其目的便是对前朝进行全幅纪事、完全总结。赵尔巽等撰《清史稿》,自1914至1927年花费13年韶光大致完成,虽然个中舛谬不少,不敷以餍天下之望,但对有清十朝的记述具有基本的完全性是事实。20世纪30年代初,22岁的萧一山凭一己之力撰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全的《清代通史》,显然对有清十朝历史的记述也是全幅性的。
“近代史”的观点涌现较早,海内最早的干系著作大约是李泰棻为北京大学预科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最近世史》,其后有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等,而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最为著名,其在中国通史与近代史关系的处理上也最有代表性。《中国近代史》中鸦片战役到义和团运动等内容原是作为《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出版,后来迭经变革,该书便一度独立成编。华北新华书店于1946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而于1947年9月重印《中国通史简编》时,将原来的上、中册分编为六册,已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册和第八册,合为一书刊行[7]。可以把稳的是,在该书出版过程中,《中国近代史》独立成编有其分外背景,但这一部分仍旧属于中国通史,是其主要的“尾声”,作为完全的中国通史不可或缺,将其合为一书刊行,符合学理认知和历史逻辑。众所周知,启动于2002年8月的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以清史的“通贯”为目的,即贯彻了这一历史逻辑。
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书影,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
范文澜
清史该当是自顺治至宣统十朝的完全历史——如果此点得到肯认的话,那么作为清史一个专门部分的清代文学史的编撰,理论上也应如此。郭则沄始编于1911年、1912年之际而完成于1935年的《十朝诗乘》,便是有清一代“诗之史乘”之作较为成功的实践。学界相称熟习的沈粹芬、黄人、王文濡辑刊的《清文汇》、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晚晴簃诗汇》,俱下迄于清末[8],显然也具有“全清”诗文总汇的意旨。
郭则沄《十朝诗乘》书影,福开国平易近出版社2000年版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书影,中华书局2018年版
那么回视一下,在1911至1949年期间有没有以“近代”命名的文学著述呢?回答是肯定性的,如陈衍《近代诗钞》、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钱仲联《近代诗评》等,这样的例证不少。但他们此处的“近代”,略同于“晚清”[9],实无意在顺、康、雍、乾、嘉与道、咸、同、光、宣之间找一个隙罅而断然划出一条鸿沟。黄人《中国文学史》中清代部分(手稿)即已涉及包世臣、曾国藩、冯桂芬、谭嗣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绛(太炎)等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自笔墨起源叙起,直至道光、咸丰往后止,无疑都是包含“近代”部分的。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多种著作,同样遵此原则,系统而完全。
黄人《中国文学史》书影,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文学的时段“是指自1644年清兵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役开始之前,凡196年”[10],但正如傅璇琮、蒋寅指出:“两段论的分期,虽然符合历史研究中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科划分,但人为地把一个完全的朝代的文学按社会性子一分为二,彷佛有些欠妥。”[11]所指出的“欠妥”紧张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作家的归属涌现问题,有些常日被划入近代的作家如龚自珍,其紧张文学活动与造诣是在1840年以前完成的,不宜归入近代;二是从清代文学的书面措辞形式(文言文)和紧张诗体裁裁看,晚清文学与清前中期文学并没有实质性差异,不必把晚清文学独立为近代文学。第一点属于技能性问题,第二点是学理逻辑问题,虽然剖析没有展开,但主要性已经显示。严迪昌《清诗史》下迄“同光体”与“诗界革命”,其结语云:“在黄遵宪去世后六年,辛亥革命起,又六年旁边,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风卷云涌而来,诗文化领域内也随之涌现弃旧图新的巨变,清代诗歌的蜕变路程究竟成为一段掀了过去的历史。”[12]值得把稳的是,一样平常将近代文学的终点确定在新文化运动发起时,而严迪昌认为,正好到这个时候清诗才完成了蜕变的全过程,其说甚韪。
应该承认,人们意识、不雅观念中“近代文学”时段里辛亥革命以前的那部分应包含在清代文学之中,自然也包含在古代文学之中,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末了的篇章。完全的清代文学史,必应是从清初到清末的文学史,而“近代文学史”如何得以成立,则是其余一个论题。如何为“近代文学”的存在辩解,或者说,该当若何为“近代文学”正名?这是不同思维、不雅观念域中的问题,应进入历史和文化语境寻求态度进行论证,绝非大略地要清代文学史转让出一个自然韶光段落,便可使近代文学安身立命、合理成立。
二、近代文学史在“特定时间构形”中展开
显然,“古代”词义,名相清晰;“清代”十朝,完全相接。如欲从中认识并区划出“近代”,当从理论与事实层面擘肌析理。笔者对“近代文学”的存在持掩护态度,但认为其与清代文学形成的是复合性并存,相互之间有一个韶光范围的共享。可以从复合存在、韶光共享角度加以恰当剖析,如此,近代文学的学科领域才能合理化地在适当的时空中安置,干系研究才能展开和深入。
文学史的学科领域设立,未必以“代际”为存在条件,也不必纠结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时序”。要阐明这个问题,仍旧要回到韶光理论。古希腊人曾经对韶光进行趋向行动的主要观点划分。“他们把韶光分为韶光克罗诺斯(Chronos)与卡伊洛斯(Kairos),前者为一样平常韶光,指流逝的与可被度量的时令之类;后者为意想不到的韶光,包含可被把握的机遇、利好时候和决定性瞬间。”[13]“克罗诺斯韶光”即自然的韶光,代际和时序包含于个中;“卡伊洛斯韶光”即不雅观念的韶光,事宜和机缘包含于个中。前者在线性流程中显现,是自然性的;后者在韶光内部对履历进行综合而在不雅观念中显现,是建构性的。建构性韶光的单元每每是一条主要的存在巨链,只不过未必以线性形式(单元)表达,而因此不雅观念形式(单元)表达,不雅观念单元嵌入社会运行过程中,蕴涵了更多的思想、文化内容,呈现出主要的变革和趋向,其影响甚巨。
须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自然的韶光还是不雅观念的韶光,都具有客不雅观的历史性,只管前者可以直不雅观创造,后者须要想象剖析。胡塞尔曾说:“在动态关系中,各个关系环节与那个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行为是在韶光上相互分离的,它们在一个韶光构形中展开自身。”[14]论证近代文学是否实存,关键在于对历史、文学史“动态关系”的想象、剖析、体认,从而理解“近代文学”是如何在“一个韶光构形中展开自身”的。
在中国文学史中,这种不雅观念单元确不多见,如果要探求的话,“盛唐诗歌”有一定的相似性。从唐代文学中的“初、盛、中、晚”命名上看,“初”“中”“晚”都基于“时”而论,唯“盛”乃据“势”而论,而“势”之如何,是对某一过程总表示象有思想的态度表达,乃至可以看作一个想象性判断,而态度和判断都带有某种主不雅观建构性。大概正因如此,清人王士禛《喷鼻香祖条记》说“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15],个中多少有消解唐诗发展主不雅观断限的意味。当代学者认为“唐诗分期的紧张不合是有无盛唐和有若何的盛唐这两个问题”[16],这种纠缠每每很难理清,一些学者便索性用“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来为唐诗发展进行韶光上的基本划分[17],而将“盛唐”予以搁置。只管搁置,但“盛唐”作为一个不雅观念单元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这个诗史判断已经储存进了“韶光银行”,其知识和影象作为永恒的文化资产,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是一种存在,并且持续地被人们重视和研究。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18],这里的“事”指事实、事宜,而“历史涉及就韶光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宜”[19]。近代文学能否在中国文学史中成立,或者说,近代文学能否成为一个不雅观念单元,取决于近代文学在历史过程中经历的事宜以及表现事宜的态度、景况。为相识释这个问题,不妨一读黄人的《清文汇序》。他在概括了“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与古为新,无美不具,盖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气者焉”的特点后,对道、咸、同、光诸朝文的阐述颇有光鲜比拟的意味:
道咸两朝,争桑弄兵,四寓多故,男儿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来,弃而去。击楫者有澄清之志,浮查者多凿空之谈。劬古并治钤符,著书旁通韪译。儒生专阃,成韩、范之勋;记室多才,得琳、粲之亚。至若贾生恸哭,杜牧罪言,尤在在皆是。故其文冲动大方峭厉,纵横排奡。忠义之骨,而参以仙侠之心;骚雅之音,而出以幽并之气。复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贯注灌注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故其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如披王会之图,如不雅观楚庙之璧,如登喜玛拉山绝顶,遘天帝释与阿修罗鏖战,不可方物。极此曩昔,四海同文之盛,期当不远。[20]
与康、雍、乾、嘉之文得春夏之气比较,道、咸、同、光诸朝文则可感秋冬之风了,以“春夏之气”与“秋冬之风”比拟,可以看出近代文学各种文体的基本气候、风貌。黄人对清代文学风气的类比、剖析,不禁使人想起吴经熊于1938至1939年所撰写的《唐诗四季》,在这本今人较少提及却极具特色的书中,他也用了类似的比喻,将唐诗分为春、夏、秋、冬四个期间:“春季包括初唐墨客,李白和王维;夏季包括杜甫和战时墨客;秋季有白居易、韩愈辈;冬季有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韩偓及其他minor诸家。”[21]《唐诗四季》是从比较文学视角撰写的,作者说:
唐诗的春是Dionysian,夏是Promethean,秋是Epimethan,冬,我应该若何称呼它呢?我不能替它题名,不过每逢我诵冬诗时总想到寇士丁那·萝色蒂美得难以形容的“过逝”(Passing away)。[22]
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往后彷佛每一个朝代都经历过兴起、发展、迁移转变、过逝的过程,唐代尤为范例,故对中、晚唐诗歌史以秋、冬来比拟,是颇为适恰的。须要把稳的是,历代文学史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寄托历史的演化,而清代以前各代的历史演化都是在内部关系冲突、浸染下发生的,哪怕几度涌现南北分治的分外局势,涉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仍旧该当看作是内部关系的冲突和浸染。这种冲突虽然带来激烈的社会激荡,但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并不钻营王朝制度的根本变革,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史,其性子也不会有根本变革。历史上的南北朝文学也好,五代十国文学也好,两宋文学也好,所采纳的韶光与地域范围复合的命名办法,只在于表现分合,无意也不可能表现出质变。而清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存在时空交叠,其间包含着质变,与以往历代文学史都短缺可类比性。
吴经熊
吴经熊《唐诗四季》书影,辽宁教诲出版社,1997年出版
近代文学是一种分外征象,而近代文学史之成立,从文学史一样平常习得履历出发难以解释。如果没有差异于其他朝代或阶段的知识性、构造性、实质性要素作为支撑,并不能形成辩解力量,故探究个中的异质性无疑为第一要义。回到一年四季的韶光性喻体中来说,春夏秋冬本属自然征象,也是一个完全过程,那么是否须要将与“春夏”不同的“秋冬”作为特定时间构形专门截取出来考量,则要看此一“秋冬”的质性如何。细读黄人对道光往后文学的论述,实际上分两个阶段:一是“道咸两朝,争桑弄兵,四寓多故,男儿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来,弃而去”;一是同光“复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贯注灌注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争桑弄兵”是历代统治延续到中后期的比较普遍的征象,但道、咸期间的“弄兵”与历代具有截然不同的性子,不尽然是社会阶级、阶层抵牾的极化形式,也不尽然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利争夺的斗争办法,而是西方列强企图实现对中国领土利益哀求的侵略。
以往历代大规模地诉诸武力的终极结果便是鼎革易代,反不雅观清代,虽然宣统立朝不久确实涌现了朝代更变,但此番易代与“争桑弄兵”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险些是一场鲜见兵戈、险些没有硝烟的鼎革之变,结果虽在猜想之中,但韶光节点和突变过程多少有些不同平凡,这显然与同光复兴后的“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大势干系。特殊要把稳的是,与历朝之易代实质上完备不同,清代统治的结束冲破了朝代更迭只是“改变权力运行者—产生新的‘继天立极’者—不改变制度”的规律,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家政体发生了根本改变。
道、咸以降迄至辛亥革命的文学史是这一历史潮流的反响,旧型文人与新型文人同时并存,旧体创作与新体创作互动共生。古范例文人生活与书写看上去一如往代,但内心亦不能不为时期传染引发,而怨言、讽言、警言、罪言、危言、惊言、壮言、年夜言、预言性文学频繁产生,穿天裂地,“每谈天下事则忘禁”[23]的文人及“多关安危大计”的创作霸占了极大的言说空间,自有某种特定的精神内容和文学气质。这种虽有继续性但差异于以往及后来而自成格局的文学阶段,走向了清代文学的结穴,在韶光的轴线上该当视为晚清;而从文学不雅观念史的角度、从古典性与当代性伴生化合的史实来看,它融进了新文化、新思潮,确有情由授予差异于“清代文学”的观点,而以“近代文学”称之符合历史和文化发展趋势。
在同一“韶光构形”中展开的清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史,各有自身的生命周期,而因近代文学史具有自身的分外性,对其发生至结束的过程,应做出客不雅观详细的剖析,从而合理地划分“时限”。
三、近代文学史的“时限”再议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险些一贯附属于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涌现的韶光很迟。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方案的京师大学堂学科门类中才涌现了文学科,次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方详细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24]。而从“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25]的提法可知,国人文学史的编纂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虽然如此,这一学科从探索成立到基本成型,其过程并没有能够真正保持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导引。这在韶光范围与阶段分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代文学史堪为范例[26]。
当近代史学科稳定形成后,近代文学史彷佛顺其自然地涌现了。有学者以“‘晚清’还是‘近代’”为题梳理了干系背景:1957年,教诲部颁布《中国文学史传授教化大纲》,该文件依据历史学界当时所盛行的新旧民主主义理论,将鸦片战役至五四运动期间的文学史单独提出;次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这两部带有深刻时期烙印的文学史著作不谋而合地设置了“近代文学编”,以相应《中国文学史传授教化大纲》的哀求;自此之后,近代文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承认[27]。在特定的时期语境中,合理性的承认已近乎合法性的肯认。
在韶光范围方面,近代文学史也合理、合法地承接了近代史的基本认定。绝大部分近代文学史著作都以1840年和1919年作为起讫的高下限定,钱仲联在2002年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近代文学丛书》所作《序》中即言:“近代的范围,现在学术界公认为始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役往后,迄于‘五四’新文学改革运动以前。但这一阶段的文学家,有生略早于一八四〇年,去世或更在‘五四’往后较长一段韶光,而其人的紧张文学造诣或成名,则在此期间内的,一样平常也认为应包括在内。”[28]这是传统的、主流性的表述,也是在较大程度上能够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接管的界定。
钱仲联
关于近当代文学史学术版图的界域,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见地,代表性不雅观点是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表示“不把‘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作是一个因果,只是把当代性推前了50—100年”[29]。这一“没有/何来”式的谈论具有一定的学理逻辑,有助于认识当代文学的源起,对近代文学研究也不无裨益。只是,如果将当代性上推50年则包括了清代同光朝,上推100年则涵盖了鸦片战役以降各朝,如此清代、近代(或晚清)、当代文学的韶光范围、学术畛域就变得更加交错繁芜了。
王德威《被压抑的当代性》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应该承认,希望对文学史学术版图做出清晰划分是不切实际的,因交叉重叠而繁芜模糊,反而更靠近于文学发展、知识衍化、不雅观念演进的实然状态。但仅仅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办理问题,纵然根据本文提出的以不雅观念为根本共享韶光,从而建构相应的学术版图,但如果不雅观念暗昧,结果仍旧会各执一端。
不雅观念是一种认知,认知化为知识,形成学术研究的工具,也内在确定了研究的范围、方法和路向。从几个干系学科领域来看,古代文学的内涵是古典性,近代文学的内涵是近代性,当代文学的内涵是当代性。那么,何谓古典性?何谓近代性?何谓当代性呢?如果诸多不雅观念的考量不能确证,难以相互支持并融为一种较为同等的认知的话,关于清代道光以降一百多年的学术体系就很难形成,方法和路向也难以确立。
不雅观念大概比较抽象,文体则更为详细。诗歌、词赋、骈文、散文、小说、戏曲等,在道光朝(或以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为始端)之后一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和演化形态并不相同,内涵的古典性、近代性、当代性也不能等约,如果不加区分,不顾肌理,一定要涵盖统括到某个学科领域范围,滞碍乃至扞格就不可避免。乃至可能涌现这样的征象:清代文体延长线上的创作成果被合并到古代文学中,而当代文学研究将当代性向前追溯的努力正好成为古代文学传播、影响、接管的证成。
这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或许并无多大妨碍,而天生于文学内部的解构力量,对近代文学学科无疑是具有压力的,近代文学学科该当有所应对。韶光性是历史性的根源,同时也酝酿、天生了历史性的结果。故通过调度近代文学史的高下限韶光来改变其学术版图大概不失落为积极且有效的方法。这方面的不雅观点较多,总趋向是上拓下延。如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该当是从清道光初年(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一百一十年间的旧体文学(即文言文、旧体诗、用文言或半文言写成的章回体小说和文学评论、旧戏曲等),而不应限于目前通畅的1840年鸦片战役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止八十年间这一范围。”[30]这一时限提出的依据是:其上限如果定在1840年,则龚自珍作为“代表”无法合理树立;而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同盟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新阶段,中国近代文学史至此才终于走完了它的全过程。
显然,这是学者为区隔近代史而建立具有近代文学独自体系所作的剖析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代价。但龚自珍的文学史意义完备可以在清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研究中得到恰当的阐述,并找到其在文学史上的主要位置,是否一定要以其作为近代文学史的开端,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而鸦片战役的爆发,作为一个突出事宜标志着清代历史的断裂,也深重影响了清代文学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若打消这个事宜标志,近代文学史的异质性便会显得模糊。不以鸦片战役为出发点,颇难令人认同。至于中国左翼作家同盟成立这样的事宜,远不及之前、之后诸多事宜在历史、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影响,以之作为下限,难以保持历史与文学史应有的平衡。
韶光内涵与知识内涵的趋一,在近代文学史上表现得非常范例。如果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其他历史阶段,韶光区间与知识内质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就近代文学而言,其内质在相称高的程度上被韶光所定义,定义的基本根据是“新”与“旧”的冲突。前文所引黄人论述的“异质化合”,即包含了“新”“旧”比拟。如果要在相应阶段探求一位新旧比照光鲜、化合特色显著的作家的话,大概黄遵宪是得当的。丘逢甲《人境庐诗草》跋云:“四卷以前为旧天下诗,四卷往后乃为新天下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天下之哥伦布也。变旧诗国为新诗国,惨淡经营,不酬其志不已。”[31]值得把稳的是,康有为曾用“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平生易近”[32]对黄遵宪的诗歌内容做出高度概括,而这三个方面确乎可以看作近代文学的紧张内容。
实际上,这些内容在逻辑上是紧密关联的:国变带来了极高的国家风险,而国家的一系列事变,使中国历史的进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涌现了种族灭亡的危急,救国与保种成为具有前辈、自觉意识的仁人志士无畏死活的抗争目标。其间一系列重大事变(包括社会性、自然性的)带来了巨大的民生灾害,与国家民族危急叠加重累的苦难感,引发出浓厚的悲悯情怀,形成了文学创作的近代背景。故“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平生易近”作为近代文学的主题,对近代文学史高下限韶光的认定具有主要的参照代价。以此来看,学界原已达成一定共识的近代文学史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19年,这是基本合理的:国变之殇、种族之殇、平生易近之殇引发出革命浪潮,同时孕育、匆匆成了新文化运动。故坚持这个一样平常共识,能够表示近代文学发展的起因、过程、冲突、走向,韶光周期与文学史周期基本吻合,自有沿用代价。
那么,是否有扩大近代文学知识版图的可能呢?近代史学界在此已经先行一步了。只管许多学者认为近代文学研究短缺独立性,其主要缘故原由即过于寄托近代史的研究。但如果深知近代文学史是近代史学科的直接派生物,对其寄托的合理性如何质疑、如何抵抗呢?这样的表述彷佛有些悲观,短缺文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但鉴于近代史与近代文学史天然的黏着特点,将两个学科置于“一个韶光构形”中结合起来不雅观照,亦未尝不可。
长期以来近代史学科发展相称可不雅观,不但以《近代史研究》(1979年创刊)学术期刊为主阵地,揭橥了丰富的成果,而且不少学者颇为关注中国近代史的重构,并扩大其学术研究面,形成了有传播力的话语。这类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集中谈论,至1997年胡绳提出了最具威信性的见地[33]。这方面系统的成果是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他一贯主见打通中国的近代、当代史,从而构建出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工具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合并供应了主要依据。王飚在《中华文学通史·近当代文学编》[34]的《绪论》中即提出,1840至1949年间中国文学体系完成了整体性的从古典向当代的转型,因而在中华文学通史中,近代文学、当代文学该当合为一编[35]。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合并后的文学史学科可以命名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也可以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英文中,近代和当代本无本色差异。如果考虑到1840—1949年间古典文学的通贯和繁盛,考虑到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冲突和混融,考虑到中国近代史、中国当代史两个学科合并后取名‘中国近代史’的先例,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合并后名曰‘中国近代文学史’,似更妥适。”[36]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书影,江苏公民出版社2013年版
将国变、种族、民生问题统归到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理念下,与近代史学科意识同等,也能够系统阐述近代文学的内在变革和革命性发展,但在考虑近代文学的“韶光”和“时限”问题时,既不应将其独立于清代文学之外,也难以不兼顾约定俗成的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实在无论若何谈论“分”“合”,预见未来清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研究仍会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那么当代文学史之成立,其上限在哪里自可谈论,下限在1949年则无疑。
其余,这样的分期以“易代”作为依据的思维特点十分明显,而未考虑近代文学的“特定时间构形”。应予把稳的是,国变之殇、种族之殇、平生易近之殇三者之中,平生易近之殇是古代文学史自然也是清代文学史一个始终关怀的主题,唯前两者更具有近代文学史的分外意义。既然国变之殇因此鸦片战役和太平天国内乱为源的,而种族之殇则萌发于鸦片战役,极危于甲午战役,至抗日战役胜利方告结束,那么如果要对近代文学史有所扩展的话,不妨将从鸦片战役外族入侵到中国公民浴血抗战八年作为一个全过程,如此则可以将1840年作为上限,以1945年为下限。
提出这一分期方法,是参考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思路。该书很简短,只有五万多字,但学理颇为明晰。其凡四章:第一章《剿夷与抚夷》,紧张论述鸦片战役前后清政府面临的外祸和对策;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侧重剖析鸦片战役后清政府遭遇的内忧及其积极应对;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落败》,重点阐论晚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的意义和失落败缘故原由;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意在讲述甲午战役后国人所进行的救亡图存的方案,其紧张不雅观点是在日军亡我中华的企图面前,全国逐渐形成联络同等抗战的大好局势,加上已经积累的近代化培植成果,一定能够找到光明的出路[37]。该书写作有一定的时期局限,但其描述近代史的发展阶段、节奏是有内在学理的。
进一步参考张海鹏提出的近代“发生‘沉沦’”和“旋转‘沉沦’”理论,这一分期也能成立。张海鹏认为:“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独立主权、领土完全受到严重损伤……但是,正像阴郁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期间涌现了向上的转机……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管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见。……在这往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公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旋转‘沉沦’。……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38]该当把稳,正因抗降服利,除了喷鼻香港租界外的所有在华租界和租借地皆予收回,鸦片战役之“因”产生的“果”,有了一个标识性的清理。鸦片战役以来近代的“沉沦”与“救亡”,形成了近代文学史的主旋律,因此以1840至1945年为近代文学史的过程,不失落其合理性。
大体上,笔者认同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相连接的不雅观点,如此作为断代文学史韶光界域清楚,各自的研究内容有较为明确的归属性。而近代文学史是一个“特定时间构形”,是事宜驱动下的“不雅观念文学史”,其“韶光”与“时限”应有事宜内涵——近代范例事宜贯穿的过程,便是近代文学史的过程。它无须承担断代文学史的义务,却自有超越断代文学史的分外研究内容和精神指向。
当然,对事宜存在不同的阐明路向和谈论空间,历史事宜与文化、文学事宜之间的关系错综繁芜,故可以想见,关于近代文学史时限的界定,本着各自的言说态度和叙事策略,仍旧会连续谈论。弥纶群言而归于一理是空想化的,纵然不雅观点存在不合,客不雅观上也能够使这一分外而主要的知识领域得到更多关注,促进古今通变这一伟大命题的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余论
文学史属于人文知识范畴,其意义由言说者的阐明和认识而天生,从而建立起一门学科的知识。言说者的主不雅观意图和不雅观念类型越贴近历史语境,这种知识越能被承认和接管。实在,与形成近代文学史的“韶光”与“时限”的某个结论比较,近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如何与断代性的文学史区分,是一个更须要谈论和明确的问题。换言之,如何安顿近代文学史固然必要,如何阐述近代文学史则更为主要。
清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应按照断代文学史的方法去写,但近代文学史无须也不应套用。其研究应有“大变局”的问题意识,以阐述和深描出“大变局文学”的分外情境和质性为主旨。1985年9月全国各地学者在中山大学参加以近代文学史分期为主题的学术谈论会,傅璇琮在为会议论文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子和分期》所写的书评中提出:“由分期问题,就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国的近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的性子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特色?它又经历过哪些阶段?”[39]三十多年来这些提问不断被回答,使认识趋于深化,但有些问题至今还悬而未决。本日如果要进一步阐明近代文学史研究的合理性、主要性、审美性的话,应进一步思考: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异质性是如何产生的?在千年未有之变中起到何种浸染?藻雪国魂的文脉是如何延续涌动的?文人在时期思潮中如何持守传统或逐渐转型?由此推及的是,那些雄襟伟抱、横绝五洲的风云人物当如何记载?年夜方激烈、横议时政的文学作品当如何评价?胡焰方张、士气弥奋的志士意气当如何阐述?西台恸哭、山陬仗剑的悲壮情绪当如何抒写?
从近代士人、知识人的天下不雅观、国家不雅观、民族不雅观、民生不雅观的角度进行知识性论证,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和文化演化的方向。中外关系的冲突、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知识的吐纳、民族意识的唤醒、爱国情怀的激扬、志士侠义的高倡——浩瀚声部中的音符,所包含的屈辱中的抵抗斗争、苦难中的坚忍不拔、空想中的自由神往,凡此都由新的天下不雅观、国家不雅观、民族不雅观、民生不雅观勾引而谱成壮美的史诗。
从普遍性来说,近代文人逐渐改变了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乃至有天下的不雅观念,也逐渐旋转了在世界之林不知如何昌兴民族、如何赋权于民的方向。在异质领悟、推陈出新的趋势中,他们形成了一股推进中华文明进程的力量。近代文学作为文学遗产足应高度重视之分外代价,正在于此。但“近代文人”是一个多义的复合凑集名词,在分外的历史韶光中,他们的认识不一,高度不同,文学书写有异。重审近代文学史的干系问题,正是为了同情、理解不同的文人与文心,走近那些作为时期坐标的精彩志士、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抉发并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内涵和文学气质。
注释
[1] 康德:《纯粹理性批驳》,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2][5]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文史哲》2011年第3期。
[3] 章培恒:《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文申报请示》1999年2月6日。
[4] 郑利华:《中国晚世文学与“近代文学”》,《复旦学报》2001年第5期。亦可拜会章培恒:《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郜元宝:《尚未完成的“当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学报》2001年第4期。
[6] 郑孝胥:《四朝诗史题词》,孙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清宣统三年刻本。
[7] 拜会《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教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8] 《晚晴簃诗汇》收录诗歌迄于宣统朝,而《清文汇》始编于光绪三十四年,故其收录下迄同、光朝。
[9] 按,如钱仲联《近代诗评》开篇即言:“诗学之盛,极于晚清,跨元越明,厥涂有四。”(钱仲联:《梦苕盦诗文集》下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511页)
[10] 按,游国恩和袁行霈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的《清代文学研究》都持此说。
[11] 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辽宁公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12] 严迪昌:《清诗史》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0页。
[13] 赵汀阳、弗朗索瓦·阿赫托戈:《韶光和历史的观点:一个实验性的跨文化对话》,王惠民、贾祯祯译,《哲学研究》2023年第1期。
[14]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11—912页。
[15] 王士禛:《喷鼻香祖条记》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傅绍良:《从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诗分期的客不雅观标准》,《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7] 按,持此说的紧张有王气中、倪其心、陈伯海等学者。拜会张红运:《二十世纪唐诗分期研究述略》,《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8]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9] 康德:《自然地理学》,《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第162页。
[20] 黄人:《清文汇序》,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第1集第1卷《文学理论集》,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308—309页。
[21][22] 吴经熊:《唐诗四季》,徐诚斌译,辽宁教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第7页。
[23] 吴昆田:《养一斋集跋》,同治八年江苏潘氏刻本。
[24] 拜会朱有[璱] [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3、770页。
[25] 拜会朱立元、栗永清:《试论当代“文学学科”之天生》,《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版序》,《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
[26] 孙之梅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分依赖历史学科,突出地反响在关于近代文学高下限与分期问题上。”(孙之梅:《对中国近代文学高下限、分期的反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另拜会张中:《试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
[27] 拜会马昕:《“晚清”还是“近代”?——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观点更替与新旧领悟》,《云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8] 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媒介》,陈三立著,李开军校:《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9] 王德威等:《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访谈》,《汉措辞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30] 张中:《试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
[31]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826页。
[32] 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郑力民编:《康有为集》,广东公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1页。
[33] 胡绳在《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题词》中提出以下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往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得当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善始善终。”(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5卷,山东教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
[34] 拜会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六卷《近当代文学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35] 任访秋对此论证得更早,应予重视:近百余年来“紧张的革命工具和仇敌,则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以是鸦片战役中,公民的反帝……到晚清的革命派,五四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没有不是领导公民进行反封反帝的斗争的,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才算彻底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任访秋:《关于近代文学史的断限与分期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6] 王达敏:《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云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37] 拜会李军全:《〈中国近代史〉导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四川公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0页。
[38]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9] 傅璇琮:《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喜读〈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子和分期〉》,《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范例事宜的文献考辑与研究”(批准号:18ZDA25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