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上图出自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1843-1924)的相册,现藏于其母校——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拍摄于三都澳开埠之初,是从三都码头往对岸礁头方向所摄,码头旁的联排建筑应为茶仓。由于三都澳周边均为产茶区,茶叶贸易迅速发展,使这个东方港口有名海内外。(曾有新闻指上面的老照片拍摄于1870年,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为大误)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的古树,在老照片中即已颇显年纪,至今依旧特立,且冠幅巨大,犹如华盖。这是一棵被列入福建省古树名木的樟树,树龄经测算有600年。也便是说,她亲眼见证了三都从一个小渔村落到通商口岸,再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又重修的全过程。近年,在树旁还新建了“福海关”门。这棵樟树仿佛成了这座海岛无言的守卫,只在风起时轻声低语。
由于老照片中对岸的礁头景致现已被建筑遮挡,笔者又到码头附近拍了这张照片,山形依旧枕“海潮”。
同样须要错位拍摄比拟照的,还有杜德维的另一张三都老照片,是往相反方向,也便是三都本岛方向拍摄。笔者从海上拍摄了比拟照,虽然位置相差甚远,但刚好可以看清山势,与百年前并无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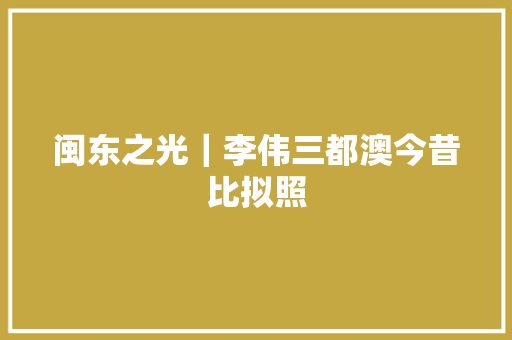
- 2 -
上图出自于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的相册,现藏于其母校——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图书馆,约拍摄于1908年。照片中心是福海关税务司私邸,券廊式建筑,双层正方脊顶,为主管关务的福海关税务司的寓所,位于三都岛松岐村落半山腰,是至今仅存的福海关建筑遗迹。据干系文史资料记载,旧时“楼房内有会客厅、餐厅、书房、起居室和寝室等十余个房间,供洋税务司一个人享用。室内装饰讲究,陈设豪华,屋顶系用水纹铁板建造,家具、地毯、沙发、窗帘,搜罗万象”,这些如今大多已难觅踪迹。私邸前有草坪,供聚会等活动。2009年11月,福海关税务司私邸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值得指出的是,它常被称为“福海关税务司旧址”,这是不确切的,由于税务司并非机构,而是官职名。
- 3 -
上图出自1995年出版的《福建省志·海关志》,拍摄韶光不明。私邸墙体上已有明显的岁月痕迹,不似初建时那般光洁,右侧的走廊新建了台阶。据悉,私邸外墙在2009年修缮时曾被漆为黄色,近年才变动为白色。参照闽海关历史建筑,白色更符合历史原貌。
- 4 -
上图出自1924年10月《Church Missionary Outlook》,拍摄的是在航行途中的题诗艇。原图并未标注地点,但由于背景的山形分外,使我预测其为三都岛上的港口山。这一想法终于在拍摄比拟照后得到验证。题诗艇是都柏林大学布道会为布道所购的一艘中国式的木帆船,从霞浦出发,往来沿海各县。读过拙文《被遗忘的宁德西医先驱》的读者应该记得,最早将西医引入宁德的密马可年夜夫(Dr. Marcus Mackenzie,1871-1922),正是乘坐这艘船从霞浦来到宁德。
- 5 -
上图出自1935年第7卷第22-23期《公教周刊》,所拍摄的是三都澳天主教堂,位于松岐村落,是天主教福宁教区主教的本堂。据郑正球、朱永春《福建三都澳近代建筑遗存稽核》,该教堂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亦即天主教福宁教区主教由福安迁往三都澳的次年。教堂为石构造,具有西班牙哥特教堂的某些痕迹。但因其建于20世纪,已呈现近代建筑的诸多特点,因此不如“近代哥特教堂”确切。建筑雕饰非常风雅讲求,采取了镂空的手腕。近年来,教堂声名远播,已成为三都澳旅游必去的“打卡点”之一。
- 6 -
上图出自1935年第3卷第10期《我存杂志》,照片左侧为三都澳天主教堂的背面,右侧可见主教府邸。远景为三都澳的地标之一——笔架山。从比拟照中,可以创造教堂的外不雅观有明显的变革:初建时,教堂拱背后是尖顶龛,后改为半圆形龛。
在比拟照中,主教府邸被树木及建筑粉饰。笔者对其理解有限,因此摘引《福建三都澳近代建筑遗存稽核》先容如下:“主教府邸位于天主教堂右翼的坡地上。府邸确切建造韶光无记载,但据当地居民回顾,建于本堂之前不久,加之其应该在福宁教区主教公署决定教迁往三都澳前后,大抵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从府邸风格与教堂附近,略呈西班牙风格的柱头及细部装饰,也可做佐证。府邸为两层砖木构造,四坡屋顶,外墙抹灰”。
- 7 -
上图出自于笔者收藏的三张三都澳玻璃幻灯片之一,可能由英国拍照师摄制于晚清,是目前三都澳老照片中仅见的玻璃幻灯片。左方为港口山山脚,下方是堤坝围护的水田。值得把稳的是,在堤坝外可见成片的红树林。红树林曾广布三都澳近岸海疆,包括旧时宁德县城附近,后来随着环境毁坏而灭迹,近年人工栽种取得了一定成果。
- 8 -
这是一组不同期间的三都岛照片。图1出自1913年8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四号。民国初诞,三都澳由于偏居一隅,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是其勃兴之际。福海关代理税务司哈次恒(J. E. Hartshorn)曾写道:“1911年发生的政治大事,对本地区的生活和贸易没有发生大的影响,1912年三都岛曾有过一段相称沉着和繁荣的期间”。图2出自1933年第2卷第12期《关声》,由海关职员吴维濂拍摄。1931年10月,强台风席卷三都澳,福海关关署、验货房、外班关员办公处等建筑受毁严重,但次年就完成重修、修复,岛上商贸兴盛、活气勃勃。经由数十年的稳定发展,三都澳迎来了开埠以来的壮盛期间。图3出自于1940年7月26日《东京朝日新闻》。1940年7月21日,日军轰炸三都岛,街道陷入一片火海,硝烟漫天。实际上,从1937年全面侵华战役爆发以来,日本便时时入侵三都澳。1940年,日本集中海陆空力量,试图从海上封锁中国。三都澳是运输抗日物资的交通要道,成为主要打击目标。日军安排了一名特派员(姓氏为冈田)随行,留下了不少影像记录。照片左上角的黑点即为飞机,是一种舰载水上飞机,可从舰艇甲板起飞,实行侦查、轰炸任务。因日本侵略,三都澳的发展遭受致命打击,街市化作瓦砾,百姓流落失落所,数十年繁荣毁于一旦。由于行船线路缘故原由,笔者未能抵达照片拍摄所在地,以是从礁头拍摄了三都岛景致。
- 9 -
这是一组分外的比拟照。读过拙文《一家人与一只老虎的往事》的读者应该记得那只名叫“太极”的华南虎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被人捕获,卖给了时任福海关代理税务司威勒鼎(H.St.T.Wilding)一家,在私邸与“小威勒鼎”共同度过了童年光阴,事后看来,大概是生平中最好的光阴。当笔者徘徊在修葺一新的福海关税务司私邸门前,早已物非人非。然而,笔者有时看到了这张石椅和草坪,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了百年之前。我相信,脚下的每寸土壤早已把影象见告每颗小草,清晨时凝成草尖的露珠,日出后化作岛上的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