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人
一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十仲春,首次任太守的苏轼在密州任满,携眷拟先回京师,到翌年仲春十二日,苏轼等人刚至赵匡胤一百一十七年前黄袍加身的陈桥驿(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陈桥镇)时,又接到改知徐州的诏令。从历史来看,徐州自古便为中原九州之一,从先秦始,便成北国锁钥、南国门户,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商贾云集中央。从苏轼当时写给朋侪、京东路转运使鲜于侁的词句“梦魂东去觅桑榆”中,可见其不无愉快之感。唯美中不敷的是,诏令中“不得入国门”使苏轼只得暂居城外范镇的东园宅邸。
未能及时履新徐州,缘故原由用苏轼自己的话说,是“改差彭城,便欲履新,以儿子娶妇,暂留城东景仁园中”。他说的儿子便是宗子苏迈,后者娶妻石氏。待喜事临门的苏轼终于动身赴徐州时,已到四月初了。苏辙当时为签书应天府判官,一同南下,从苏辙当时《寄范丈景仁》诗中的“留连四月听 ,扁舟一去浮奔浑”一句可知,他与苏轼是取道汴水。一行人过南都(今河南省商丘市)、宿州、符离后,于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徐州,时有国子监通判田叔通、寇昌朝、石夷庚等人相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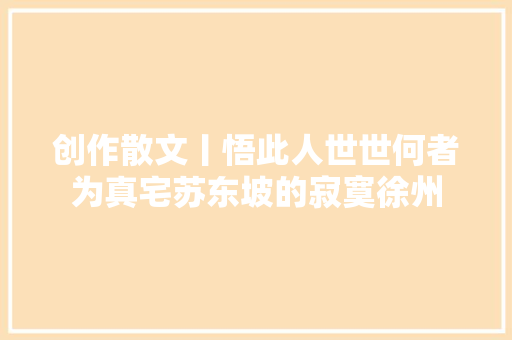
此时此刻的苏轼自然不会知道,在徐州任上,自己将碰着什么人、感慨什么事、写下什么诗。能确定的是,四月到任的苏轼,心情便如后世陆游描写春末夏初的诗句一样,“糁径落花犹片片,拂云新竹已离离”,极为惬意。
徐州果真麦丰米熟,官务不多,确是苏轼预见的清闲之所,故其时间都用在了迎来送往和诗词歌赋之上。
首先是收到继自己为密州太守的孔宗翰和郎中赵庾的诗函。孔宗翰以诗谈密州时势,苏轼遂写下《和孔密州五绝》回赠;赵庾虽年至花甲,还是喜开玩笑,在诗中戏言徐州歌伎不如密州,唯一值得称许的是“只有当时燕子楼”。他说的燕子楼虽比不上“江南四大名楼”(即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谢朓楼),却也是无人不知的徐州名胜。该楼建于大唐贞元年间,是当时武宁军节度使兼徐州刺史张愔特地为爱伎关盼盼所建。但天妒良缘,建楼两年后,张愔于赴京途中病故。关盼盼感其深情,誓不嫁人,在楼中孤苦度日达十余年。曾在张愔部下任职多年的员外郎张仲素在长安见到白居易后提及此事,曾在徐州亲见关盼盼舞姿的白居易闻她守节至此,大为冲动,读过张仲素诗后,也写下三首诗以和。此时的苏轼,还未亲临燕子楼,要到一年多后,他才在一个秋日薄暮孤身前往,为燕子楼和关盼盼写下情动肺腑的千秋绝唱。
刚入五月,苏轼又接司马光来函,内附一篇《独乐园记》。司马光在文中称自己在洛阳“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为园”,细写自己的园中生活是“投竿取鱼,执纴采药,决渠灌花,操斧伐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惟意所适……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故将其“命之曰独乐园”。苏轼如何不知,司马光流传宣传“独乐”,乃因八年前王安石变法后,礼部侍郎范镇上疏称变法是“残民之术”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离朝,居洛阳编纂《资治通鉴》。今将新园题名“独乐”,自是编书之余,只愿与山水自然为伍,绝口不问政事了。读过司马光的笔墨后,苏轼百感交集,且不说司马光对苏氏一门皆有恩德,就其才学而言,全球鲜有人能与之匹敌,今退居洛阳已达六载,苏轼不能不为之惋惜。今日苏轼,经密州任上熬炼,已体会外任颇能造福一方,未尝不是人生志向的实现。但司马光愿为“独乐”,还隐含劝诫苏轼多入自然之意。作为同样被王安石和新法修理过的苏轼,如何看不出司马光在“独乐”中模糊透出的不甘和抵牾?
左思右想之下,苏轼终还是提笔回函,并写了一首二十六行五言诗《司马君实独乐园》相赠,全诗末了以“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师长西席,年来效喑哑”的坦率,表明了自己对司马光思想的理解和劝其入政的苦心。清代学者王文诰在《苏诗总案》中称此诗“无攻击之意……是常梦不醒人语矣”,但正好是“常梦不醒”,才见出苏轼脾气为先,从他生平来看,这种“常梦不醒”的状态贯穿今时今后,也就决定了苏轼的不宜官场,决定了他终至发出“人生如梦”的喟叹,但也末了令人创造,苏轼的“不醒”,不过是面对世俗与官场的“不醒”,而非面对人生深处的“不醒”,更不是对生命认知的“不醒”。
二
苏轼在徐州写诗不少。古人题诗,大都题于墙壁亭阁,苏轼也不例外。他有很多诗因出于即兴,嫡黄花后多有遗忘,譬如七绝《登望谼亭》。“河涨西来失落旧谼,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壑无寻处,千里禾麻一半空。”就诗本身来看,不算佳构,以是忘却也正常。当他后来听到徐州人吟诵时,仔细想了想,才有了“乃知其为仆诗也”的确认。
这首诗给后人供应的信息是,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州遇大水。关于这次洪灾,清代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有触目惊心的描写:“是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乙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落。澶州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西)曹村落决堤,大水东南而下,毁城之多,坏田之广,实乃罕见。到八月二十一日时,大水围困徐州,“水深凡二丈八尺九寸”。这天,苏轼至徐州履任刚刚四个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作为太守,苏轼急速开始阻洪。与在密州时碰着的蝗灾比较,洪灾令人更加畏怖。自古谓“水火无情”,便指二者随时有夺人性命之凶。因徐州城南有吕、梁两山环绕,大水触山而返,竟至“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余”,全部汇于徐州城下。全城顿时“东薄两隅,西入通洫,南坏水垣,土恶不支”。眼看水将灌城而入,徐州的富人争相逃离。苏轼闻讯大怒,厉声说道:“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当即敕令,命士卒将刚刚逃出城的富民驱回城内,严令禁出,以得众志成城之效。
随后,苏轼又亲入武卫营,将卒长唤至身前说道:“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感佩说道:“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
”当即命众禁卒短衣赤足,各持畚锸外出。苏轼心下稍安,又急召五千民夫,往东南筑堤。该堤从戏马台一起筑至城边,全堤高一丈,长九百八十四丈。当“附城如环”的大堤筑成,大水也终被阻于城外,全城民心得安。但此时大水虽堵,大雨却昼夜一直,河水又随之暴涨,乃至“城不沉者三版”。亲守城头的苏轼再次敕令,将数百船只“分缆城下,以杀河之怒”。在苏轼的官场生平中,这段无歇无休的治洪生涯最为触目惊心,但他无暇多思,连居室也索性迁至城头,内外巡行,过家门不入,随时命人分堵而守。终于,到十月十三日,“昼夜亲作”的苏轼在城头见大水“忽然归壑无寻处”。诗句不免夸年夜。这天,大水乃“渐退,城遂以全”。
三
大水虽退,不即是不会卷土重来。就苏轼的徐州生活来看,这次洪灾也像一道冥冥中的分水岭,将他“闲终日”的日子一并卷去。有此亲历,苏轼自不敢掉以轻心,带王户曹相和监徐州酒税吴琯等人出郡察看。苏轼发觉,要防黄河再侵徐州,最好的办法便是修建石岸,遂上疏朝廷,请“拨款拨粮,征民修岸”。不料,朝廷对此奏不从。失落望之余,苏轼给好友、刚至开封府为判官的刘攽去函,不无遗憾地说道:“擘画作石岸,用钱二万九千五百余贯,夫一万五百余人,粮七千八百余硕……虽用度稍广,然可保万全,百年之利也。”
翌年即元丰元年(1078)正月十八日,朝廷下诏奖谕苏轼的防洪之功。对苏轼来说,甘心诏令是“允修石岸”,但知朝廷不欲耗资,遂动机一转,再次上疏,将“修石岸”之奏改为“修木岸”。他算得详细,修木岸只需“夫六千七百余人,粮四千三百余硕,钱一万四千余贯”,不仅工费减去一半,效果“虽非耐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岁月,待河流之复道”,并不无急迫地说“惟便得指挥,闰月初便可下手”。同时,苏轼又再给刘攽和刘攽之侄、时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的刘奉世去函,望他与刘攽能力言于朝。这一次,神宗准奏,赐钱发粮,苏轼得以在徐州外督民筑岸,终极建起木岸四条,“以虞水之再至”。二十三年后苏轼去世,苏辙为其撰墓志铭时,仍有“徐人至今思焉”句,足见苏轼在徐州时日虽短,却以造福一方的政绩令州人思之留恋。
四
还是元丰元年(1078)正月,木岸竣工前后,苏轼意外接到京师国子监教授黄庭坚(字鲁直)的赠书和随书附来的两首诗歌。
关于黄庭坚,苏轼早在熙宁五年(1072)十仲春时就闻其人、读其诗。当时苏轼以杭州通判身份前往湖州察看,时湖州知州孙觉设宴相迎,并于筵席年夜将一些诗文交予苏轼过目。苏轼读面前笔墨,惊其超逸绝尘,忙问作者是谁。孙觉回答说是半子黄庭坚之作。苏轼赞黄“如精金美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后来给黄庭坚去信说道:“礼部苏公在钱塘,始称鲁直文章,士之慕苏公者,皆喜道足下。”意思是黄庭坚的文章被苏轼夸奖后,天下文人纷纭向黄庭坚祝贺——足见苏轼影响之甚。
当时苏轼收到黄庭坚的诗书后颇为喜悦,写了首十六行的《春菜》诗相赠,后者收读后步其韵,再写一首回赠。这也是黄庭坚首次步苏轼韵作诗。当苏轼读到末了“公如端为苦笋归,嫡青衫诚可脱”两句时,对身边人大笑说道:“吾固不愿为官,为鲁直以苦笋硬差致仕。”意思是我原来不欲为官,可黄庭坚怎么硬说我是爱吃苦笋而想退休呢。从中可见,苏轼不愿为官是真,但身在官位,就需竭尽全力,证明是时至三月,苏轼在给文同信中,仍忧心黄河决口未塞。但从苏轼当时读黄庭坚次韵诗时的大笑来看,苏轼内心开阔,与自己心仪之人在瞬间便心领神会。
苏轼虽至今与黄庭坚未谋一壁而憾,却终于与另一想见之人在徐州相见了。那人便是后来与黄庭坚同有“苏门四学士”之称的秦不雅观。
苏轼知秦不雅观之名,是在熙宁七年(1074)离杭赴密途中。经扬州一山寺时,苏轼见壁上题有一诗,质量之高,颇感触感染惊。待至高邮见孙觉讯问时,后者将收藏的数百篇秦不雅观诗词捧出。苏轼读后问了句:“向书壁者,岂此郎耶?”孙觉称是,并言秦不雅观曾往杭州拜见苏轼,却逢苏轼外出赈济,未偿所愿;当得知苏轼赴密,料定将过扬州山寺,便预先留诗于壁以盼苏轼一读。苏轼听闻,对秦不雅观大起神交之感,却不料四年后的一天,才“皆至是始见”。
是年,二十九岁的秦不雅观赴京师开封应举,四月途经徐州,携苏轼好友李常荐书拜会。后者刚于三月离徐过淮,途中与秦不雅观相遇而知。当苏轼闻秦不雅观来访,心中大喜,一见之下,尤觉秦不雅观豪俊年夜方、超然胜绝,顿生相见恨晚之感。秦不雅观因赴考在即,不能多留,只在分别时写下一诗相赠,个中“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句令苏轼冲动,也步其韵,写下一诗,以为回赠。从“谁谓他乡互异县,天谴君来破吾愿”句可见苏轼喜悦之情。二人约定,待秦不雅观秋试之后,再同游徐州。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的日后造诣自是压倒一切,但就当时来看,最为苏轼看重的,真还非秦不雅观莫属。苏轼不仅直接对儿子苏过称秦不雅观“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还在元符三年(1100)夏日闻其卒于藤州(今广西藤县)后,痛惜说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足见秦不雅观在苏轼心等分量是何等之重。
能够想象,当苏轼立城头望秦不雅观远去后,一股难耐的寂寞涌至心头。他生平中良朋好友不少,却多数天涯相隔;入仕后,与弟弟更是聚少离多,虽与徐州僚属如舒焕、梁左、傅裼等人有游山泛舟、会饮赏画之举,究竟算不上平生心腹。就苏轼性情看,豁达之人自易与人交往,但内心最主要之域,却非常人能够踏入。今《苏轼文集》中信函颇多,阅读时易见他对来往故人总怀顾虑之情。在送秦不雅观之前,苏轼已在徐州送别不少朋侪,从还算不上深交的前任太守江少卿开始,陆续送别的还有颜复、苏辙、王景纯、李清臣、杨奉礼、李察、郑仅、李常等人,其送别的感伤就在“老送君归百忧集”和“此身与世真悠悠,苍颜华发谁汝留”等句中表示。这些诗句与其说感伤,不如说有难为人察的寂寞,尤其给秦不雅观那首《次韵秦不雅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虽有“一闻君语识君心,短李髯孙眼中见”的喜悦,终极仍掩不住“千金敝帚那堪换,我亦淹留岂长算”的落落寡欢。
人生原来寂寞,尤其人到中年,对生命与情绪的体会自与少年时大不相同。所谓“高处不胜寒”,也便是寂寞的表示。人格越独立的人,越能体会思想深处的寂寞;越是爱慕之友,越易被告别的伤感替代相聚的欢慰。在徐州的苏轼,除了深感寂寞,对去世亡也有了彻骨的体认。首先是苏辙的幼时保姆杨金蝉于熙宁十年(1077)六月十一日去世,当时苏辙尚在徐州,杨氏的墓志铭却由苏轼亲笔撰写。纵不雅观苏轼的创作,祭文、哀诗写得不少,唯墓志铭只写过寥寥可数的十三篇,足见他视去世者如亲人的认同,并祈求“百世之后……尚勿毁也”。随后,苏轼又陆续接到刁景纯、王安国、胡允中、张方平夫人马氏先后去世的噩耗,均以诗文为哭。从其笔下“忍见万松冈,荒池没秋草”等句中,能见苏轼人到中年后的内心薄弱和去世者留给生者的寂寞人间之感。其余不可忽略的是,洪灾更使他理解生命的薄弱。“今日忽不乐,折尽园中花”句已充分解释,看似无缘无端的寂寞总时时萦绕苏轼心头。
到这年秋日,刻骨的孤寂终于淹没了苏轼,也匆匆使他创作出在徐州的顶峰之作。
五
和今人熟习的正月十五、八月十五不同,古时的每月十五都为隆重之日,民间俗称“望日”,意指月圆之日。元丰元年(1078)十月十五日,苏轼与众僚属会聚黄楼不雅观月。黄楼位于徐州东门之上,该处原有霸王厅,相传不可去坐。自熙宁十年(1077)治洪之后,“民以重生,全城修缮”,苏轼遂拆厅建楼,以为镇水。至于楼名,秦不雅观有所阐明,“以为水受制于土,而土之色黄”,苏轼便将这座新建的十丈高楼命名为“黄楼”。
十五月圆,苏轼等人在黄楼不雅观月,对酒吟诗。席上有同寅应景作诗后,苏轼步其韵,也写了首名为《十月十五日不雅观月黄楼,席上次韵》的七律,如下:
中秋景象未应殊,不用红纱照座隅。
山下白云横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屠。
未成短棹还三峡,已约轻舟泛五湖。
为问登临好风景,明年还忆使君无。
饮酒赏月,原为人生快事,在苏轼这首诗中却看不到丝毫快意,从“未成短棹还三峡,已约轻舟泛五湖”来看,能创造苏轼内心不无悲惨之感。前句采取了唐代李源与圆泽“三生石”的典故,二人上荆州、出三峡、次南浦,目的地未到,圆泽就在维舟山下去世,临终说与李源缘分未尽,李源于十三年后在杭州果真见到圆泽后世已为牧童;后句则引用了《吴越春秋》中“范蠡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的传闻。大凡引典,自是典与当事民气境吻合。因此能知,眼望十五圆月时,苏轼心情起伏,他应是想起苏辙,又一次涌上退隐之想。他与苏辙早就约定,退隐后兄弟同居,尽享伯仲明日亲之乐。这是朝堂上失落意的士大夫们随意马虎涌起的动机。对苏轼来说,此刻虽为徐州太守,但所做之事毕竟有限,内心渴望“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来宾,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的抱负如不圆之梦,乃至连建“百年之利”的石岸也心愿难酬,连续留下去又能做些什么呢?但“吾侪眷微禄”,也是他在徐州写下的活生生的现实之句。还能料到的是,自熙宁十年(1077)仲春苏轼接诏知徐州算起,至元丰二年(1079)春日,便又三年期满,该到自己离开徐州之时了。“悟此人间世,何者为真宅”,委实难言。下一站会是哪里呢?无论什么地方,无非另换一州当太守罢了,以是,“明年还忆使君无”的句子如何不感伤?若真能如范蠡那样泛舟五湖,至少能做一回完全的自己吧?
大约从苏轼诗中看出其心情压抑,众人转换话题,谈及燕子楼和关盼盼。苏轼听闻,更为感慨。关盼盼十余年孤守空楼,委实寂寞之极,却究竟是她对选择的实现。自己呢?无数年里的无数想法,没哪个能由己选择。当夜深席散后,苏轼回府就寝,居然梦见自己登上燕子楼,醒来后大为惊异,觉有冥冥中的天意嘱自己前往。
明天将来诰日,苏轼遂在薄暮时撇开一众人等,独自前往燕子楼。
六
彼时的燕子楼已早非张愔所建时的样子容貌。早在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朱温命部下大将庞师古攻打徐州,时为徐州行营兵马都统的时溥兵败将亡,携百口登燕子楼自焚。到苏轼所在的北宋期间,被烧毁大半的燕子楼尚未重修,因此面前所见不过一座荒凉残楼。缓步逡巡的苏轼只感深秋风寒,明月如昨,面前统统便如自己内心无端堆起的废墟,除了寂寞还是寂寞。寂寞不是表面的孤身只影,而是内心无人能入,很多话也无人能诉。“古来圣贤皆寂寞”,不到一定年事,真还无法体会。苏轼未必以为自己是圣贤,寂寞之感却环抱不散。
苏轼此时难免想抵家乡,父母、正室早在“短松冈”里永眠。人生看起来不过如此,先人会去世在自己之前,自己又将去世在后人之前。李白不是说过吗?“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苏轼摇摇头,自己虽喜酒,酒量却不大,“独饮一杯,醺然径醉”。数月前往山村落巡视,还写下“日高人渴漫思茶”句,真不像李白那样时时需酒。但茶也好,酒也好,人生不便是“三万六千日”吗?现实总一次次击败空想。彷佛真正实现空想的,只有在面前孤楼中度过半生的关盼盼。又想起当年白居易为关盼盼写的诗,“满床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这便是刻骨入髓的寂寞,但关盼盼的寂寞有思念为核心,自己却不得不四处飘零;更何况,无论关盼盼如何寂寞,此时早归尘土,自己却仍在活着的本日品尝一点一滴的寂寞滋味。
关盼盼若还活着,会是自己的知音吗?
苏轼从残楼北面登上,见表面秋夜荒凉、废园荒凉、小径荒凉、水塘上的荷叶荒凉,自己内心更加荒凉。今夜索性不回去了吧,在楼内住上一夜。既是寂寞的一夜,也是排解寂寞的一夜。心念到此,苏轼果真不再回府,就在楼中入睡。意外的是,昨夜梦见燕子楼,今夜竟然梦见了关盼盼。苏轼自不知关盼盼是何样子容貌,但此夜梦中,那个凄然起舞的女人不是关盼盼又会是谁呢?醒来后,苏轼情绪难抑,写下一首《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词前有一行“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的自叙,全词如下: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宅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从这首《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和三年前写给亡妻王弗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旬日夜记梦》中可见,当苏轼豪放的一壁消逝时,时感凄楚的一壁就凸显了出来。在苏轼这里,他不会因一次大略的凭吊而抒发大略的感伤,而是深觉千秋万代的人间何其寂寞!
今日在燕子楼凭吊,多少年后,自己不也将告别人生?建在此处的黄楼,日后会不会也有人登临凭吊自己呢?岁月流逝,所有人的人生也一同流逝,有谁可以阻拦流逝吗?在冷漠而不可见的韶光当中,自己究竟算不算得上尘埃?面对人生的终极,自己究竟该报以激情亲切还是冷漠?
没错,此刻自己虽活着,但活着的体会真是感伤多于欢愉,哪怕望一眼故乡方向,也令内心痛楚难当。千百年后,有人知道自己的情绪体会吗?有人会拥有和自己此刻一样的心绪吗?在无穷无尽的岁月面前,人的欢愉、感伤、孤独、爱恨等,又究竟算什么呢?今人读这首《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词,还能创造,苏轼不无一种当代语境下的虚无感。“虚无”虽是一当代词汇,但不即是古人就没有和今人相同的感想熏染,正如今人能够体会古人的感想熏染一样。
关于这首词,事后还有个故事,南宋曾敏行记录在他的《独醒杂志》第三卷。故事讲苏轼尚未公开这首词时,竟听到城中有人吟唱。惊异之下,苏轼问吟唱者何处得来该词,对方说听巡逻士卒唱过。苏轼又将士卒叫来讯问,士卒说自己数夜前在张建封庙中值宿,模糊听得有人吟唱,因自己稍知音律,就把词句记下传了开来。苏轼闻言一笑,不做深究,料是自己当夜吟唱时,恰好被听去了。能被急速传诵,足见苏轼该词的传染力,令人甫一过耳,就刻骨难忘。
七
果如苏轼所料,当冬去春来,到元丰二年(1079)仲春时,他已得到自己将“移知湖州”的。在徐州的末了一个春天,苏轼内心始终都不惬意。首先是收到秦不雅观来函,称“秋试失落利”。苏轼即刻回函安慰,“此不敷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话虽如此,苏轼终还是在诗中写下“底事秋来不得解,定中试与问诸天”,以表达自己的愤愤不平。但与秦不雅观落第的比较,欧阳修之子、年仅三十四岁的欧阳奕和既是好友又是从表兄的文同的去世讯令苏轼更感彻骨之悲。
为文同写过祭文之后,苏轼与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遹、王肄、苏迈、羽士戴日祥及舒焕之子舒彦举等人游泗水,登桓山,入石室,以愉快扉,时戴日祥操琴为歌,苏轼也终有“想象斜川游,作诗寄彭泽”的暂时解脱,并写下《游桓山记》一文刻石。他当时还无法预见,他诗中以“彭泽”代指的陶渊明会在自己日后匆忙跌宕的人生中成为压倒一切的精神支柱。苏轼回忆入仕以来,从凤翔到开封,再从开封到杭州、从杭州到密州、从密州到徐州,每次离开一地,心情都不一样。对苏轼来说,徐州是自己入仕以来所处最为艰辛之地,也是心情最为起伏之地,更是人到中年体会到寂寞原为人生实质之地。
但苏轼到底是苏轼,终不会让寂寞与感伤盘踞内心。元丰二年(1079)三月初,命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的诏令正式到达。眼看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苏轼至国子监通判田叔通家中做客。宴饮中,田叔通招歌女于筵前以舞助兴。苏轼一边不雅观舞饮酒,一边填下两首《南乡子》相赠。第二首的末了一句“唱遍山东一百州”,似是总结自己在徐州的生活。解释一下,宋时的“山东”乃指徐州。对苏轼来说,两年来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体会什么心情,自己究竟识遍徐州、走遍徐州、唱遍徐州,离开也没什么遗憾可言。但人生的很多离开,无异于流落,流落又无异于寂寞。以是,苏轼告别徐州时的心情就和告别以往其他地方的心情有了格外的不同。这是岁月带来的深化,也是人生体悟带来的深化。当它们落到纸上,就成了苏轼写给徐州的末了一首词。
词牌是他极为偏爱的《江城子》,副题则当然是“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
回顾彭城,清泗与淮通。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苏轼在这首词中的感伤与柳永词的婉约很不相同。柳永词每每渲染过多,苏轼词则在感伤之下依然有股情绪纵横——不纠缠某个细节,但细节又自然而然地在个中涌现。这是苏轼与生俱来的格局所决定的。同样写到感伤,苏轼能给人以开阔的背景,使人体会到他磅礴的内心。
携眷离徐州时,正值烟花三月。当年从京师赴湖州上任,苏轼先至陈州,与张方平和苏辙相聚。此番动身同样如此,苏轼并未直接南下湖州,而是先西行至南都,与时为南都留守的张方平及在张方平手下任判官的苏辙相聚。这是苏轼最为顾虑的两人,除了他们,苏轼真不知何处何人才能排解自己内心的“流落”之感。在南都勾留半月之后,心绪渐复,才终于南下湖州。路上有点不同的感想熏染是,以往数次履新都是去陌生之地,这次去往的湖州却再熟习不过。当年在杭州任通判时,苏轼多次前往湖州赈济。才子多爱江南。在苏轼眼里,湖州既是旧地,也是自己喜好之地。从南京南下,一起过宿州、龟山、淮水、高邮、金山、京口、松江,当真是“来往三吴一梦间”。当他于四月二旬日到湖州上任后,以为可过上“欲伴骚人赋落英”的日子了,却未能想到命运为了造诣他,已决定在这里给他最惊惶失措和最深的人生重创。这也是苏轼体会过的活着的原形之一:不知道来日诰日将发生什么,只要它来临,大家都得服从它带来的统统后果。
(原载于2023年第4期《创作》)
远人,197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等千余篇作品,散见于《公民文学》《中国作家》《随笔》《天涯》《山花》《文艺报》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诗集、近体词集、传记等个人著作30部。获湖南省十大文艺图书奖、广东省第二届有为文学奖·金奖、深圳市十大佳著奖等数十种奖项。有部分作品被译介外洋,其译文涉及英文、日文、匈牙利文。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