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很多学生可能以为学诗只是为了考试而已。但事实上,诗歌的浸染远不止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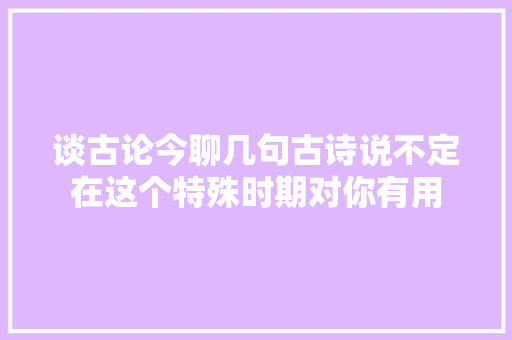
为了考试,那只是实用,除了这个实用,诗歌还有为人生的大用。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不雅观,可以群,可以怨。”“兴不雅观群怨”是最早的关于诗歌浸染的论述。
《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敷,故太息之,太息之不敷,故咏歌之,咏歌之不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以是,诗的浸染大着呢!
平时学了诗,彷佛没什么用,到了某个特定的时候,忽然创造那些诗句就从心里一下子蹦出来了。
本日就和诸位聊几句在这个分外期间,你可能会用得到或者想得到的几句古诗。
一
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
这是出自唐代墨客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名句,近乎妇孺皆知。野草有其强大的生命力,野火无论如何多么凶暴,但野草总是东风吹又生。
现在,这个诗不仅仅用在形容野草,也用来形容统统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东西了。
比如,最近的某篇文章,被灭掉,但又在更多的地方复活,又被灭到,又在更多的地方以不同的形态复活。这不便是范例的“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吗?
与此诗句相类似,还有去年有一段韶光由于《经典咏流传》节目而大火的一首小诗。
苔
【清】袁枚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白日不到没有关系,我的青春我来做主。虽然我的花蕾只是如米粒大小,但是并不妨碍我像牡丹一样绽放。这不便是革命的乐不雅观主义精神吗?每个人虽然都很弱小,但是每一个弱小的生命,都该当学习“苔”的佳构德,要有一种韧劲,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而不是只是如虫豸一样无知无觉地活着。
二
横算作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是出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题西林壁》中的诗句,后两句是“不识庐山真面孔,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我们局限在此山之中的时候,是很难识得清山的真面孔的。须要故意识地跳将出来,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一看,去瞧一瞧,然后才创造原来远近高低各不同。
所谓“当局者迷,察看犹豫者清”。有些时候纵然是察看犹豫者,如果我们只是相信我们自己所乐意看到的,相信我们自己所乐意听到的,而对其他的统统信息,都采纳一种选择性失落明,选择性耳聋的状态,那么,无论我们见了多少,听了多少,终极都只不过是盲人摸象而已,只触碰到了自己触碰的那个部分罢了。
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有“草色遥看近却无”一句,细细揣摩,这一句不仅仅是在说“小草嫩嫩的绿绿的,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一定程度上,何尝不是和“横算作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样,解释同一个一个道理,那便是我们要拉开间隔来看,有些事情,太近了看是看不清楚的。
三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唐代墨客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的诗句,这句的好处是虽然承接着上一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而来,看似只是在写想要看到更远的景物,就要再上一层楼。
但是,这样一句看似实写的诗句,却不能不让人产生更为深入的遐想。在人生中,在历史中,都该当努力站得更高,然后才能看得更远。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中,有一句与此意思比较靠近。“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只不过这一句更为直白而已,把宋诗的说理的特点表露无疑。
当我们“身在最高层”的时候,才能打破历史的重重迷雾,看得更辽远,更清楚,更透彻。
正如革命先驱孙中山师长西席曾经说过:“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不过这一句并不是孙师长西席的原创,是他化用了司马迁的文句。 “夫阴阳四季,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去世则亡。”
这个中的“之”指代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客不雅观规律,无论是谁,违背了这客不雅观规律,等待他的都只能是灭亡而已。
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落。
这是宋代墨客陆游的《游山西村落》中的诗句。在这首诗中,这两句诗原来是在描述墨客前往山西村落途中所见之景,山回水转,正担心无路可走,忽然间又柳暗花明,一转眼,又是一处村落落。
这个诗句,被后人很自然地授予了其余一层更深的含义,那便是仿佛到了绝境,忽然又有了新的活气。所谓“绝处逢生”“暗室逢灯”“绝渡逢舟”等等,均是这个意思。
在人生中,也常常会有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遭遇,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以为,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看开一点,佛系一点,随缘一点,自然可能可能这个原来看似过不去的坎也就过去了。
还有一条路是什么呢?那便是要拼一下。借用最近盛行的一句话:“早知有今日,老子到处说”。鲁迅不是说了嘛,“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虽然,“时期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便是一座山。”但是,当这座山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要扛得住。一座山怎么个人能扛得住呢?确实很难,但是如果有了“老子到处说”的精神,说禁绝期间的灰尘落在每个人身上的几率就小一些。
法国历史学家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历史的韶光区分为地理韶光、社会韶光和个体韶光,进而表述为永劫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他认为永劫段思想深刻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
只管在历史长河滔滔向前的过程中,可能碰着旋涡,可能碰着乱流,但是,那只不过是历史的短时段而已,我们每个人都该当充满信心,昂开始,挺直腰板,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