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中有两人,有着最壮志的豪情,却过着最悲惨的人生,亦成为了患难的至交,难得的心腹。
杜甫和岑参,初识与相似,渐远与不同,终极又怜惜于懂得,盛世没有磨灭各自的初心,浊世没有打断他们的顾虑。
交往了一辈子,却也遗憾了一辈子。
这世上,一时的朋友不难,一世的朋友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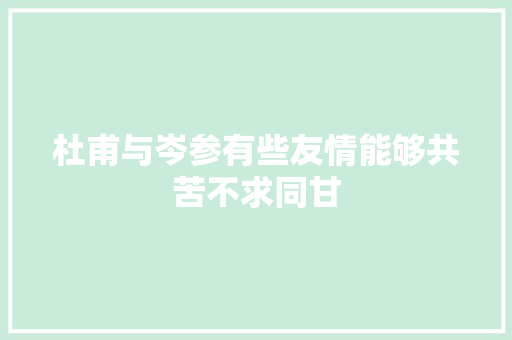
由于共苦,以是相知
真正的友情,并非由于双方故意拉拢,是一种冥冥之中惺惺相惜,让彼此不知不觉靠近。
杜甫岑参的相交,大概是第一次瞥见对方,就陡然一惊:他仿佛是这天下上的另一个我。
杜甫常骄傲地说:“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
这可不是吹牛,他们家族历朝历代人才辈出,尤其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与陈子昂齐名,受武则天赏识,自诩:
论写文章屈原和宋玉也只能为他听差,论书法王羲之也只能望其项背。
岑参的家族更了不得,他出生于“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的累世公卿之家,曾祖、伯祖、伯父都因文墨非凡而名动朝野,一门三相是真正的大唐光彩。
站在仕途顶峰的古人仿佛已经划定了后人的义务:继续家族光荣的意志,背负东山再起的希望。
自小资质聪慧的杜甫和岑参背负着相同的义务,也走向了相同的道路——入仕做官,光耀门楣。
然而,杜甫和岑参都在20岁那年来到长安,四处献书阙下,却苦于无人举荐。
现实见告他们:长安城到处都是有才的人,而能与这天下规则对抗的,从来不是才华。
岑参辗转10年才考上进士,守选三年熬到头,才换得一个扼守兵器的九品小官。
当他感叹“参年三十,未及一命”之时,比他大六岁的老杜更惨。
杜甫“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如果说第一次科举还是年少轻怠,第二次则是碰着了百年难遇的大奸臣李林甫,其以一句“野无遗贤”,便让全部参考的士子落选。
人便是这样,见识过顶峰的辉煌,哪甘于脚下的平淡。他们不甘心,也不想再等待。
岑参打破着文人之弱选择出塞,而杜甫忍耐了诗人意气选择改变。
然而岑参飞沙走石赶赴塞外,却依旧无人重用,第一次出塞就戛然而止在寂寂无为里,出了个寂寞。
杜甫忍住肉麻为驸马爷书写“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也只辗转换得卖力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
两个出身非凡,才华非凡的人,在成家立业的坎节上,经历着同样的中年之难:
心中光芒万丈,但现实无比窝囊。
相同的经历,注定了两人的行动交集又惺惺相惜。
当岑参回到长安,约老友们一同登楼赏景,谈起人生和空想,在彼此眼中瞥见的是无可奈何的沧桑。
除了至心相待的老友,没有人会在意失落败人的苦难。
正如杜甫在岑参出塞后寄诗上说,这世道不过是:“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
偌大的长安,不过多了几个失落意的文人,繁华的盛唐,却容不下这些热血的才子。
不能同甘,只因三不雅观
都说,浊世出豪杰,时势造英雄。
755年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唐玄宗时期即将划上句号。
此时的岑参正二度出塞,塞外的风、天山的雪、轮台的月让岑参写下了不少壮丽的诗篇,也重燃着他建功的热血。
但没想到,塞外尚未建功,却等来了上司奉命回朝叛乱却被赐去世的噩耗,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他只能匆忙班师回朝。
再回来,已是物是人非。
老友杜甫,从长安一起逃跑去追随新皇肃宗,见到肃宗时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漏两肘”,让天子大为冲动,被封为左拾遗,潦倒半生彷佛终于等来自己迟到但并未缺席的成功。
“思君令人瘦”的杜甫,知老友归来很是高兴。
他看到岑参迷茫痛惜,又深知他仍怀着建功报国,振兴家业的空想,便极力向肃宗举荐岑参:“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
肃宗正欲招揽人才,让岑参补充了右补阙的空缺。
拾遗、补阙,都是给天子提见地的言官,品阶不高但地位还行,也算是近天子了。
杜甫很骄傲,这是他这辈子做过最大的官了。
他兢兢业业,忧国伤时,为国效力。
当两京收复,皇位稳固,平叛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这样的朝局更须要文人的赞颂。
贾岛写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的颂诗,杜甫拉上岑参纷纭点赞、唱和。
比拟贾岛父子世代执掌帝王诏书,“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的殊荣,杜甫以“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点缀升平,岑参却在这种应酬诗中写道“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真正见证过边关战乱和山河血泪,经历过同寅被杀,奸倭当道,长安失落守,天子出逃,岑参身在朝堂,但“剑”、“旗”、“星”、“露”仍在贰心中,边塞墨客与宫廷墨客之别,略见一斑。
他也曾如老友一样平常安身立命,做一个拿笔打仗的言官,毕竟“令初下,群臣进谏,熙熙攘攘”,但“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二心坎无比空虚,对杜甫说:“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
不是无事可谏,而是朝堂上没人乐意再瞥见真实人间。
文辞才华曾是岑参最骄傲的成本,如今只能用来歌功颂德,他深悔:“早知逢世乱,幼年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
贰心里却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或许本不该回来。
在随老友写完和诗的第二年,岑参就马一直蹄地再次出京,任虢州长史。
杜甫见高适、岑参两位老友皆离京远去,写下了自己不舍老友们的孤独与悲惨:“海内有名士,云端互异方。”
朝廷像座围城,进去或出来,坚守或离开,每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是经历改变了选择,是心境选择了各自的路。
殊途同归,彼此释怀
可是缘分便是这样,有些人,分不开,有些情,断不了。
真正的老友之间总有一种笃定和默契,纵然光阴匆匆,道路不同,但人生漫漫总有缘分殊途同归。
岑参走后不久,杜甫因卷入一起政治纷争,被肃宗嫌弃,弃之如草芥。
见识了官场阴郁又领略了人情的冷暖,他举家如逃难般迁徙,落魄如托钵人,终于来到了成都。
在成都,有几位故交照拂,他在浣花溪边建筑一草堂,暂得落脚之处。
此时的杜甫已经不愿掺和官场的勾心斗角,亦看淡系统编制内的功名利禄,只愿:
“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
两位老友数十年未曾相见,也疏于书信联系,可是心中一贯牵挂着彼此。
没想到几年后,命运的齿轮再次重合,岑参被贬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
杜甫得知岑参即将来嘉州履新,他渴望与老友在成都相见,寄信一首:
“不见故人十年馀,不道故人无素书。愿逢颜色关塞远,岂意出守江城居。”
只管嘉州刺史是岑参这生平最大的官衔,但他早知道此时的自己上无权改政局,下无兵平盘据,去了四川恐怕也只是一个空架子。唯一的期待,大概也是与老友相逢。
没想到天意弄人,岑参走到汉中时,蜀地发生叛乱,加之交通不便,他并没有准期履新,直到第二年的秋日,才困难地来到四川。
此时的四川在叛乱之后,贼寇当道,尸积江湾,野兽出没,血流江河。
杜甫在成都的日子愈发困难,又思乡心切,已经乘船离开了成都,真正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天意弄人,岑参和杜甫都在蜀中待了许多年,却阴差阳错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四川,没有成为他们末了相逢的地方,却成为了他们再次靠近的契机。
他们都曾执着于奔赴功名,但现在只见蜀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们曾立志效忠于朝廷,但朝局变化多端,地方敛财伤民。
空想幻灭让他们真正见识到一个连人命都不顾的朝代,也开始反思心中的光荣与梦想,是不是放错了地方?
“从前迷进退,晚节悟行藏。”
岑参在四川也逐渐学着老友的样子,将生平的执念放下。
“数公不可见,一别尽相忘” 也怀念着与老友们把酒言欢,畅聊人生的好光阴。
功名不是真正的救赎,年纪的增长才知道现世安稳的重量。
769年冬,岑参在四川的一个小堆栈孤独去世,他究竟成为了一个异域人。
第二年冬,杜甫在前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他究竟成为了一个流落客。
两个在晚年渴望北归回家的人,究竟未能如愿以偿。
这世上,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情意都走不长远。
杜甫与岑参恰好相反,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心灵相通,守望相助,而当人平生稳之时,却与对方渐行渐远。
个中自然有命运的造化弄人,更多的是,他们虽然相似但并不相同,时期变幻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我的权利,各自忙乱的人生, 更有不愿重复他人之路的执着。
但末了,共同的发展让他们懂得,共苦让彼此有患难的真情,不是一方的名声、名誉、快乐、财富附加的重量。
真正的交情,即便没有参与对方的好光阴,也会让自己变得独立倔强。
作者 | 北方有佳,怡然自乐小女博,不雅观察社会爱生活
图片 |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