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仆人聪为聂绀弩所作的小像
最早知道聂绀弩名字,是听沪上百岁老作家欧阳文彬谈及。她说,1940年在桂林新知书店,事情之余,店里常请一些文化名人来讲课,那次请了刚到桂林的聂绀弩,大家在书店打烊后,又联系附近的一些进步书店,搬来板凳,支配了讲堂。可讲课韶光超过良久了,仍不见聂的身影,大家丧气地把凳子还原后回家。几天后,欧阳在店里偶见聂绀弩,怪他怎么可以失落信,害得大家搬凳子白忙活!
他不讲缘故原由,也不表示道歉,而是嘻嘻一笑:“凳子在哪里?我帮你搬回去”。说得欧阳哭笑不得。后来,欧阳对聂绀弩的印象却不错。聂绀弩在桂林办《力报》副刊,对书店进步青年的来稿,能刊尽刊,极力扶持。“皖南事变”后,新知书店、读书书店遭到伤害,勒令三天内停业,书店就抓紧开大卖场,读者踊跃,买卖出奇的好。聂绀弩这时写杂文《韩康的药店》,刊在《野草》杂志上。一韶光,“韩康的药店”成了进步书店的代称。
还是说《元旦》。此书由喷鼻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初版,定价港币一元三毫”,这“毫”在内地大概便是“角”吧,印数三千册。小小的六十四开本,像袖珍型的口袋书。封面颇有特色,书名《元旦》两个留白的老宋体,上部是一幅丰收归来的剪影,左下是一簇留白的火焰,除了留白和黑的剪影画,封面底色是一片大红,彷佛象征着新中国就要出身的喜庆。
聂绀弩新诗集《元旦》,1949年喷鼻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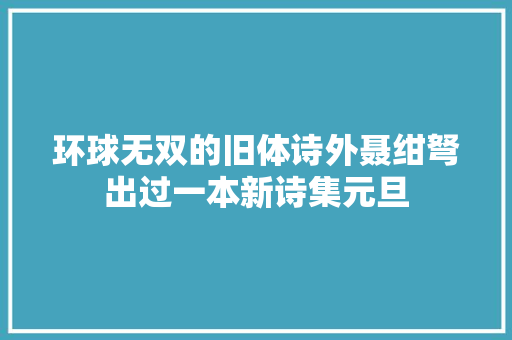
在书的末了,有一个两页通版的求实出版社书目广告,有十一种新书出版信息,另有三种重点先容的书,即黄药眠的《论走私主义的哲学》,以及聂绀弩的两书, 一是《二鸦杂文》,说“绀弩师长西席的杂文,一向是读者爱读的好文章,本书共十万余字,分高下两辑,包括至反动派逃出南京时为止的杂文选集,下辑全部是妇女问题的作品,有不少分外而新鲜的见地,尤为妇女们及关心妇女问题的读者,不可不读”。在先容《元旦》一书中写道:“作者自己说:‘当愤怒的时候,我叱骂了;当欢欣的时候,我歌唱了’。的确的,从这激情亲切洋溢、音响铿锵的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作者心情的欢欣愉快。墨客以火山一样地爆发着激情亲切的火焰,在歌唱着新生的统统,可以说是时期的真实的记录,是歌颂公民解放战士的史诗”。这段笔墨,大体概括了《元旦》的主题和内容。
《元旦》共收是非诗歌十首,每首诗的末了,都有写作日期,韶光跨度从1936年到1949年的十多年间。第一首诗稍长,诗题为《论元旦》,副题是“为一九四九年元旦作”。诗分八个章节,“一、绪论”,共九行,末了两行是:“真的元旦是真的春天的开始/只有真的春天才有真的元旦”。中间依次是:历史的春天、公民的春天、生活的春天、感情的春天、思想的春天,接着是“七、结论”,诗中写道:“春从冬天来/还带有冬天的寒意/往后的日子/就一每天变暖/春天/再不会离开我们了!
”。作者大概意犹未尽,又写下“八、余论”:“让垂死的人们说:/春天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去世了!
”。以此来反证公民的心情:“欢迎我们的春天/走进我们的春天!
”这是作者借用论文形式,用诗句来抒发对春天的渴求和期盼。诗集的第二首诗是《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可以说是长诗或组诗了,由四首诗组成,即《比喻》《我们》《日出》《报答》。《报答》的末了一节是《给毛泽东》:“新天下的创造者领路人/四切切七千万双眼睛望着你/四切切七千万双耳朵听着你/四切切七千万双手推戴你/四切切七千万颗心爱着你!
”。全诗近六百行,读来真是一气呵成、一泻千里。
更早的一首诗写于鲁迅逝世的1936年,诗题为《一个高大的身影倒了》,他开头就写道:“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那走在前头的/那高擎着倔强的火把的/那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着歌的/那比统统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那天,聂绀弩与张天翼、胡风等十二个鲁迅弟子,抬着鲁迅的灵柩,一起走到虹桥万国义冢。1939年,他又写下《收成的时令》,副题为“为鲁迅师长西席三年祭作”,聂绀弩对鲁迅崇拜且敬仰,其杂文写作便是以鲁迅效仿模范,曾出版鲁迅研究专著《高山仰止》。《元旦》出版后的1949年9月,他写长诗《山呼》,刊在《光明日报》一整版。他以此诗庆祝新中国的出身,可惜此诗未及收入《元旦》,却是他揭橥的末了一首新诗。他的新诗,不是月牙派或当代派,是左翼作家同盟提倡的现实派,普通易懂,直抒胸臆,与他后期的旧体诗有着一脉相承的格调。
聂绀弩(1903—1986)原名聂国棪,笔名绀弩、耳耶、二鸦等。幼时在家乡湖北省京山县读学堂,1921年考入上海高档英文学校。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曾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并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皖南,任新四军文化专员,编辑军部刊物《抗战》,后到金华,编辑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刊物《东南战线》。之后,在桂林编《力报》副刊等。1943年到重庆,担当多家报刊编辑。1949年7月到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及开国大典。之后受组织遣派,赴港任喷鼻香港《文申报请示》总主笔。1951年回京后,任公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等。
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
聂绀弩对新诗打仗甚早。他回顾道,胡适《考试测验集》一出版,他就读到了。又从朋侪处借得郭沫若的《女神》,“借一盏洋油灯的微光,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那往后,对付新诗竟至少有了一点好奇心了,开始在书店里找书,起初自然是找新诗,有一回买到一本《星空》”(郭沫若新诗集)。1942年,他为彭燕郊的诗集《第一次爱》写过长序,纵横评说。以是说,聂绀弩对新诗并不陌生,只是写作的量并不多。结集成新诗集《元旦》,就区区十余首诗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相应组织上写诗的号召,在北大荒劳动的聂绀弩,“忽然想起做旧诗来了,第一次正式写旧诗,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以为旧诗适宜于表达某种情绪,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绪,故发而为诗”。1981年8月,公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胡乔木在序中说:“作者所写的大都是七言律诗,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此后,聂绀弩的旧体诗广受赞誉:“新奇而不失落韵味,诙谐而满含酸楚”。那么,他从前的新诗,已乏人问津。他唯一的新诗集《元旦》,在作者人生和创作上,都留下了极难堪得而宝贵的印痕。 (本文原题《聂绀弩的新诗》,作者韦泱,学者、书评人,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