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铄铄,硝烟弥漫,屠刀在那兵燹中架起一座残酷的红色长城。岁月如梭,历史总会在某个时空节点上凝固成永恒的痕迹。而在这些濒临死活的关键时候,有多少人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墨,拾起锈迹斑斑的刀枪,踏上荆棘遍布的征程?年轻气盛时,他们也曾抱有诗书梦想,渴望以温润典雅的笔墨播种和平的种子。然而,现实总是捉弄人生存划的把戏,时期的召唤让他们不得不暂时搁置空想,投身到烽火连天的硝烟里。
墨客杨炯临危不乱,奋勇杀敌。他以"从军行"一作彰显了无畏文人的勇武气概。文词中充满了悲壮、豪迈之情,令人为之动容。历代抗争中,时常呈现出诸如杨炯这样的文人骑士。他们虽习气了温室中清雅闲适的生活,却也能临危不惧、奋勇杀敌,用生命守卫了家国肃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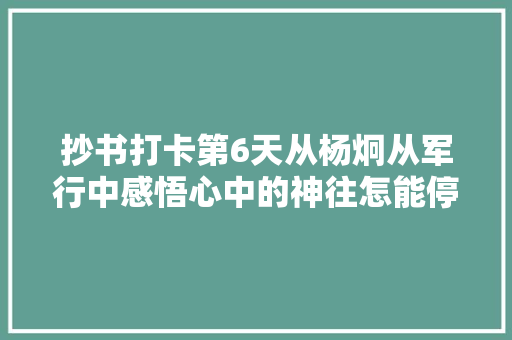
试问何人不爱太平?谁人不羡鸟兽之无忧?可古往今来,和平岂能不是从硝烟战火中夺来?文人虽无甲胄勇武,却也要在狼烟四起时豁出身命。公卿将相中,不乏文人出身者。魏晋南北朝时,竟连袁枚、谢灵运这般名垂青史的文豪佳作,也多出自金戈铁马间隙。历朝历代,无数人抛家舍业、离亲别友、含泪赴沙场,难道也不正是由于他们太神往"重朝迈凤阙,三际绕龙盘"的太平景象?
正所谓"戎马万里凭谁力,诗人自护在经编"。王维、李白等大墨客,也曾随军征伐,以诗词驰骋疆场。所谓"妻子亲家远,锥䆆不相亲",正是因不得不从军从军。一旦战火蜂起,便是青年才俊,也难免逃其"白发三千丈,缙绅一万余"的毒手。无数文士为之力竭而亡,曾作"立时曾相呼,黄尘人已去"的凄凉诗句。即便不去世于非命,也要 "刘镕辞朝贵,沈休下伍贱",阔别家乡亲友多年,蹉跎岁月。这统统,何尝不是为了来日换来一方太平?因而,多少儒雅文士,也要在关键时节强做雄壮,履尽困难险阻,"直入尘凡,历览风雨"。
杨炯师长西席本是诩馆之士,本当以旁观山林之美景为事。然而,他也亲历亦臻亦陷的战火,更曾在从缧城的赤壁一战中,亲眼目睹残阳如血、白骨累云。于是,他写下了那首永垂青史、气韵非凡的"从军行"。个中丰裕着对和平悲切的神往、对残酷战役的不平之鸿气,和面对死活绝境仍旧坦然从容的勇武豪情。实在,这正是古今中外无数文人学士在面对战乱时,内心激越澎湃的真实写照。
谁能否认,一位温润如玉的诗人,心中也会时时时升起被硝烟蒙蔽的烽火情怀?多少才华出众之士,也曾在戎马旗影下历尽坎坷,终极造诣了不朽的劳苦功高。由此可见,文人终极也要为和平而战,不得不在某些关键时候背井离乡、临阵杀敌,以守卫民族大义。所谓"持戈使门前"常不得不兼济天下。
以是,我们本日能享受太平盛世,不也正由于古人在动荡年代曾一雕琢前赴后继、奋勇杀敌吗?以是请同学们评论:在你们看来,文人理应全心向学还是要体恤世情、合时而变?文人笔耕究竟与征战互为表里,是否也该把军旅生涯视为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