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李白的这篇《登金陵凤凰台》,我不禁深深的感慨。这个时候的李白,已经不再是盛唐时期那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李白,也不是那个“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李白,他已经是一个多舛多难,流放遇赦归来的老者。
李白的诗作充满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色彩,是天才的无穷的想象力。
他的诗多用古风,乐府、歌行和绝句造诣最高,这些古风诗每每不拘一格,英气干云。李白作律诗较少,由于律诗对诗的格律哀求苛刻,不太适宜他旷达洒脱的风格。
但是,即便如此,他的一首七律却冠绝古今,与杜甫的《登高》、崔颢的《黄鹤楼》并驾齐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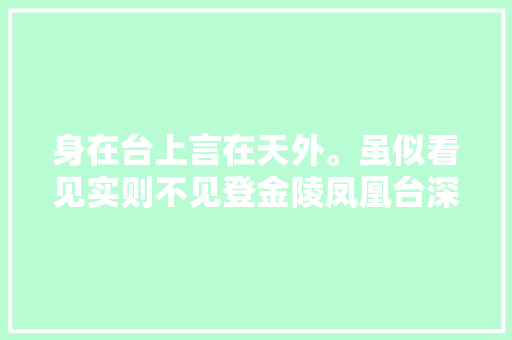
这便是没有崔颢,黄鹤楼依旧是黄鹤楼,但是没有李白,金陵凤凰台就不是今日凤凰台的《登金陵凤凰台》。
一、创作背景:飘泊的逐客,人生老矣关于李白创作《登金陵凤凰台》的背景,目前紧张有两种学说。
第一种说法是,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后,离开长安,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漫游所作。
第二种说法是,公元761年(上元二年),李白流放夜郎,中途赦还后,又回到金陵所作。
笔者更方向第二种学说。
情由如下:
其一,从诗中表述,已经险些没有了李白特有的自傲(后文详细剖析),只有历经磨难和垂老之际无尽的感慨和落寞;
其二,李白该当去过三次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多次金陵。
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第一次去江夏登黄鹤楼的时候,李白看到了崔颢的《黄鹤楼》。
公元759年(乾元二年),发配夜郎遇赦后,又到江夏。
公元760年(上元元年),从洞庭湖返回江夏。
李白确实深受崔颢《黄鹤楼》的影响,平生模拟崔颢作过两首诗,一首是《鹦鹉洲》,一首便是本诗《登金陵凤凰台》。
据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考证,《鹦鹉洲》作于公元760年(上元元年)。
而在写出《鹦鹉洲》之后,潦倒穷困的李白又辗转到了金陵,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六十一岁高龄,基本靠接济为生。
同为模拟崔颢,《鹦鹉洲》痕迹太重,不像《登金陵凤凰台》有时得之,以是相信《登金陵凤凰台》在后。
以是,便是在六十一岁高龄,多舛多难、病患缠身的李白又回到自己最喜好的金陵,登上了城郊的凤凰台,写下这首千古名篇《登金陵凤凰台》。
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上苍外,二程度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图1 金陵凤凰台
二、身在台上,言在天外自古登高临远的诗词从来不乏佳作。
远眺江山、家园,感怀世事沧桑,感怀自己出生,险些是每一个都不由自主发出的声音,而千载之下,真正震耳欲聋者却寥寥无几。
一开篇,墨客登上凤凰台,遥想当年,南朝刘宋永嘉年间,在凤凰山筑此凤凰台,筑台之时,有凤来仪,一时繁盛。 而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台下长江水仍旧东流,仿佛还在诉说着这段沧桑。
紧接着,墨客从面前景象转向更远的时空。不只是凤凰台“凤去台空”,金陵曾经是吴(三国期间)和东晋的首都,曾经显赫一时,而现在,吴宫的野草已经比人还高,东晋那些显赫的王族早已变成一座座荒丘。
墨客没有完备沉浸在历史的感慨中,接下来他又回到面前的景致中。
面前的景致仍旧让他沉醉。
“三山半落上苍外,二程度分白鹭洲。”根据陆游的《入蜀记》记载:“三山自石头及凤凰台望之,杳杳有无中耳,及过其下,则距金陵才五十余里。”陆游所说的“杳杳有无中”恰好注释“半落上苍外”。
李白把三山半隐半现、若隐若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白鹭洲”在金陵西长江中,把长江分割成两道,以是说“二程度分白鹭洲”。这两句诗气候壮丽,对仗工致,是难得的佳句。
末了,墨客把对历史的追溯和面前景致的陶醉,变成了对自己命运的感慨和对时期王朝的愤怒。
“总为浮云能蔽日”语出《新语·慎微篇》,“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这里,李白和陆贾的语义同等,都是在痛斥朝廷中奸臣当道的阴郁环境。
“长安不见使人愁”中,“长安”语带双关。
“长安”指都城“长安”,墨客在金陵遥望都城长安,千山万水,云遮雾罩,看不到自己昼夜思念的长安。
“长安”指皇上,由于奸臣当道,“浮云蔽日”,以是,皇上当然看不到自己,而自己也当然报国无门。
整首诗看似写的都是墨客登凤凰台所见所感,但是,细细读来,实在都是写的看不见。
已经六十一岁的墨客历经劫难,已经看不见自己的未来;
“浮云蔽日”,皇上看不见天下有空想有才德的人;
奔波生平,多舛多难,墨客看不见自己一贯怀揣的伟大梦想。
方回在《瀛奎律髓》评价道:“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此诗以凤凰台为名,而咏凤凰台不过起二语已尽之矣。下六句乃登台而不雅观望之景也。三、四怀古人之不见也。五、六、七、八咏今日之景,而慨帝都之不可见也。登台而望,所感深矣。金陵建都自吴始,三山、二水,白鹭洲,皆金陵山水名。金陵巧以北望中原唐都长安,故太白以浮云遮蔽,不见长安为愁焉。”
图2 六朝金陵
三、自比凤凰,来不逢时李白生平桀骜不驯,曾经自比麒麟,乃至自比孔丘,而他自比最多的是大鹏。
这首诗里,李白则因此凤凰自比。
第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实在也是一语双关。
既写出了怀念当年凤凰台繁盛,感慨世事沧桑之情。更因此凤凰自比,写出了自己来不逢时的悲哀。
当年孔丘闻麒麟降世而落泪,《春秋公羊传》:“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者。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孔子曰:‘孰为来哉!
孰为来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
孔丘为什么落泪,便是由于麒麟生不逢时,“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而李白在凤凰台已经没落的时候,登上凤凰台,显然也是来不逢时。正如那头生不逢时的麒麟一样,只能是怀才不遇,没落生平。
四、李白的谢安和金陵情节东晋谢安一贯是李白的偶像,希望自己也能像谢安那样,为王朝履立大功,因此,李白一贯也有“金陵情节”。
而今日,已经六十一岁高龄的李白,再次来到谢安曾经建功立业的金陵,回顾自己,只是一个参加了永王叛军而被流放遇赦的“逐客”。
胸中虽然梦想不灭,怎奈天不遂人愿。正如杜甫所说“出师未捷身先去世,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时此景,怎么能不深深的嗟叹堕泪。
五、与崔颢的《黄鹤楼》北宋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二十一》在《黄鹤楼》诗下注曰:“世传太白云:‘面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作《凤凰台》诗以较胜负。”
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记载:“《该闻录》云: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尚曰‘面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
以是,李白的《鹦鹉洲》和《登金陵凤凰台》与崔颢的《黄鹤楼》一决牝牡,就成了后世津津乐道之事。
而《登金陵凤凰台》确实有《黄鹤楼》的痕迹。
两首诗都是登高远眺,吊古怀今的绝唱。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
都是从当地的传说开始,追溯前年繁盛,抒发自己情绪。
王夫之在《唐诗评比》评价道:“‘浮云蔽日’、‘长安不见’,借晋明帝语影出。‘浮云‘以悲江左无人,中原沦陷;‘使人愁’三字总结‘幽径’、‘古丘’之感,与崔颢《黄鹤楼》落句语赞许别。宋人不解此,乃以疵其不及颢作,觌面不识,而强加是非,何有哉!
太白诗是通首混收,颢诗是扣尾掉收;太白诗自《十九首》来,颢诗则纯为唐音矣。”
《登金陵凤凰台》不及《黄鹤楼》的意境缥缈。
但《登金陵凤凰台》意境更为弘大,不仅写出了墨客对自己的感怀,更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情绪,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更见肚量胸襟。
总之,这首诗是一个垂老之人,历经死活后的感言,是一个生平流落的逐客,寻觅到了他生平眷恋的深情表露。如果这个人是杜甫,我们还尚可,但是这个人是那个狂妄自傲,伟大的浪漫的从不言败的李白,怎么能不让人深深动容!
末了,笔者只想说,如果没有崔颢的《黄鹤楼》,黄鹤楼依然是黄鹤楼。
但是,如果没有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就不是今日的凤凰台。
图3 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