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代表浮世绘
比如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日本战国枭雄织田信长在本能寺自焚前吟诵的辞世诗:
人生五十年,与天地长久相较,如梦又似幻,一度得生者,岂有不灭者乎?
本能寺,据传织田信长在此自焚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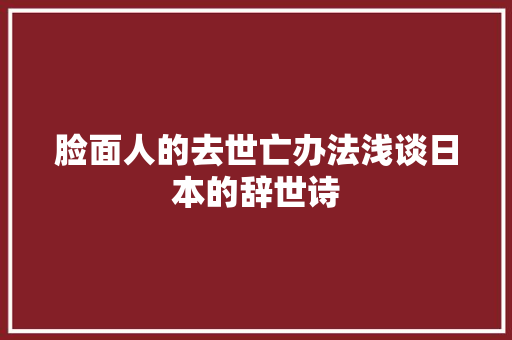
还有“下克上”,背叛了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也留下了一首汉诗作为辞世诗,用以总结自己的生平,并为自己的叛逆辩白:
逆顺无二门,大道彻心源。
五十五年梦,觉来归一元。
乃至就连战犯东条英机在实行绞刑之前都非要留一首辞世诗:
再见,我在青苔之下,静候大和岛的花开。
战犯东条英机
由此可见,辞世诗对付日本人的主要性。
辞世诗的起源日本的辞世诗实在是宫斗的副产品。
与中国一样,日本的皇位更迭同样伴随着血雨腥风,宫斗失落败的皇子每每不愿寂寂无名的去世去,同时也为了表达对人生境遇的慨叹,因此这些饱读诗书、深受汉学影响的天潢贵胄们就喜好在去世前作下一首诗词来玉成自己的体面。
比如公元658年,年仅18岁的有间皇子卷入了太子之争中,失落败即将被杀,在被逮捕的途中他将两根松枝绑到一起,作下悲歌:
如果命运眷顾,我愿回到岩代之滨,重见我所结的松枝。
日本皇室“万世一系”,宫斗比起中国也不遑多让
而在这位文艺皇子被处去世的20年后,同样的命运又降临到了大津皇子身上,他也学着有间皇子作下了一首辞世诗作为遗言:
这是末了一次,我见到水鸭在湖上鸣叫,而我将消散在云中。
而在这两位皇子之后,日本的贵族们逐渐喜好上了这么一个体面的去世亡办法。
佛学对辞世诗的补充日本人能够坦然的面对去世亡,并且发展出一种病态跟畸形的自尽文化,这与佛学的传入是分不开的。
就在遣唐使将天朝的景致带回日本时,佛教也随之传入日本。最为著名的便是鉴真东渡的故事。大批的僧人东渡日本进行传教,建造禅寺。
日本禅寺
而当时的传教僧人在日本每每还兼职着文学老师和技能顾问的身份,他们极大的推动了日本科技与文化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佛学思想也被好学的日本人通盘吸收,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中就包括对死活的态度上。
在日本佛教的宗教不雅观念里,有贤德的人是可以预知自己的去世亡的,而如果能在去世亡之前保持沉着,进入寂灭的状态,就能使人在去世后不必受六道循环之苦,这也是我们看历史上许多日本人都热衷于自尽的缘故原由了,由于在他们的思想不雅观念里,体面的自尽非但不是一种苦楚,反而是得到救赎的一种路子。
可以说,佛教思想便是日本自尽文化的根本。
日本属于一个佛教国家
我们看日本《太平记》中记载的日本人认为的最为体面的去世亡办法:
日野俊基从他的长袍中拿出一轴白纸,用纸角擦了擦脖子,然后把白纸展开,写下了他的辞世诗:古来一句,无去世无生,万里云尽,长江水清。写完之后,俊基把羊毫平放,用手理了理头发。就在这一瞬间,行刑者的长剑从后方一闪。俊基的头颅向前倒下,身躯也随之倒下。
并且不仅仅是如此,佛教思想也使得日本人的辞世诗多以风、花、雪、月等须臾即逝的四季景物作为紧张诗歌的紧张内容,用以表达人生的无常、无我思想。
辞世诗的发展在很长的一段韶光内,辞世诗都这天本上层贵族用来装逼的利器。早期的日本辞世诗多以汉诗或者是和歌的形式写就,而在日本能够接管汉学教诲的每每都是上层贵族,底层武士乃至没有体面自尽的权力,直到俳句的涌现才改变了这一现状。
日本贵族
由于措辞差异的缘故原由,虽然汉诗被日本的上层贵族中十分盛行,但是它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格律跟平仄与日语相差甚远,普通人听都听不懂,更何论产生共鸣乃至是自己创作呢?因此俳句作为汉诗跟和歌的本土化产物就应运而生了。
俳句一样平常以“五七五”十七个日本字音组成,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三句统共十七个音组成一首短诗。
而在俳句本土化中,影响最为巨大的该当这天本俳圣松尾芭蕉了,他曾为他早夭的孩子作了一首俳句:
我知这天下,本如露水般短暂
然而
然而
松尾芭蕉被誉为日本俳圣
其余号称日本美女的冲田桑也在将去世之时留下了一首不俗的俳句,翻译过来大意是:
水若不流花不落,两心永隔暗冥中
当然,也有一些放飞自我的辞世诗,例如日本武士竹田留下的辞世诗:
阿修罗岂能将我制服?
来世我要重生,
砍掉胜家的头!
日本武士
虽然全无辞世诗以往的坦然寂灭之感,却有着一股武士的决然跟狠厉在里面,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辞世诗的多样化发展。
辞世诗的虚伪辞世诗中的哲理与作者在面对去世亡时的坦然心境不免让阅读者感到由衷的敬佩,但是其本身是含有着极大的虚伪身分的。
流传下来的辞世诗,有很大一部分并不这天本人去世前开悟所做。当辞世诗形成潮流时,许多人都喜好早早的就把辞世诗写好,乃至是请人代笔,而等到临终之际再假装是自己的开悟所得吟诵出来,颇多造作之感,全无辞世诗的坦然安寂。
日本文化追求闲寂
例如曾有一位叫做鸣岛的日本人,在自己五十岁时就写好了自己的辞世诗,并要求冷泉帮他修正:
年已五十多,
感谢父亲与母亲。
我的内心宁静,
徜徉在花海之中。
而早早就准备好辞世诗的鸣岛却活了良久,一贯到他八十多岁时他又去找冷泉为他改诗,冷泉见告他你自己哪天去世,就把第一句的数字改掉就好。
而除了预先写好之外,也有很大一批的辞世诗并不是其本人所做。有些人去世于战乱或是突发疾病,来不及留下遗言,他们的属下或者后人就从他们在世时喜好的书本或者诗歌当中找到一句,用以作为他的辞世诗。
例如最为著名的织田信长所吟唱的那句人生五十载实在并不是他本人所做,而这天本传统戏剧《敦盛》中的一句戏文,只不过后人默认是他的辞世诗而已。
织田信长墓所
末了总结,辞世诗作为日本人自尽仪式的一部分,其有没有、好不好,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这个人去世的是否体面,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梳理出日本的历史与文化脉络,是研究日本文化不可忽略的一个点。
参考文献:
《日本古典俳句中的美学意蕴研究》
《日本人自尽行为背后的文化成分探析》
《论日本武士道自尽文化生理》
《从俳句「ひごろ憎き」看芭蕉俳句中雪的“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