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教《诸子百家精选课》里的《韩非子•十过》一文,个中的缺点实在是有点“不忍卒读”,有一个章节的缺点更可谓是“触目惊心”。现在我就把个中的笔墨和标点缺点梳理和更正一下,以便其他同行在教授此篇时做个参考:
奚谓顾小利?昔者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马也。若受吾币不假之道,将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若受我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君勿尤(忧)。”
这一段中“君勿尤”应为“君勿忧”,什么道理呢?由于在荀息建议晋献公用祖传的玉璧和自己的宝马去贿赂虞公时,晋献公担心他受了贿赂后不肯借道,荀息在说了一番道理后劝“君勿尤”,而“尤”是“责怪”的意思,此处明显用“忧”更合理,是“担忧”之意。
君曰:“诺。”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贪利其璧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夫虞之有虢也,如车之有辅。辅依车,车亦依辅,虞、虢之势正是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不可,愿勿许。”虞公弗听,逐(遂)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处三年,与兵伐虞,又克之。荀息牵马操璧而报献公,献公说曰:“璧则犹是也。虽然,马齿亦益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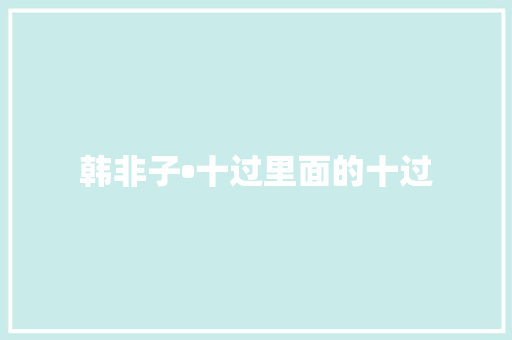
上述这段便是紧接着前面那段的内容,此处的“逐”为“遂”之误,我就不多阐明了。
奚谓贪愎?昔者智伯瑶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灭之。反归,休兵数年。因令人请地于韩。韩康子欲勿与,段规谏曰:“不可不与也。夫知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骜愎。彼来请地而弗与,则移兵于韩必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他国。他国且有不听,不听,则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韩可以免于患而待其事之变。”康子曰:“诺。”因令青鸟使致万家之县一于知铁(伯)。
这段末了的“知铁”毫无疑问是“知伯”之误。
襄子惧,乃召张孟谈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备具,吾将何以应敌。”张孟谈曰:“臣闻贤人之治,藏于民,不藏于府库,务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遗三年之食,有馀粟者入之仓;遗三年之用,有馀钱者入之府;遗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缮。”君夕出令,嫡,仓不容粟,府无积钱。库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备(具)已具(备)。君召张孟谈而问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备(具)已具(备)。钱粟已足,甲兵有馀。吾奈无箭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墙之,其楛高至于丈,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虽簵之劲弗能过也。君曰:“箭已足矣,奈无金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用之,有余金矣。号令已定,守备(具)已具(备)。
上面这段,“守备已具”和“守具已备”看似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还执意要“改动”呢?你看之前章节中的一段就明白了:
知伯因阴约韩、魏将以伐赵。襄子召张孟谈而告之曰:“夫知伯之为人也,阳亲而阴疏。三使韩、魏而寡人不与焉,其措兵于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张孟谈曰:“夫董阏于,简主之才臣也,其治晋阳,而尹铎循之,别的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而已矣。”君是曰:“诺。”乃召延陵生,令将车骑先至晋阳,君因从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邑无守具。
韩非子在“贪愎”这一过里详细写了晋海内争之后,四大家族之首的智伯被韩、魏、赵三家“反攻倒算”的历史故事,后来智伯门下的刺客豫让为主人报仇,也出身了“士为心腹者去世”这种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这两段里,赵襄子是唯一一个对智伯说“不”的人,他的智囊张孟谈就建议赵襄子去晋阳坚守,结果赵襄子去了那里创造支撑防御的粮食、钱财、兵器,什么都没有。整座城市(邑)没有“守具”,而“守具”的意思便是“守卫用的战具”。
赵襄子当即就慌了,张孟谈让他下了几道命令,到了第五天竟然统统准备就绪。前面的“仓不容粟”对应“仓无积粟”,“府无积钱(无法再堆积钱财)”对应“府无储钱”。“库不受甲兵(无法再接管甲兵)”对应“库无甲兵”。以是对应“邑无守具”确当然就该当是“守具已备”。
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实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裁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奢)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硃画书其内,缦帛为茵,将(蒋)席颇缘,触(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辂)而建旒九,食器雕琢,觞酌刻镂,白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
这一段的缺点可就多了,最离谱的便是“财子”一词了。这是韩非子在论述“耽于女乐”这一“过”时讲述的故事:秦穆公讯问戎国的青鸟使由余古代君王攫取江山和失落去江山的根本缘故原由,由余回答说是“奢俭”,然后开始举例证明,就有了上面这段论述。
本来“尧”的期间,餐具用的是陶土制品,到了“舜”的期间就用木制品,那么砍伐山林中的树木(斩山木),当然先要砍去枝叶,以是“裁之”才是原文该有的笔墨,结合后面的“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从“裁之”到“输之”,不便是从树木到餐具的一套流水线制作过程吗?“财子”是什么玩意儿?
“诸侯以为益侈”中的“益”应为“奢”之误,不仅是由于前文已经有“奢”字,若把“益”当作“增益”或“更加”来解读,则前面的“尧”的土质餐具并没有“奢侈”之意,是与“舜”做比拟的。这在文理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更何况后面是用“弥侈”的“弥”来表示“更加”的意思。
“将(蒋)席颇缘,触(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和“作为大路(辂)而建旒九”中的“蒋席”(茭白席)、“觞酌”(盛酒的礼器)、“大辂”(古代的一种大车)都是当时的物品名称。
君曰:“诺。”乃使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遣戎王,由于由余请期。戎王许诺,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几不迁,牛马半去世。由余归,因谏戎王,戎王弗听,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故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
上面这段没有缺点,我为什么还列举出来呢?由于唐代学者颜师古居然把“设酒张饮”中的“张”解读为通假“帐”,看来水平也不过尔尔。“设酒张饮”实在是个联合词组,即“设张酒饮”。“张”和“设”基本同义,便是张罗、支配的意思。
“张饮”一词在古文里都能用“开饮”来阐明,根本无需“帐篷”。由于“帐饮”一词才是在“帐中饮酒”的意思,没必要通假。南北朝的江淹在《别赋》中就有“帐饮东都,送客金谷”,唐朝墨客王维的《不雅观别者》一诗中有“都门帐饮毕,从此谢亲宾”的句子。《史记·十二本纪·项羽本纪》中有“项羽晨朝年夜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的记叙,充分解释“张饮”通“帐饮”理据不敷,用《史记·十二本纪·高祖本纪》的“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作为“张”通“帐”的依据,逻辑何在?
奚谓离内远游?昔者齐景公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去世。”颜涿聚曰:“君游海而乐之,奈臣有图国者何?君虽乐之,将安得。”齐景公曰:“寡人布令曰‘言归者去世’,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将击之。颜涿聚曰:“昔桀杀关龙逄而纣杀王子比干,今君虽杀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为国,非为身也。”延颈而前曰:“君击之矣!
“君乃释戈趣驾而归。至三日,而闻国人有谋不内齐景公者矣。齐景公以是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地(也)。故曰:离内远游,则危身之道也。
这段末了的“地”毫无疑问是“也”之误。
公曰:“但是竖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竖刁自獖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公曰:“但是术(卫)公子开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齐、卫之间不过旬日之行,开方为事君,欲适君之故,十五年不归见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亲也,又能亲君乎?”公曰:“但是易牙何?”管仲曰:“不可。夫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爱其子,今蒸其子以为膳于君,其子弗爱又安能爱君乎?”公曰:“但是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为人也,坚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坚中则足以为表;廉外则可以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多信则能亲邻国。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
“术公子开方”应为“卫公子开方”,缺点的缘故原由估计是“术”的繁写体是“術”,“卫”的繁写体是“衛”,除了中间部分不同,两边相同。
君曰:“诺。”居一年馀,管钟(仲)去世,君遂不用隰朋而与竖刁。刁莅事三年,桓公南游堂阜,竖刁率易牙、卫公子开方及大臣为乱。桓公渴馁而去世南门之寝、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虫出于户。
韩使人之楚,楚王因发车骑陈之下路,谓韩青鸟使曰:“报韩君,言弊(敝)邑之兵今将入境矣。”青鸟使还报韩君,韩君大大悦,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实害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听楚之虚言而轻强秦之实祸,则危国之本也。”韩君弗听。公仲怒而归,旬日不朝。宜阳益急,韩君令青鸟使趣卒于楚,冠盖相望而卒无至者。宜阳果拔,为诸侯笑。故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者,则国削之患也。
管钟之误无需多言,“敝”是对自己的谦称,“敝邑”便是“我们的城”,而“弊”最多是通假“蔽”。
综上是《韩非子•十过》中一些没有改动之处,总结一下古文里面造成这些缺点的缘故原由:一部分是字形附近造成的,属于缮写缺点;一部分是发音附近,属于听写缺点;一部分便是理解缺点,造成在传抄的过程中被故意修正。
以是,我对古诗词和经典国学著作的传授教化和改动,是建立在笔墨学,文理逻辑的根本上,力求严谨通达,符合当时文言文的普遍运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