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柳、春雨、黄莺、东风,道不尽万物勃发的春天,墨客尤爱春天,或如贺知章立于春柳下发出“不知细叶谁裁出,仲春东风似剪刀”的咏叹,或像杜甫在《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感触春雨,又如王维身处《鸟鸣涧》看“月出惊山鸟”,听“时鸣春涧中”,亦像朱熹体会《春日》中“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美,墨客们踏春、赏春、探春、咏春,诗酒颂春天。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不祁寒,夏不剧暑”,山川环抱,川泽渟泓,“风虽高而不烈,节虽变而长温”,四季如春的自然环境引发了文人墨客对云南春天的创作灵感和激情。明代文学家杨慎在《滇春好》小令中写道,“滇春好,韶景媚游人。拾翠东郊风袅袅,采芳南浦水鳞鳞,能不忆滇春?滇春好,百卉让山茶。海上千株光照水,城西十里暖烘霞,能不忆滇花?滇春好,翠袖拂云和。雅淡装扮堪入画,等闲言语胜听歌,能不忆滇娥?滇春好,最忆海边楼。渔火夜星明北渚,酒旗飘影荡东流,早晚复同游。”正因滇春如此好,清云贵总督阮元在《游黑龙潭看唐梅》中感叹“千岁梅花千尺潭,东风先到彩云南。”晚年的楚图南在《乡心》中回顾道:“遥忆南天春不老,繁花满野四季喷鼻香。”四季旖旎的春景助就了诗词中云南的炫彩书写。
绘春景,赞繁花层出美妙
“天开胜景彩云生,四季花柳无寒燠”“奇花异卉,四时不歇,风景熙熙,实坤维(南方)之胜区也。”云南春连四季、繁花不断的景象成为文人笔下云南之春的独特素材。元代大理文人羌奴作“云旧山高连水远,月新春叠与秋重”,另一位元代文人高雅昌《题大理点苍山》道“水光万顷天开镜,山色四季环翠屏”,都写出了云南四季环翠的独特景象。明初云南学者兰茂作《行喷鼻香子(四季词)》描写春景“红杏芳菲,庭草葳蕤。满乾坤、买卖熙熙。山明水秀,鱼跃鸢飞。更雨轻轻,风淡淡,日迟迟。”绘出了云南春景中万物生发,和风暖日的景象。明代墨客贾惟孝在病中写《新春》亦感叹道“自从长至过元宵,绿到河湾第几桥。”长至是夏至的别称,墨客推测从夏日到元宵,春色不断,春绿不知染了河湾的几座桥。明正德举人张含在《兰津桥南新开仄路险山》中描述“钩藤野葛四季茂,鹦哥杜鹃千数开。”描述了藤蔓野葛四季都茂盛,春末夏初开的杜鹃花状似鹦鹉开满枝头,争奇斗艳的景象。明代文人杨士云在《红圭寺见山茶》中描写“繁霜十月见花开,山北山南未放梅。”写出了在北方隆冬,万木凋零的时候,云南则是艳阳和煦,山茶争艳。明吴懋登楼远眺“入窗随意看春山”,于是由衷感叹“只恐五湖无此景,便应长住不须还。”清乾隆举人罗元琦为官陇西,回籍入滇时,看到“茶花似火梅如雪,好是红儿对雪儿。”滇中残酷春景大异北方冰封雪飘,感叹不已,写下《入滇沿路梅开似雪,茶花斗艳期间,非复朔方景象矣》一诗,诗中洋溢着对云南春景的热爱。近代墨客李坤在偶遇早春昆明下雪后,觉得弥足宝贵,于是赋诗《雪后登五华望昆明湖上诸峰》“滇山冬不枯,草木蔚深绿,昆湖浸芙蓉,倒影浣城角。物罕自见奇,境妙故无复。”从侧面道出了云南冬无寒冷,草木常绿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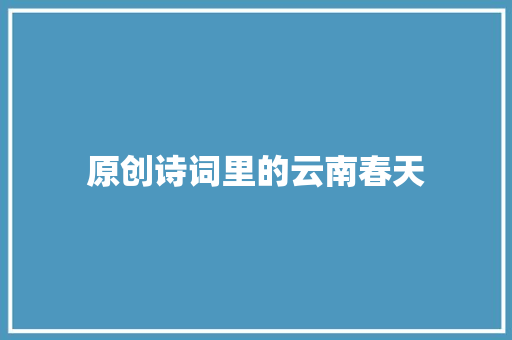
借鸟啼,描山色绮丽图景
温暖的景象,让云南成为莺燕、鸥鹭等春日物候的流连之地,也成为春日云南诗文中主要的素材。兰茂在《新春》中写道“新莺初出谷,旧燕复家来,东风莫辜负,诗酒作生涯。”以莺燕写出新东风景,道出春日热闹的景象。明正统年间云南巡抚侯琎写《高黎贡山》“高黎贡山花正红,千岫万岫烟云中,莺声鹊声满丹峤,远色近色皆苍松,记取此景付彤管,豪吟野眺生东风。”描述出高黎贡山春日莺歌环抱,山色绮丽的景致。明景泰举人朱克瀛在《早春登金沙望海》中吟道“金山春早独登台,万里昆明气候开,鹭沙鸥渚轻寒在,鹾估渔舟返照回。”颂出了早春昆明气候万千,鸥鹭水鸟在早春微寒的沙渚上嬉戏,盐商渔船也趁着春色归来的景象。明孟富站在水边高地吟诵《暮春东皋晚眺》“连朝来好雨,新水涨平溪。春残鹃叫切,风软燕飞低。”杜鹃飞燕一派雨后晚春田园景致。清代名宦赵士麟在《界亭》中写春景“四十八盘青未了,春山一片画眉声”,借鸟啼描述春山清丽图。清代墨客郭复虢《春日远足》时看到“水浅鸥争浴,风轻柳自斜”的春日美好。元代墨客马臻的《春日幽居》“杏花一树开如锦,怕触啼莺不倚阑”春日情致跃然纸上。康熙举人窦琏《柳堤春雨》道“槛外春光接五华,半堤新柳绿荫遮。好从小雨轻寒后,坐听流莺数落花。”春雨流莺,清新闲适。同是康熙举人的许湜在《春兴》中表达了残酷春光使人愉悦的情绪,诗末再次寓情于黄鹂啼鸣“尚有东山丝竹兴,听鹂多向绿杨村落。”
写湖泊,颂春日烂漫风光
云南这般春日花开不断、莺歌燕舞的景象,除了归功于分外的地理条件,青山环抱,阻隔寒潮之外,也归因于滇池、洱海等高原湖泊对气温的调节浸染。历代文人在写春的同时,也把这些高原湖泊作为咏颂素材,写入诗歌,代代外扬。杨慎在春月泛舟滇池时描写“汀蘋袅袅风色起,崖草凄凄春兴连”,写出了春夜滇池蘋浮摇荡、水草茂盛的样子。明嘉靖进士李元阳在《泛洱水》中写道:“柳青春已半,晓日初曈昽。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诗中将浩瀚明静的洱海与春日领悟,道出了春日泛舟洱海的所乐所感。李中溪自鸡足山归来泛舟洱海再次写到“天镜阁前春可怜,波光淡淡生绿烟,岛屿萦回春浩荡,桃花仲春下江船”烟波浩渺的洱海一番春意盎然的景象。清乾隆进士熊郢宣写《官渡》,把笔触放在描述滇池畔春景田舍生活“昆池近锁河流碧,太华平临野气青。”清末墨客戴絅孙在《春晓望太西岳》中极富浪漫色彩地描述春日滇池西山的美景“波涛下搏鲛宫紫,楼阁凌虚绛霄起。万里空青开断烟,百丈峭壁照春水。绿萝何处梁王宫,沐浦桃花锦浪中。”滇池春日浩荡,墨客旷达肆逸的情怀激荡于字里行间。
抒胸臆,道百感丛生心境
诗歌不仅承载美景,更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诗词里不但有云南的春景,更记录着文人们伤春、思春、怨春、叹春、惜春的情绪,正所谓“风景不转心境转”。元代墨客张翥在《踏莎行》一词中,写暮春江上送客的愁绪“碧云红雨小楼空,春光已到销魂处。”明正统贡生金齿人(今云南保山)陶宁抒发“桃花红雨梨花雪,铺得春愁一寸深。”明代墨客贾惟孝《登螺峰四顾亭》描写滑腻调皮山雨过青树、鸟语花香的春日好景后,便抒发了人生奔波的感怀,“雨过树头云气湿,风来花底鸟声喷鼻香,人生能得几时健,世事可怜终日忙,一春好景须寻乐,回顾南桥空夕阳。”明代名臣云南安宁人杨一清在刘禹锡“紫陌尘凡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的根本上,曾作《碧桃花》,“犹记看花紫陌回,一年一度向人开。东风本是无私物,何必玄都不雅观里栽。”讽刺了朝廷新贵,道出东风无私,各处都是桃花开放与民同乐的心境。清康熙举人钱熙贞在《春怨次京师才女》一诗中写道:“九十春深小院东,夜来月色满花丛,喷鼻香闺一样天涯恨,愁杀条条柳絮风。”将春怨表达得如此强烈,春景越美春怨越深。清道光进士何彤云在《春晓登五西岳》诗中,借“春声万户里,山色一城中”的春城秀色,表达“镇国天威重,兴文云瑞隆”文化发展,彩云南现的兴盛气候,昆明至今还有云瑞路的街道名。
说风尚,讲意趣盎然故事
少数民族文人眼中的春天也异彩纷呈。丽江世袭土知府木公,作咏怀诗《逐痴堂寄题愈光》“哀牢四月莺花尽,丽水经秋雁信稀”,写出了哀牢山、金沙江的春景秋色。他在《南湖晚眺》描写了湖畔渔村落“烟花三月暮,春水满渔家”的写意山水画。不仅写春景,木公更写少数民族的春会“官家春会与民同,土酿鹅竿节节通。一匝芦笙吹未断,踏歌起舞月明中。”诗歌描述了春会中少数民族群众打歌吹芦笙通宵欢庆的热闹场面,意趣盎然。纳西族墨客木曾继续家学,在《晚归白屋》写道“每沽前坞村落醪美,独钓长江春鳜肥。”诗中充满春野之气。白族墨客杨晖吉作《春兴二首》绝句:“林外寻诗去,江头得句来,含怀忘世虚,花谢与花开。”彝族墨客高奣映写七律《登浩然阁不雅观海有感限韵》,为读者编织一幅“碧波千顷落群溪,杰阁攒空洱水西。柳影游镳鸣系马,棕篱渔䱓立连鸡。东风自我招携得,秋月何人感慨齐”的春景惬意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诗词里的云南之春活气盎然、鸟啼花放,诗歌外的云南“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正是韶光妖冶时,怎能不展卷孜孜,莫辜负一番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