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玉龙/文
可哩麻嚓三锤两梆子;
把绳子糸(mi)起来;
你踩着我的脚巴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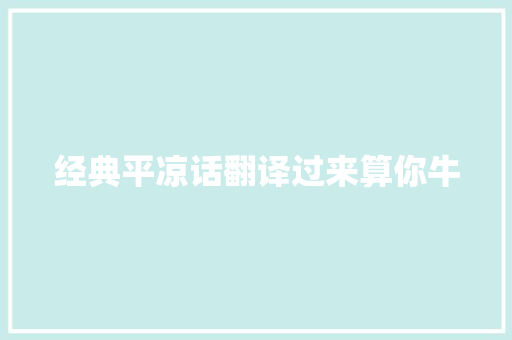
往前直飚奏到了;
你一下(ha)凛(lin)人的;
给我买二斤三月;
你的四我管不了;
咱们一块爬三去;
我腿猪娃子疼的;看
你一下把做的;
灵子里有巧巧……
上面这些隧道平凉话,大平凉人基本上都明白意思,但是让你用普通话正儿八经把它翻译过来,确实有不小的难度。
在曹臧恰我哩俺的大平凉,七县一区方言各有特色,韵味不同,如曹庄浪、臧静宁、恰灵台、我哩泾川、俺的崆峒等等,但大致上差别不大,统称平凉话。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方言也一样。一个县不同村落庄、族群,方言发音都有差别。许多崆峒华亭人,不一定能听明白庄浪静宁话,庄浪静宁人也不一定能听明白灵台泾川话。
如在崆峒区北部塬区的草峰、喷鼻香莲一带,鱼、驴不分,把女子称为咪子。特殊是鱼和驴,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干系的东西,硬让草峰原上人给扯到了一起,缠成了搅团,糜子麻子不分了。
比方说:我们去集市上卖驴,但草峰、喷鼻香莲人会说成:卖鱼。再比方说:我们要去市场买鱼,草峰、喷鼻香莲人会误以为我们去买驴。实在,这是比较范例的平凉方言的标志:声母错位。本来读作lü驴,却读成了yu鱼。而nü女子读作mi咪子,也是此类环境。
但凡平凉人,我们都知道,泾川人把猪不叫猪,叫zi彘。这让很多不熟习泾川话的人觉得很“雷”。弄不明白到底他们说的是鸡呢还是猪呢?当然,我们也曾经大言不惭地笑话人家泾川人不会说话,太土气。殊不知,把猪叫彘是泾川人从古汉语继续过来的雅言。《辞海》阐明为:彘,猪也,象形字。汉武帝原名刘彘。本义指大猪,后泛指一样平常的猪。只不过,泾川人把声母zh读成了z,也就把zhi彘读成了zi彘。
还有咱平凉人常说的“瓜子”,就让很多外地人误以为是说嗑瓜子。实在,平凉人说的瓜子、瓜娃、瓜怂都是一个意思:即傻子!
至于瓜子一词的出处和来历,半瓶子不是很明了,也就不敢胡卖派了。
如平凉话把“脚扭伤”叫“wo踒”了,把“冷”叫“sen瘆”的,把“斟酌、计算”叫“尺mao毣”,把“顺当、好”叫“wo倭也”等等,虽然听起来觉得很雷人,很费解,但它确实不是咱平凉人发明创造的土话,而是代代沿袭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词汇。
还有,我们平时口头语常说的:可利马嚓、日渎来亥、胡求马嚓、二不拉叽等等,是平凉方言接管了外来词蜕变形成的。如:褡裢来自蒙语。麻食来自波斯语“乌麻什”。麻达、颇烦来自维语等。而平凉话中常见的形容词“胡拉海”、“可利马嚓”、“胡求马嚓”、“扑稀来亥”等都是古匈奴语音译词。
可利马嚓,意思为:麻利、赶紧;日渎来亥,意思为:邋遢,不精神或不整洁;胡求马嚓,意思为:因陋就简,胡乱交差了事;二不拉叽,意思为:卤莽、蛮干,不讲策略;胡拉海,意思为:某人很大度,反面别人计较得失落;扑稀来亥,意思为:干事没有章法,不严谨,乱七八糟。
以上这些平凉话,我们平凉人代代口口相传,自然其意思了然于胸,不会觉得很难明得。但对外地人或90、00后一代习惯用普通话互换的平凉娃们来说,就像听“外语”一样难懂和晦涩。例如,你对一位初来平凉的外地朋友说:瓜娃,可利马嚓的,咱咥饭走!
不雷晕他才怪呢。
平凉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史上,这些不同民族来自不同地域,也保留了其不同地域的措辞特色。有些少数民族的方言,听起来也比较雷人:如崆峒区部分回族群众把你们叫“你哪”,把我们叫“俺哪”,把水叫“fei匪”,把跑叫“lou喽”,把拿叫“撼”,把哪儿叫“wan腕儿”,把喝水叫“huofei嚯匪”,把馍叫“mu牧“,把水开了叫“feijian匪尖”了等等。
当然,平凉话当中还有一些看似没啥意思的话,听起来也很雷人。如:你大个头。大,这里指父亲,翻译过来便是:你父亲的头。这句话原来是平凉人熟人之间相互调侃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但彷佛谁也没有仔细想过“你大个头”到底是啥意思。是说他父亲的头长得好看还是丢脸?是聪明还是蠢人?实在,你大头并非你大的头,而是另有所指,因少儿不宜,故不再详加阐明。
总归,平凉方言博大精湛,各地发音、吐字、表述不一,意思也就大相径庭。如果你以为自己家乡方言更故意思,请发到评论里与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