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最高形式
我大约是197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我一贯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期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有人认为至少在我们这里,诗的时期是过去了,大行其道的该当是小说。小说的边界一贯在扩大,但诗仍旧居于它的核心。出于这种认识,诗就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没有捉住诗之核心的文学,都不可能精彩,无论得到若何多的读者都无济于事。一样平常来说,阅读景况是一个陷阱,写作者摆脱它的影响是困难的。对付诗的写作来说就尤其如此。写作者的生命重心会放在诗中。有这样的认知,那么生命能量无论大小,都会集中在一个方向,这方向几十年乃至终生都不会改变。
我在青春在即乎猖獗地写,不知写了多少,但我知道并没有写出哪怕靠近一点的心中的好诗。青春期的冲决力是强大的,也更有纯度,以是诗神会眷顾。但诗还要依赖对生命的觉悟力、洞察力,特殊是仁慈。人上了年纪会更加不存抱负,更加仁慈。我这几十年来一贯朝着诗的方向走去,这种意境和激情亲切把我全部笼罩了。一个经历了漫长诗路的人,在其生平的劳动与判断中,必会有个人独到的眼力,这眼力不是他人能够取代的。
口语文运动与当代诗
中国自由诗显然须要与口语文运动联系起来稽核,就此看它有两个渊源:一是受到了西方当代诗的影响,二是脱胎于中国古诗。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自由诗紧张吸纳了西方诗,准确点说是译诗。这彷佛是一个不可更易的道路。但是想一想也会有问题,乃至有点后怕:割断了本土源流。这源流包括了形式和气韵。这个土壤的抽离让民气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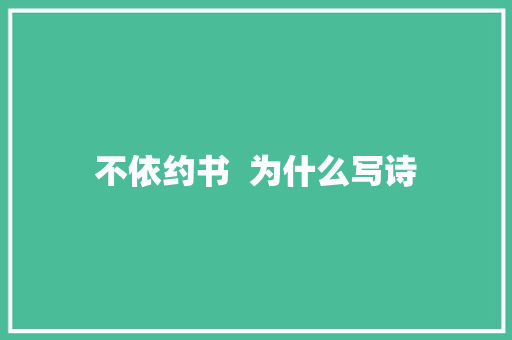
中国当代诗不会直接回到古风和律诗,也不会回到宋词。但前边讲的气韵境界之类是可以衔接的。若何交融和借鉴,这是最难的。弄不好会有一些反当代性的元素参与进来,弄得非驴非马。这是墨客极其苦恼的事情,却无法回避。我较少沉浸在西方译诗中央安理得,而是深深地疑惑和不安。
从补课的初衷出发,我这二十多年来将大量韶光用以研读中国诗学。对付中国文学的正源,从寻觅到谛听,透过当代主义的薄纱,有一种逐步清晰的迷离。当代主义和中国古典美学不是要大略地二者相加,不是镶嵌与组合,而是繁芜的血缘接续。
我只能说,至少在这二十几年的韶光里,我用全部努力改变了自己的诗行,走到了本日。我并不满意,但走进了个人的一个阶段。
诗歌与音乐的诠释空间一样大
这是无法言说的部分。能够言说的一定不会晦涩,真正的晦涩是另一种实在。这种环境哪怕稍稍当成一种策略去利用,落下的诗行也就变成了二流。墨客以一种极力清晰的、千方百计靠近真实的心情去表述,如此形成的晦涩才是自然的、好的。这实在是另一种朴素和直白。
当代墨客畏惧抒怀。虚假的滥情令人厌恶,轻浮的多情也足以反胃。但是诗一定是有深情在的,其情不抒,化为冷峻和麻木,化为其他,张力固在。无情之情也是情。真的无情,就会走入笔墨游戏。词语自身繁衍诗意的能力是极有限的。
有人认为当代诗的唯一特长,便是可以随意言说,可以纵情使性或天子新衣,可以唬人,那就犯了人生大错。当代诗必须朴素和诚笃,它的这个品质才是立身的根本。朴拙朴素的墨客走入了晦涩,这晦涩才故意义。
我对诗一贯有一种庄敬的心情,从少年时期便是这样。在所有的措辞艺术中,唯有诗,最靠近音乐了。一部纯音乐作品的诠释方法有多少,诗就有多少;前者的空间有多大,诗就有多大。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诠释是完备正常的。但大的审美方向与格调还是被一首诗或一部乐章给固定了的,这种固定的方法我称之为“诗螺丝”,拧在一个地方,使之不能移位,跑不走飞不掉,也便是成了。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平常不会被误读为一首小夜曲或圆舞曲。
长篇小说与诗
一部千余行以上的长诗,其体量的蕴含不会少于一部长篇小说,就体力和智力的耗费而言可能更多,这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一个构思在心里装了良久,但不一定成熟。很难下手,由于不成熟。一段较长的孤处和独处,会有利于思想和形象的归纳。思与诗,这二者的交融正是文学的发展。其他笔墨的写作中,实在也同时会是一部或多部诗的酝酿过程,只是在散文化的记录中,没有在形式上直接达成。这里的关键是,一个写作者是否将诗当成了全部笔墨的核心,如果是,那么他的着力点和最大发力点,终极就一定会是诗。
一部长诗就像一曲纯度很高的咏叹,起落颠簸是很大的,这之前还要有长长的宣叙做以铺垫。以是我虽然没有一气呵成,但肯定是在一个大的感情笼罩下持续事情的。以是说,没有比写诗再耗力气的事情了。
“诗意”与“诗”不同
小说太靠近娱乐了,太依赖故事了。只管后来小说的地位已经上升得比较高了,比如梁启超将它定位于一个民族性情最主要的塑造者,主要到关乎国家的未来。但我们也把稳到,梁的界定虽然成为不刊之论,却毕竟是从事物功用的态度上谈的,而不是精神气格的意义上谈的。就精神与人生的崇高追求来说,小说仍旧有落魄气和末流气。诗最高,关于自然大地的言说也很高。
小说除了娱乐功能太强,还有进入商业时期之后的商品属性太强。我在心里疏远小说,却一贯未能免俗,乃至就自己的几种文体来说,小说的写作量和影响较其他更大一些。这就有些尴尬了。不过我深知作为一种措辞艺术,小说高超的蕴含和表达是多么令人神迷;其余,当代主义小说的边界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小说。就此来讲,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常日在文学性上很难足斤足两,以是凡精良作品一定要具备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当然不包括“伪先锋”。这也是我终极未能放弃小说的一个缘故原由。
“诗意”与“诗”不是同一种东西。“诗意”浓郁到一定程度,并授予相应的形式,才会变成“诗”。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将“诗意”与“诗”混为一团,这是审美和精神格局上的毛病。
“诗意”打破一个临界点之后也就可以称之为“诗”了。统统能够以散文或其他办法表达和呈现的“诗”,都是“广义的诗”,即具有“诗意”而已。“诗”是生命中的闪电,是灵智,与感性和理性有关却又大幅度地超越了它们。这是一种极致化的、强烈的瞬间领悟,是通神之思,是通过措辞而又超越措辞的分外显现。
在一些古代墨客中,就人生的意象和境界来看,我最喜好的还是陶渊明。他的农耕生活除了末了的贫穷潦倒,总能深深地吸引我。他的酒和菊多么迷人,他的吟哦多么迷人。
在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李商隐中,就诗艺而言,就与当代自由诗的间隔而言,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李商隐。他最靠近纯诗的实质,更靠近音乐的特质。只有《三吏》《三别》《卖炭翁》一类,没有《月下独酌》《锦瑟》一类,中国的诗和墨客也就太单一了,诗性也就大打折扣。
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