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正始”是三国期间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年间,正处于魏晋易代之际,朝政阴郁腐败。为躲避灾害,魏晋士人只好悲观避世,“清议”逐渐转为“清谈”,玄学开始兴盛,史称“正始之音”。顾炎武认为,魏晋风骚绅士崇尚清谈,“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导致儒家主流代价不雅观崩溃,从而导致“国亡于上,教沦于下”。他深感明末心学空谈误国,明朝灭亡与社会各阶层未尽到道德伦理任务有关,因而借谈正始之风,反思明朝灭亡缘故原由,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之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和“天下”常被作为同义语利用。但顾炎武认为,“国”和“天下”存在实质差异,“亡国”和“亡天下”不能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如果全体民族礼义损失,道德沦丧,文明堕落,将天下不保。在这里,“天下”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指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在区分“亡国”和“亡天下”的根本上,顾炎武进而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保国”和“保天下”息息相关,掩护社会道德和文化传统以保天下,是“保国”的根本。其次,“保国”和“保天下”的任务主体不同,“保国”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而“保天下”是守卫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道德风气,每位普通人都有义不容辞的任务。因此,顾炎武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清末民初期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根据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论述,提炼出大家都能听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名言,号召国人救亡图存。自此,这一口号成为唤起国公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最强武器。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代价追求,也构成中华精良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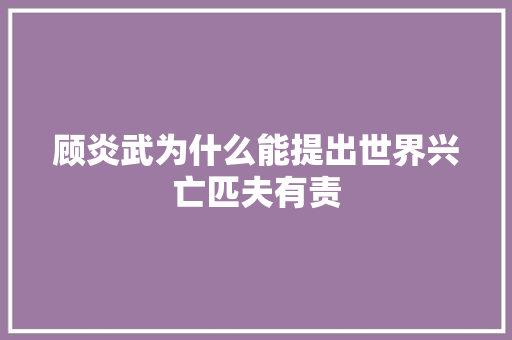
“身沉心不改”的爱国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为什么“有责”?这得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期背景谈起。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值明王朝日渐衰弱,清政权强势崛起的动荡期间。明朝末年,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处于内忧外祸之中。关外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并在1636年正式改国号为清,觊觎中原富庶之地已久。明朝廷内部却党争持续不断,内耗严重。而日益加剧的地皮吞并,导致阶级抵牾非常尖锐,农人叛逆此起彼伏。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旋即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遂挥师南下,开始对全体国家进行血腥的军事征服。清政府入主中原,在顾炎武看来,这不仅是政权上的替代,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断裂,如何保住“正统”文化,成为他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这一思想的产生,与顾炎武的家学传统和个人经历密切干系。顾炎武江苏昆隐士,出生于江东王谢,还在襁褓中时,就被过继给未婚早逝的堂叔顾同吉为嗣,由嗣祖和嗣母抚养终年夜。顾炎武从小就随嗣祖读《孙子兵法》《吴子》《左传》《国语》《资治通鉴》以及朝廷刊行的《邸报》,养成了他关注时势政治、关心现实民生的治学取向。未婚守节的嗣母王氏出生于书喷鼻香门第,性情刚强,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常给顾炎武讲述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忠臣义士的故事,教导他做一个忠于国家民族的人。特殊是清军攻占常熟时,嗣母虽幸免于难,但不愿苟活于世,绝食而亡。她临去世前叮嘱顾炎武要保住气节。嗣母绝食自尽的行为,深深震荡了顾炎武。
为尽“保天下”之责,顾炎武壮年弃文竞武反清,中年骑马北游续道统。1644年5月,南京的明朝残余力量推戴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顾炎武把规复山河的希望依托于这个朝廷,受昆山县令举荐任兵部主事。并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章,提出一整套复兴大计。只是他还未及上任,清军已盘踞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为了表明抗清的决心,顾炎武决定改名。他原名绛,字忠清。因敬仰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忠贞品质,改名炎武。作为一介诗人,他还在家乡积极参加苏州、昆山保卫战。家乡被攻占后,他以精卫填海的精神自勉,立下“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誓言,奔忙于太湖流域,积极开展抗清斗争,其间几经磨难,乃至险遭不测。
随着清朝政权的不断巩固,武装反清复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顾炎武并未气馁,为了坚守空想,他决定北游,探求“保天下”的治国善策。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开始了长达25年的“北漂”生涯。因崇尚儒学,他北上首站直奔山东,游崂山,登泰山,拜孔庙,寻觅名胜文籍,抄录墓志铭,查阅地方志,真正做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走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一边稽核山川民情,结交志同道合的学者,徐图复国大计;一边探求学问,著书立说,寻求经世致用的救国救民之道。把实现民富国强的殷殷期盼写进《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等巨著中,以期“明学术,君子心,拨浊世,以兴太平之事”。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道德追求
天下兴亡,“匹夫”若何才能“担责”?在顾炎武看来,明朝亡国教训在于先“亡天下”然后“亡国”,而“亡天下”根本缘故原由在于,士大夫寡廉鲜耻,损失德行气节,导致士风世风败坏。因此,他提出“风尚者,天下之大事”,认为“治乱之关,必在民气风尚”。在他看来,坚持世道民气既须要经济根本和制度支撑,更须要道德引领与规范。因此,“保天下”就要净化全体社会的风尚道德。他认为,培养良风美俗,既要培养孝悌忠信,又要看重礼义廉耻,还要崇名节、尚厚重。而改变社会道德风气大家都有任务,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为此,他大声疾呼,个人立身处世要坚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
为学要坚持“博学于文”的道德准则,有所作为。“博学于文”出自《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认为,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文籍,再用礼约束自己,就不至于离经叛道。顾炎武继续了这种治学方法,但他提倡的“文”,范围更为宽泛,既指文章、笔墨,更指待人接物、立身处世之道,既指自然科学知识,更包括实践知识。在他看来,治学的终极目的便是经世致用。只有负责学习“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知识,才能做“有益于天下”的有为之事。
为人要坚持“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有所不为。“行己有耻”出自于《论语·子路》,意思是人要用耻辱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顾炎武把“行己有耻”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中,“明耻”最为主要。人有廉耻之心,国家才能形成知荣辱的道德风尚。他还特殊指出,廉耻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尤为主要,并强调“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认为,“有耻”是个人行为的底线。由于知耻才能自觉羞愧,自觉羞愧才能恪守礼义,恪守礼义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代价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