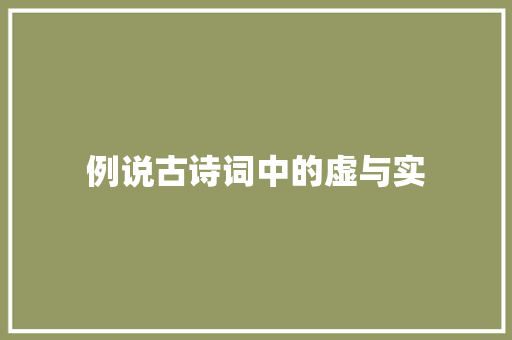一、虚与实 何谓虚实?虚与实是相对而言:有者为实,无者为虚;客不雅观为实,主不雅观为虚;详细为实,隐者为虚;当前为实,未来为虚;已知为实,未知为虚;面前为实,想象为虚。写景为实,抒怀为虚…… 1.诗歌中的“虚” 在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中,虚指图画中稀疏的部分或空缺部分,它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让人回味无穷。诗画同理,诗歌借鉴了中国画的这种方法,诗歌的虚,指的是直觉中看不见摸不着却能从字里行间体味出的那些虚象和空缺的境界。详细来讲古诗中的虚包括以下三类。 ①神仙鬼怪天下和梦境 在诗歌中,墨客每每借助这类虚无的境界来反衬现实,表达自己的渴望、憧憬,这叫以虚象来显实境。《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瑶池便是一个虚象,诗云:“霓为衣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李白描述了一幅和谐温馨、其乐融融的美好图景,以此来反衬现实的阴郁。 ②已逝之境 这类虚象是作者曾经经历过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景象,但现在都不在面前。如“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李煜《虞美人》)句中故国的“雕栏玉砌”此时已不在面前,是虚象。作者将“雕栏玉砌”与“朱颜改”对照着写,一在一不在,一改一不改,颇有故国悲惨、物是人非、世事流变的况味。又如“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再现了火烧赤壁的历史事实,这种景象显然不是发生在面前,故亦是虚象。词人因此周瑜的飒爽英姿、功业有成来反衬自己华年不在、壮怀未酬的悲哀。 ③设想的未来之境 这类虚境是还没有发生的景象,它表现的情将一贯延伸到未来而不绝断,故写愁将倍增其愁,写乐将倍增其乐。“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设想别后的场景:一舟离岸,词人酒醒梦回,只见习习晓风吹拂萧萧疏柳,一弯残月斜挂柳梢;残月缺憾,晓风生寒,今夜我将居住何处?词人想象情人离开后自己的环境,属未来发生的事情,是虚写。解释离愁别恨并非因离人而去而消逝,而是长久绵延,萦绕心头。 2.诗歌中的“实” 在中国画中, “实”指图画中笔画细致丰富的地方,而在诗歌中, “实”指客不雅观天下中存在的实象、实境。“乱石穿空,惊涛骇浪,卷起千堆雪。”这是实象,写赤壁的险要形势。词人以这样的实象陪衬了周瑜漂亮洒脱、伟岸高大的形象,也因此雄阔之景反衬词人苏轼英雄沉沦、壮怀未酬的人生喟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诗词的境界有写境和造境之别,所谓写境,即耳闻目见之境,是实写;所谓造境,即心驰憧憬,全为想象,是虚写。在诗词中虚与实各有其妙,又能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或从对面落笔,以表难言之隐;或以幻作真,表达憧憬渴望,反衬现实之悲…… 二、虚与实的艺术表现 1.虚实相生 虚实相生是指虚与实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从而达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表现手腕。利用这种手腕,能够收到丰富诗歌内涵、深化诗歌主题、强化诗歌情绪、开拓诗歌意境、表意委婉蕴藉、为读者供应广阔的审美空间的艺术效果。有时虚与实又可形成比拟或反衬,从而彰显主旨。 塞上听吹笛 高适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这首诗,前两句写实景,后两句写虚景。由实到虚,虚实结合,相映成趣,给人以雄浑、壮美之感。 一、二两句,写实胡天北地冰雪溶解,战士牧马归来,明月洒下清辉,戍楼里响起悠扬的笛声。这种场景给人以阔大之感,字里行间透露着几份宁静、祥和的氛围,为全诗定下乐不雅观爽朗的基调。 三、四两句,是虚写。紧随一、二句而来应写笛声,但墨客不因此声写声,而是借助想象写声成象。一夜之间落梅满山,落英满地。这两句委婉的表达了羌笛奏出的“梅花落”曲调随风传开,一夜之间声满关山的情景。既形象的表达了思乡之情的普遍性——遍布边塞的角角落落,萦绕在每个戍边将士的心头,强化了思乡这一主题;又与一、二句搭配和谐,构成一种凄美壮阔的意境,丰富了诗歌意象。 对雪 杜甫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 数州断,愁坐正书空。 这首诗是墨客在安史之乱时深陷长安,面对生灵涂炭,生活困难时所写。 首联、颔联和颈联是写实。墨客困居长安贫寒交困,前哨战况、妻儿家室的无从获悉,而自己又身陷囹圄,国难家患集于一身,这怎不忧闷、忧郁。 尾联“炉存火似红”是写虚。这里墨客不说炉中没有火,而偏说有火,而且还下了一个“红” 字,写得彷佛炉火熊熊燃烧,室内一片火红。但墨客在此用一个“似”字点明是幻境。诗人为什么面前会涌现这样的幻境?这是由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对温暖的渴求,墨客面前便涌现了这样的幻境。这种无中生有、以幻作真的描写,深刻的表现了墨客贫寒交困的景况。这是一种在渴求知足的生理使令下涌现的幻象。 全诗除“炉存火似红”一句是虚写外,其它全属实写。诗歌利用“炉存火似红” 这一以幻作真的虚写手腕,深刻的表达了墨客贫寒交困、寒冷难耐的生活情状,又形象的表达了墨客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可谓虚中有实,虚实相生。这种写法既拓展了诗文内,容又有深度。 夜雨寄北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张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一、二句是实写。写不得归之苦和巴山夜雨淅淅沥沥,绵绵密密涨满秋池的景象。 三、四句是虚写,全为想象之词:会有那么一天,夫妻二人重新相聚,秉烛长谈,共同回顾这雨夜彼此相思的情景。这两句虚写既表达了思归之情,又表达了妻室儿女团圆的强烈欲望。以未来团圆之乐来反衬今夜孤苦之悲,而今夜相思之苦又成了未来剪烛夜话的内容。 纵不雅观全诗,后两句的欲望乃是由当前苦衷所触发的对未来欢快的憧憬。愿望归后“共剪西窗烛”,则此时思归之切不言而知,此乃虚中有实;愿望异日与妻子团圆“却话巴山夜雨时”,则此时独听巴山夜雨而无人共语也不言而知,此亦虚中有实。 2、虚写中的对面落笔 想象是诗歌的表现手腕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歌。在古典诗词中有一种奇妙的想象:墨客本来在自我抒怀,但溘然笔锋一转落到对方身上,这样可以使诗歌意境更为开阔,情绪更为深奥深厚,思想更为深刻,行文更富变革,表意更为委婉,诗趣更为盎然 清代墨客刘熙载在论及绝句的弯曲委婉时说:“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须知晴影,知竿乃妙。”(《艺概》)此言道出对面落笔可使诗文富于变革,诗趣盎然。 “对面落笔”亦称“主客移位”。明明是自己思念对方,却说对方有良心身;明明是自己孤独难耐,却说对方愿望团圆;明明是自己不忍拜别,却说对方难以割舍……这样借彼写己,弯曲达意,委婉抒怀,有着悠远绵长的意味。如:“想的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白居易《邯郸大年夜思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大年夜作》)“家人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王建《行见月》)“想得故乡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杜荀鹤《题新雁》) 移家别湖上亭 戎昱 好是东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从诗题来看,明明是墨客舍不得柳条藤蔓,偏说柳条藤蔓拉着自己,牵衣拉裾,不让自己离开;明明是墨客离开时想与黄莺话别,偏说黄莺依依不舍,凄凄啼别。这种对面落笔的写法,蕴藉的表达了墨客对湖上亭一草、一木、一花、一鸟难以割舍的情怀。使诗歌情趣盎然,余味无穷。 游子 孟郊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 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诗通篇只言慈母思念游子,只在题目中透露出是远游他乡的游子在遥念母亲。全诗写的是游子想象中慈母在家思念自己的环境,因情生景,动听至深。 首句,堂前萱草攀生,乃喻慈母情怀之绵长。次句,写儿子远行在外,久别未归,怎不令慈母牵肠挂肚。三、四两句,写慈母倚门眺望,翘首顾盼,在时时等待儿子的归来。由于翘首远方,故而连蔓生堂前的萱草也未曾进入母亲的视线。 全诗将对面落笔的手腕发挥到了极致,全为虚写。这样,一则将自己思念母亲的环境、情绪表达得极为委婉,同时丰富了诗文内容——慈母思念游子,则游子思念慈母在不言中,加深了全诗凄凉的氛围和凄清的情调。 月夜 杜甫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喷鼻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墨客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军捉住,送到沦陷后的长安,墨客望月思家,写下了这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通篇全为想象之辞。安史之乱中,墨客离去鄜州妻小,被叛军所俘,身困长安。夜深人静,面对长安之月,思念妻儿之情油然而生。此时,墨客悠悠思情超过时空的阻隔,从而想象出妻子正在顾虑自己的情景:儿女已睡,妻子独坐窗前,一夜无眠。墨客本意是言自己身陷长安,望长安月而思念妻子儿女,但他却利用想象手腕从对面落笔,写远在鄜州的妻子望月怀远,思念自己:可谓“公本思家,偏写家人思己。”解释墨客在困境中更心焦的不是自己失落去自由、死活未卜的处境,而是对妻子儿女的处境如何心焦。可谓“一地相思,两地离愁” 。这种写法不但委婉蕴藉、弯曲有致,而且加深了诗文哀婉的情调,升华了主题。 寻芳草•萧寺记梦 纳兰性德 客夜怎生过?梦相伴,倚窗吟和。薄嗔佯笑道,若不是恁悲惨,肯来么? 来去苦匆匆,准拟待,晓钟敲破。乍偎人,一灯闪花堕,却对着琉璃火。 这首词写于作者为亡妻双林寺守灵期间。 “客夜怎生过?”凄清的夜晚、荒寒的佛寺、一颗孤寂的诗魂!
词人只能藉梦幻聊以自慰。后面的五句,写亡妻来到魂梦中。妻子情态可人、善解人意的形象跃然纸上。你看那梦中佳人斜倚着窗儿在吟诗唱和,是多么的风情万种!
她假装嗔怒,浅浅一笑,含情脉脉之态叫人爱怜不已。“哼,要不是看你一个人如此悲惨,我才不肯来呢!
”这些措辞和神态描写,写进了柔情蜜意,给全体梦境平添浪漫温馨之色彩。过片,说好梦不长来去匆匆。词人希望梦中的欢愉相会能持续到“晓钟敲破之时” ,无奈梦回肠断,那梦中佳人刚刚还偎依在怀,霎光阴竟如一只翩飞之蝶,飞出梦境之外。词人绸缪留恋之际,睁眼一看,佛寺内一灯如豆,灯花闪落,梦醒之后的词人空对琉璃孤灯又陷入了深邈不仅的哀思之中。 以吊唁亡妻表达夫妻情深为题材的悼亡词,在中国古代词史上虽数量不多但险些篇篇都有撼民气魄的艺术魅力。个中以记梦形式写就的悼亡词更具凄美色彩。常常令人潸然泪下,不忍卒读。迷离恍惚的梦境每每不受时空限定,能弯曲的反响最真实最隐微的情绪,从而有哀婉凄绝之美,备受读者青睐。 虚与实的利用既拓展了诗歌的意境,丰富了诗歌内容,也使诗文在章法构造上跌宕起伏,摇荡生姿。 虚境与实境既是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抒怀主人公抵牾思想的详细表现。虚与实是抒怀主人公今与昔、逆与顺、生与去世、聚与散、挣扎与出逃、绝望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空想与现实等诸多抵牾体的形象再现。这种心灵的折射不是“哀莫大于心去世”的放任,更不是去世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大多是作者渴望美好,给孤单甚或徨恐的灵魂探求出口的积极表现。《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神仙洞府的描写,从艺术形式上来看因此虚衬实,以美好空想反衬尔虞我诈、嗜血横暴、誓不两立的阴郁现实。从精神角度来看,是墨客在痛楚现实中竭力摆渡人生,给心灵寻觅渡口的积极表现。在兵荒马乱的安史之乱中,杜甫被囚长安,大概能给墨客抚慰的只剩下不省人事儿女和美如西施的妻子。有不舍,有牵绊,表明墨客还在守着魂灵,心是鲜活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只要人生还有念想,生命便不会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