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成宇 | 主讲:成宇
上期答案
过故人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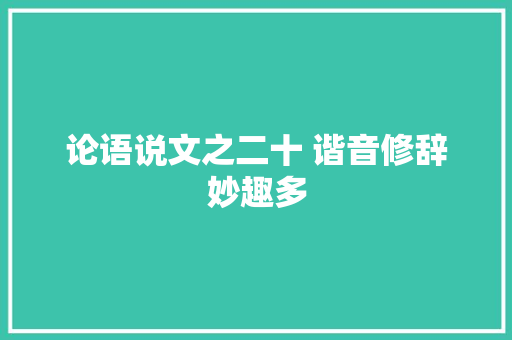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舍。
绿树村落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唐代墨客孟浩然。菊花除了凌寒不屈的象征意义以外,还有龟龄的象征意义。古人就有重阳节送长辈菊花的习俗,表示对长辈的尊敬和祝福龟龄之意。菊花的别称有傲霜枝、东篱、寒英、黄花、霜英、金精、金蕊、冷喷鼻香、日精等。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无耻之徒大献殷勤,纷纭祝贺,贺联中有一署名“灵谷老人”的对联写道“昔具盖世功,今有罕见才”,拍马者对此联大加讴歌,汪精卫也洋洋得意,忽有人指出此联谐音“昔具该死功,今有汉奸才”,此时汪精卫才觉醒自己被骂,这便是谐音的妙用。
谐音是用同音或近音的字词构成分外表达的一种手段,是对同音征象的积极利用和开掘。在汉语、汉文化中,谐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艺术,而国人又将这一措辞艺术发挥到极致,其言在此,而意在彼,妙趣良多,雅俗共赏。
谐音之雅,在诗词等文学形式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示。古典诗词常以“柳”入文。《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李白《劳劳亭》:“东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柳永《雨霖铃》云:“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诗句借用“柳”,是由于“柳”和“留”相谐,古人折柳枝送别以示挽留之意,以“柳”入文,依依别情蕴藉而朴拙。“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莲子”谐音“怜子”,一幅生动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 妖童媛女采莲之时,不忘“怜爱于你”,“无字处皆其意”,虚实相生气韵生动。
谐音不仅是阳春白雪,也是下里巴人;不仅为文人骚客所喜好,也为世俗之人所喜闻乐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谐音双关的妙用,表示了谐音雅俗共赏的文化特质。
谐音之俗,表示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处不见谐音。明代《推篷寐语》记载:“世有误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之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箸”字因与“住”谐音,随意马虎引起“结束”的遐想意思,犯忌讳,以是转而反其意而称“快”,先在民间盛行,后来士大夫也采取,于是社会上都改称“快子”,反而忘了它的本名。由于筷子多为竹制,后来又在“快”上加了竹字头,就成了“筷子”。婚俗中,于新人被褥之中撒“枣”“花生”“桂圆”“栗子”,即谐音 “早生贵子”之意;给新娘子吃面或饺子,不能做熟了,由于要“生”;以博取好的兆头。在中国剪纸、中国画、中国刺绣中,也能看到与谐音有关的内容。在这些艺术作品中,鱼、羊、鹿、猴、蝙蝠、马等常常成为主角,于是有了“金玉(鱼)满堂”“三阳(羊)开泰”“五福(蝠)捧寿”“鹿和(鹤)同春”“立时封(蜂)侯(猴)”“福(蝠)禄(鹿)双全”诸如此类的吉祥图、吉祥语。
在当代措辞利用中,尤其是在商业广告中、网络措辞中谐音征象更是比比皆是,有些巧用针言谐音既达到了宣扬产品的效果,增长了措辞意见意义。然而“物无美恶,过则成灾”。如果不考虑表达效果、措辞规范,而滥用谐音,也和规范化的措辞原则相背离。因此,利用谐音,要把握好“度”,应以符合规范、经济方便、利用适度为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