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在战后波兰文学中,切斯瓦夫·米沃什霸占着重要的位置。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文学相辅相成,始终环绕着两个关键词,即“战役”与“流亡”。
1939年,已是著名墨客的米沃什在华沙加入左派抵抗组织,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这一期间,他见证了第二次天下大战和纳粹大屠杀,也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所处时期与欧洲文化的精神危急。1951年,米沃什正式走上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是在法国寻求庇护,随后于1960年移居美国,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执教生涯。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流亡使米沃什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外部环境的间隔感和客不雅观性,多年以来,他坚持以波兰语创作,企图在“崇奉已去世”的时期中探求人类生存的出路。
可以说,米沃什的文学是根植于波兰而面向天下的。他在诗歌中显露出的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令人惊愕,正如爱尔兰墨客谢默斯·希尼所言,这套知识在表面上看是墨客的东欧履历,核心却是对宗教传统的眷恋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心。这一点在米沃什阅读的其他文体与风格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例如讲述二战后中东欧知识分子处境的传记《被禁锢的头脑》、阐述诗歌之于时期的主要性的论著《诗的见证》、呈现20世纪历史文化的回顾录《米沃什词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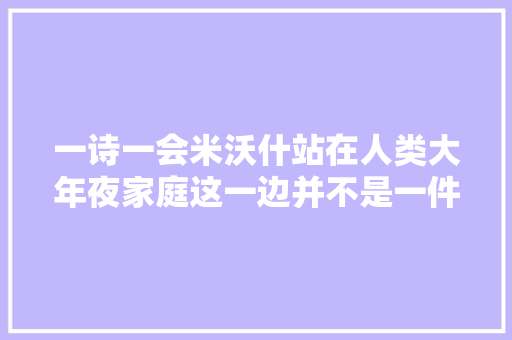
对付多数中国读者而言,米沃什的非虚构作品或许比诗歌更能表示他作为一名“流亡墨客”的影响力,个中一些哲学议题被反复提及,标志了作家最关怀的根本性问题:历史的意义;邪恶与苦难的存在;生命的短暂;科学天下不雅观的崛起与宗教想象力的衰落。日前出版的《站在人这边》辑录了米沃什最主要的随笔作品,包括传记性和自传性的素描、对哲学和宗教的沉思、对诗歌创作以及几位主要墨客的评论等。这些作品的韶光跨度达五十余年,却在主题上保持了高度的连贯性,表露了米沃什精神发展的诸多方面以及他对当代诗歌的思考。
米沃什认为,当代西方的悲剧就在于人们忘却了人的神性来源,而断然以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取而代之。在磋商诗歌创作的文章《反对不被理解的诗歌》中,步入晚年的米沃什深刻批驳了那些难懂、贫乏、方向于纯粹形式练习的仅供精英阅读的诗歌。他进一步激赏了W·H·奥登的不雅观点,即诗歌“必须尽其所能赞颂存在和事宜”。这就意味着墨客对外部现实的描写不应仅仅勾留在临摹的层面,而该当以顿悟的眼力对现实进行一种揭示。有趣的是,这一诗学不雅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米沃什在阅读古代东方诗歌时受到的启示。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文中节选干系内容,以飨读者。
《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节选)
文 | 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 | 黄灿然
在经历了献身于反省和写作的漫永生活之后,我一贯在思考对我来说什么才是我反省的核心。我得出的结论是,它与我十五岁时完备相同,那时我在罗顿时帝教家庭中终年夜,首次在我的生物课上碰着所谓的科学天下不雅观。没错,我们现在听说我们都学会了把两个领域分开,听说宗教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没有共通之处。然而,我们的科学技能文明的宗教想象力一贯都在无可阻挡地削弱。那些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宗教,在坚持他们的崇奉时都碰着重重困难,不管他们承不承认。那些接管崇奉的恩典的人所信的,已经不同于他们的先辈。
这番话作为反省诗歌的弁言,难免不免有点古怪。我们大概要质疑,这些困扰神学家或哲学家的心思的问题,对本日的墨客到底有何意义。我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而我将考试测验阐明为什么。
文学和艺术已变成与基督教分开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文艺复兴期间的人文主义者们创造古代墨客和哲学家,从而触发他们守卫理性法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十九世纪的科学天下不雅观涌现之后,这个过程便急剧地加速。与此同时,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同样的缘故原由,诗歌进入了这样一个领域,那里有关人买卖义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那里心灵必须努力搪塞意义的缺席。在这个脉络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墨客是塞缪尔·贝克特。
这并不虞味着我们的世纪没有产生受宗教启示的诗歌精品,赖纳·马里亚·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宗教灵感并不一定意味着基督教灵感;有些例外,包括其作者以某个基督教教会的成员说话的长诗——譬如保罗·克洛岱尔的《颂歌》或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明显不过的是,它们必须战胜一种主要抵抗,既要抵抗公众年夜众的知识习气,又要抵抗诗歌中所有被认为是当代的东西。
我必须承认,被当成当代墨客,我并不感到舒畅,承认我对以各种名目涌现的“纯诗”(它被以一系列名称提出来)持疑惑态度,由于我在人们对这路诗歌的赞颂中觉察到偶像崇拜。然而,在我青年时期,我也积极参与社会,而我知道这条逃离塔楼的道路并没有通往好结果。
彷佛我们都是眼见者,眼见这个以“当代性”为名的包含各种理念的复合物的解体,而在这个意义上“后当代主义”一词是适用的。诗歌已不知怎的变得更谦卑,大概是由于对艺术作品的永恒和永久性的崇奉已经受到削弱,而这当然是对“庸众”的鄙视的根本。换句话说,诗歌已不再孤单地望着自身,而是开始转向外部。在美国,如果诗歌不雅观察当今人在这个科学技能文明阶段的处境,连同其缺少代价根本,连同其在爱和家庭的纽带中探求温暖和蔼,连同其对付无常和去世亡的畏惧,它就会使我感兴趣。我还从中觉察到高高在上的伶仃的传统,从而觉察到形式繁芜性的传统,后者源于畏惧来自封闭的社会环境的友好判断。这乃至表现在遣词造句中:无数为普通人所难以理解的说话,哪怕是想象自己是精英的一部分的读者也得偷偷跑去查百科全书;还有,浩瀚对当下知识分子中盛行的理论和奇思妙想的指涉。大概大众文化的粗俗本身连续迫使少数人在一个常规符号系统中寻求庇护;在过去,波希米亚常常寻求庇护,以躲避资产阶级和市侩,但在这场精英与不足高雅者之间的辩论中,站在“人类大家庭”这一边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很多译成英文的中国和日本古典诗使我有很多感想。它们被很多不喜好读当代诗并责怪当代诗难懂、贫乏、方向于纯粹形式练习的人激情亲切地阅读。显然,在我们的世纪末,这些远东墨客所写的诗更贴近读者的须要。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它们有什么特色?这样说吧,它们的背景是一个文明,它不同于我们的文明,它强烈地受到非有神论宗教例如玄门和佛教的影响,这些宗教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不同的理解。谁知道呢,大概这证明了佛教徒关于科学天下不雅观与佛教没有冲突的说法,只管很难与圣经中人格化的上帝相容。但还有别的东西。西方思想的根本一向是对立的:主体对客体。“我”对外部天下,外部天下必须被认识和节制。而这正是西方人的史诗的内容。在很永劫光里,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一种平衡。专断的“我”在这种平衡被扰乱时涌现。愈来愈趋于描写客体的绘画,就很好地解释了这点。
在古代中国和日本,主体与客体不是被理解为对立的范畴,而是同一的。这很可能便是带着深深的敬意描写我们周围环境、花草、树木、风景的根源,由于我们可以瞥见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但仅仅由于事物是它们自身并保持它们的真如——借用禅宗的一个用语。在这种诗歌中,宏不雅观天下反响在每一个详细细节中,犹如太阳在一滴露水里。
东亚诗歌的榜样,还启示我去别处探求类似于我在东亚诗歌中找到的优点。犹如在参不雅观了迢遥国家的美术馆之后我们回到本国的美术馆,并以新眼力来看待它们,同样地,欧洲和美国诗歌也向我揭示了一股特殊的趋势,而以前我对它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把稳。我开始挑选各种措辞中由于尊重客体而不是主体而使我喜好的诗,并萌生了编辑一部诗选的动机,这些诗既符合我的哀求,又颠覆了诗歌是不可避免地晦涩和难懂的这一普遍意见。
得益于我在多种措辞中的阅读,我一贯都在准备一部极其变革无常的当代诗选,它反对当代诗的紧张趋势:反对大量的艺术隐喻和不受口语意义约束的措辞布局。我探求诗行的纯粹、朴实和简明。例如沃尔特·惠特曼这首短诗所展示的:
在平坦道路上那个演习有素的奔跑者奔跑着,
他精瘦而肌肉发达,双腿强健,
他衣衫细薄,他奔跑时向前倾斜,
双拳轻攥,双臂稍稍抬起。
(《奔跑者》)
西方诗歌近期已经在主不雅观性的小道上走得如此远,甚至不再承认客体的法则。它乃至彷佛是在流传宣传统统存在的事物都是觉得,根本没有客不雅观天下。在这种情形下,你想说什么都可以,由于已经完备失落控了。但是禅宗墨客建议我们从松树理解松树,从竹理解竹,而这是一种完备不同的不雅观点。
回到我的重点。当W.H.奥登说诗歌“必须尽其所能赞颂存在和事宜”时,他是在表达一种神学崇奉。在西方思想中,对生命切实其实定有漫长而卓著的历史。托马斯·阿奎那在上帝与纯粹的存在之间画上等号即属于这个范畴,犹如人们不断把恶与存在的不敷等同起来,由于妖怪利用这种不敷而充当了虚无的力量。在这个历史中,还有歌唱自然的神奇,自然被视为造物主双手创造的精品,这精品授予无数画家灵感,也为学者们供应强大的动力,至少在胜利地占上风的科学的最初阶段是如此。“对存在的神奇性的玄学觉得”紧张是指我们在沉思一棵树或一块岩石或一个人的时候,溘然明白它如是,只管它可能并非如是。
意味深长的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诗歌中,尤其是在法国诗歌中,描写能力一贯在消逝中。把一张桌子称为桌子太大略了。但不应忘却——让我们再次拿诗歌与绘画作比较——塞尚不断调度他的画架的位置,画同一棵松树,试图用他的眼睛和心灵吞噬它,穿透它的线条和颜色,由于它的繁复性使他以为耗之不尽。
描写哀求强烈的不雅观察,如此强烈,甚至日常习气的面纱脱落,我们以为过于普通因而未加把稳的事物奇迹般显露出来。我不想遮盖一个事实,也即我在诗中寻求显露现实的原形,也即希腊语所称的epifaneia。这个词曾经首先用来指神灵在凡人中显现,也指我们认出化身为普通、熟习的形状例如化身为人的神灵。因此,显现中断了日常的韶光流,从而犹如我们在某个荣幸的时候本能地捉住隐蔽在事物或人物中更深刻、更实质的现实那样进入个中。一首显现诗讲述一个瞬间事宜,而这须要借助某种形状。
显然,这种类型的显现,在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这个意义上,并不会耗尽笔墨的所故意义。它还可以表示感官向现实洞开。在这点上,眼睛彷佛是享有特权的器官,但显现也可能借助听觉和触觉而发生。不值得去竭力达致精确地定义它依赖什么;那会使我们太受限定。一样平常来说,当把稳力中央那被感知的物体及其描述达至比一个人物的生理、紧张情节等等更大的主要性的时候,我们便是在跟显现打交道了。
在日本俳句中,显现的发生,是作为某种微光、某种在瞬间被意外瞥见的东西,宛如彷佛闪电或火箭的强光使我们熟习的风景变得不同。例如,在墨客一茶(1763-1827)这首诗中:
从树枝
漂浮在河流上
昆虫之歌。
与此干系的是墨客米龙·比亚沃谢夫斯基(1922-1983)的感知短诗,他大概是波兰诗歌中最“东方”的。就他而言,这很可能与他的生活办法有紧密联系,这种生活办法使认识他的人感到犹豫:对自己一点也不在乎,一种离群的态度,险些是一个完美的佛僧。
大概,再也没有什么比为巴西墨客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诗供应主题的东西更大略和更明显的了。当一样事物被真正地瞥见,专心地瞥见,它便永久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惊异,只管它本身彷佛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
在道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有一块石头在道路中间
有一块石头
在道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在我这怠倦的视网膜的生平中
我将永不会忘却这次事宜。
我将不会忘却在道路中间
有一块石头
有一块石头在道路中间
在道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在道路中间》)
顺带说一下,这个例子可使我们相信,被不雅观察到的事物能被笔墨捕捉到的是多么少,由于很大略,措辞因此不雅观念来运作的。“石头”并非恰好便是这块石头,也没有特定形状和颜色——只是一样平常的石头。为了把它描述成它应被描述成的样子,我们得耗费巨大心力。同样地,读到“道路”,我们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道路——一条人迹罕见的小路、一条土路还是一条沥青公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这首诗很出色地描写与物体相遇的瞬间,但是它难以令人满意,说句实话,就犹如任何旨在把感官知识转化成笔墨的企图那样,只能多多少少令人满意。
以这种办法编选的诗,会使我们相信它与神秘的沉思有关,只管诗中所描写的题材是天下本身。而鉴于天下在诗中常常被理解为上帝的身体,大概我会被称为泛神论者。这将是精确的,如果对物质天下的虔诚态度与一种斯多葛式接管物质天下那无所不包的、独特的存在的态度携手共进,犹如在卢克莱修的作品中。然而我想,人类命运的悲剧不许可这样沉着地接管宇宙那壮丽、自足的构造,而对苦难不闻不问。基于这个情由,我很难赞许佛教的办理方案。唉,我们的基本履历是双重的:心灵与肉体、自由与一定性、恶与善,当然还有天下与上帝。这与我们对痛楚和去世亡的抗议是一样的。在我所选的诗中,我不寻求躲避恐怖,反而是要证明恐怖和敬畏可以在我们身上同时存在。
我编选这本诗集的意图,超越了文学领域。普通人所感所思都很多,但他们无法研究哲学,并且不管若何,哲学能给予他们的并不多。事实上,严明的问题通过创造性的作品抵达我们,而创造性的作品表面上彷佛只是把艺术技巧作为其目标,只管它们装满了每一个人向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大概,正是在这里,在供精英阅读的诗歌的围墙里,一道门打开了,把诗歌引向所有人。如果我这守卫诗歌、反对狭窄和枯竭的考试测验被视为浩瀚可以做到的考试测验之一,我将会感到很知足。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站在人这边》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
|ᐕ)⁾⁾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大众年夜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