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谬法,便是故意把对方的谬误向前推进一步,使之变成更加显而易见的荒诞可笑的一种手腕。归谬诗,便是指用归谬格创作的诗词。
清朝时,有个秀才把“琵琶”写成“枇杷”,有人用归谬法写诗嘲讽这事:
琵琶不是此枇杷,
只恨当年识字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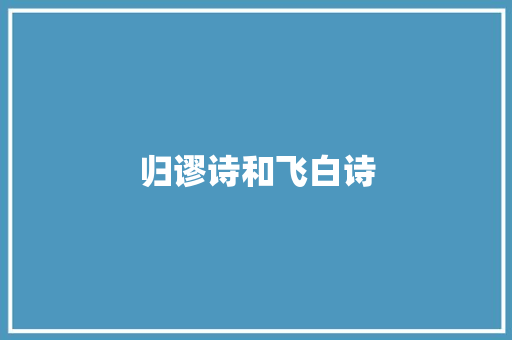
若是琵琶能结果,
满城箫管尽着花。
还有一个秀才写信给朋侪,不但把“琵琶”错作“枇杷”,而且还把“舴艋”错作“蚱蜢”。朋侪收信后,写了下面的联子回敬他:
筵上出枇杷,
吃呼?弹乎?
原来是无声之乐;
河中不雅观蚱蜢,
蹦也!
跳也!
还同那不系之舟。
北宋书法家米芾,当县令时,遇上蝗灾。他发动百姓捉虫灭害。不料,邻县昏官诬说米芾把蝗虫赶到他的县里去。米芾不与其争辩,题诗一首回赠:
蝗虫本是天灾,
不由人来安排。
若是敝邑遣去,
却烦贵县发来。
诗中包含这般推理过程:
如果你县蝗虫,是我县赶过去的;
那么你县蝗虫,给我县发回来吧。
既然你县蝗虫,无法发送给我县;
那么你县蝗虫,就不是我县赶去的。
米芾利用归谬推理,驳得邻县昏官无言以对,自讨没趣。
飞白诗
飞白诗
将错就错,称之曰飞白。利用飞白格作的诗,名之曰飞白诗。
秦时阮翁仲,身高丈三,秦皇命他出征匈奴,去世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因称铜像或墓道石像为“翁仲”。
清朝,翰林院有个大臣,在表折中将“翁仲”误作“仲翁”,这使一向严谨的乾隆天子大为不悦。一怒之下,将此人贬到山西作通判,并作飞白诗戏之。曰:
翁仲如何说仲翁,
只因窗下少夫功。
从今不许归林翰,
贬汝山西作判通。
诗中,乾隆将错就错,将每句诗的末两字都作了颠倒:翁仲——仲翁,功夫——夫功,翰林——林翰,通判——判通。
明朝,英宗天子出游,有个祭酒刘某和诗奉承,诗中错把“雕弓”吟作“弓雕”。一个寺人听后,以为十分可笑,故意用飞白格将“雕弓、标志、祭酒、朝廷”数词颠倒作诗,以讥之,曰:
雕弓难以作弓雕,
似此诗才欠致标。
若使是人为酒祭,
算来真个负廷朝。
宋朝,一个解元自命不凡,一次瞥见书本里有“蔡中郎”一词,以为书本错了,便大骂古人连“郎中”都不懂。旁人闻之,嗤之以鼻,赋诗戏之:
转业当郎中,
大门挂牌招。
如何作元解,
归去学潜陶。
中郎,官职;郎中,年夜夫。自己学浅,说人笔误,如何不可笑!
难怪人家颠倒“招牌、解元、陶潜”来飞白他一下。
鲁迅短篇小说《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名称,用的也是飞白辞格。古云“上大人,孔乙已。”孔子一个人而已。由于“己”、“已”形近,后来就谣传为“上大人,孔乙己。”“已”、“己”不辩,儒岂不腐?可惜中学语文教材的注释,竟没看出“飞白”。这,大概也是一个诙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