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杂谈说了诗词的格律,这期我们来说说对联的对仗,对仗涌现的韶光要早于对联很多,从诗经、楚辞乃至散文、骈体文、诗词曲赋都有对仗句涌现,对仗对付对联来说更是应有之义,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律诗,那么这篇文对付律诗的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对联的核心特色是对仗,但是对仗涌现得比对联早多了。《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说这种对仗之美是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乃至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在对联涌现之前,先秦的《诗经》《左传》都有大量对仗,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又如“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等等。再之后,律诗和骈文自不必说,对仗是它们的“必选科目”,而散文和古体诗也不乏对仗的成分。至于对联,则是将这种对仗美发挥到极致,成为一种以对仗为核心的独立文体。
那么,什么是对仗,若何在创作中运用对仗呢?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大略——对仗与对偶大同小异,恐怕连小学生都懂,难道还有什么须要研究的吗?可惜事实是残酷的,很多人对对仗的理解似是而非,运用起来更是错漏百出,乃至有不少人用自己僵化的对仗不雅观念去衡量他人作品,那真是误己误人了。
鉴于此,我想非常有必要负责梳理一下对仗的观点以及该当若何利用对仗。须要解释的是,我没有笔墨学、修辞学、语法学的科班功底,以下只是从实际创作的角度出发,在古人律诗或对联作品的根本上,谈一些自己的履历和心得。想来是有不少不严谨的地方,也只好勉强开解自己“虽不中亦不远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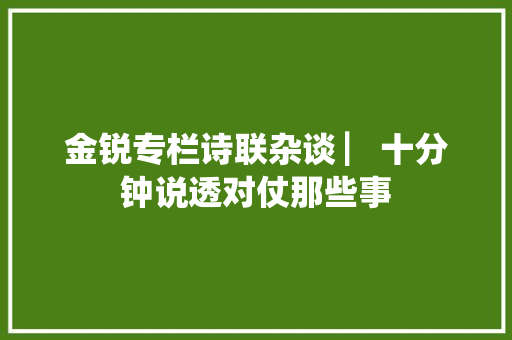
词性与构造
如果用当代汉语阐明对仗的特点,该当可以概括为“词性附近”。
“词性”是当代汉语的总结,古人没有这个观点,如果生搬硬套,难免似是而非。但是介于加入“词性”的观点便于理解,以是在初学阶段可以暂时性引进。不过千万不可拘泥,这就像一根拐棍,当能够正常走路之后,就一定要武断地抛开它。因此,这里不说“词性相同”而说“词性附近”。
当代汉语将词性分为以下几类:
实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差异词、代词、数词、量词
虚词类: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拟声词、叹词
相同词性肯定是可以形成对仗的,我们要研究的是对仗的边界。
首先看最主要的名词。直不雅观来看,名词和代词肯定可以相对,比如“海阔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天”是名词,“我”是代词。此外,名词有时也可以和数词、量词、形容词等形成对仗:
名词对数词:海国烟霞笼宝树;一天星斗灿云阿。
名词对量词:解带千山雨;谈天一片云。
名词对形容词:尘榻每缘佳客下;清风还许后生传。
动词和形容词是天然可以形成对仗的,比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阔”是形容词,“悬”是动词。此外,动词还可以和连词、介词、副词等对仗:
动词对连词:药院爱随流水入;山斋喜与白云过。
动词对介词:白气夜生龙在水;碧云秋断鹤归天。
动词对副词:鼎鼎百年皆梦幻;悠悠万事判穷愁。
形容词是润色名词用的,那么很随意马虎想到,同样起到润色浸染的数词自然可以与形容词对仗,比如“自傲胸中无一事,得居林下作闲人”,“一”和“闲”便是范例的数词对形容词。有些时候,副词也可以与形容词对仗,由于二者都起到润色中央语的浸染,只不过一个是润色名词,一个是润色动词而已,比如“赖有清吟消意马;岂无美酒破愁城”,“清”是副词,“美”是形容词。
一样平常情形下,虚词的对仗是比较宽泛的,比语气词、拟声词、叹词等,每每都可以冲破边界随意对仗。也常常有虚词与实词相对的情形,前面所举的连词对动词、副词对形容词都是例子,而助词与代词相对更是可以视为工对,比如“君为来见也;吾其与闻之”。
之以是用了这么多篇幅讲词性对仗,又没有明确哪些词可以对仗哪些词不能,缘故原由有二:一是解释不必严格拘泥于词性对仗,赞助参考即可;二是用词性剖析对仗,既不准确也未便利,实在没有必要。
有些人除了哀求词性对仗,还哀求构造对仗。常说的“构造”包括两种,一种是句子构造,一种是词组构造。句子构造完备不必剖析,由于诗词对联是凝练的笔墨组合,个中有大量的省略、倒装,根本无法也无须考虑句子构造。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上苍”,按照句子构造剖析,“翠柳”是方位状语后置,“上苍”是宾语,不须要纠结这种地方。至于词组构造,比如偏正构造、动宾构造、主谓构造等,有人主见词组构造必须相对,这个说法可以参考但同样没故意义,缘故原由便是前面说的:既不准确也未便利。
虚实去世活
既然古人完备没有词性的观点,那么古人是如何判断是否对仗以及对仗的工致与宽泛呢?明代屠隆在《缥缃对类》中有关于字类的解读:
以“虚、实、去世、活”字教之。盖字之有形体者谓“实”,字之无形体者谓“虚”;似有而无者为“半虚”,似无而有者为“半实”。实者皆是去世字,惟虚字则有去世有活。去世,谓其自然而然者,如“高、下、洪、纤”之类是也。活,谓其使然而然者,如“飞、潜、变、化”之类是也。
关于这段话,不必作严格的学术性剖析,大概可以看出,古人是根据字的自身属性来分门别类的。与当代语法干系联——实字基本是名词,虚字有活字去世字,活字是动词、去世字是形容词。对仗的时候,首先考虑这个字的意思,然后有一个大体的归类,如果能归到差不多的种别,就可以形成对仗。
对仗中最主要的是实字。在古人看来,并非实字对实字即可,这只能属于宽对,而风雅的对仗该当利用工对。何谓工对?古人将实字分为许多门类,只有相同门类或附近门类对仗,才能形成工对。实字的分类有很多种,王力在《诗词格律》一书中“依据律诗的对仗”,将实字分为天文、季候、地理、宫室、衣饰、植物、动物、形体等种别,大略举例如下:
天文:日、月、星、云
季候:春、秋、晨、夕
地理:山、河、地、海
宫室:屋、门、户、窗
衣饰:带、襟、领、袖
植物:花、草、树、木
动物:鱼、鸟、虎、牛
形体:手、足、耳、头
除了实字,还有一些字也可以明显分类,比如:
方位:上、下、前、北
数字:独、三、万、双
颜色:红、绿、青、白
人伦:公、父、子、兄
称谓:尔、其、我、君
这些小类难以逐一列举,也无法准确的划分,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字义自行分类。除了相同门类可以形成工对以外,不同门类也有远近的差异,相对较近的门类相对同样可以视为工对。比如,天文对地理、动物对植物、人伦对称谓,等等。
孰公孰宽不须要去世记硬背,大略归纳便是:如果字A属于门类甲,字B属于门类乙,门类甲和门类乙的范围越小、重合度越高,字A和字B的对仗越工致。比如,牛属于家畜类,猪也属于家畜类,它们无疑是工对,虎则是野兽类,与牛相对就稍宽一点,但仍旧很工。再宽一些,草对牛,它们都属于生物(虽然这是当代科学观点,但是古人花木、鸟兽也属于附近的门类),范围更大了一些,这就介于工对与宽对的边界。到了“牛对水”或者“牛对日”的时候,虽然也是合格的对仗,但门类相隔太远,只能算宽对了。按照这样的对仗逻辑,白雪当然可以对南山,但是从工致来讲,青云对白雪才是工对。
一副对联的利害有很多层面,比如意境、气候、格调等,对仗只是个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说工对就一定赛过宽对,但如果只谈论对仗的技巧层面,那当然是越工致的对仗越动人。
对仗的基本单位
对仗的基本单位是语素。语素是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字,但大多数情形下是一个字。可以将词作为整体进行对仗,但是不多也不好。比如以下两个例子:
澧阳书院(陶澍)
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
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
挽甥(彭玉麟)
定论盖棺,总系才名辜马谡;
灭亲司法,自挥老泪哭羊昙。
两副对联都利用了人名对仗,第一联是“车武子”对“范希文”,第二联是“马谡”对“羊昙”。可以看到,第一联因此人名为整体进行对仗,也便是人名对人名而已。第二联则因此单字进行对仗,不仅是人名对人名,还把人名中的字拆出来,以“马”对“羊”形成工对。仅仅从对仗的技法来看,后者无疑是远胜于前者的。
一样平常情形下,词的对仗和字的对仗是同步的,比如“清风”对“明月”,无论词的角度还是字的角度都属于工对。词对仗而字不对仗的情形,如前面所说“车武子”对“范希文”,虽然不能说失落对,但毕竟不算工致。至于字对仗而词不对仗的情形,我认为是可以属于工对的,缘故原由如前所述——对仗的单位是语素,语素每每表示为一个单独的字。比如,
洪亮吉题某酒楼对联
第一楼边浮大白;
初三月上荡空青。
此联的对仗非常有特点。上联的“边”是方位词,下联的“上”是动词,从词性角度看是不符合的,但是如果从语素的角度,两个词都是“方位类”,自然属于工对,这种对法也可以看作“借对”中的借意对。上联的“大白”是酒,下联的“空青”是颜色,一个名词一个形容词,以词为整体考虑并不对仗,但是详细到每一个字,“大”和“空”表程度,“白”和“青”表颜色,是非常严格的工对。
更加极度的例子,比如
丁中翰题西湖宋庄联
红杏领东风,愿不速客来醉千日;
绿杨足烟水,在小新堤上第三桥。
末了一分句每个字都可对仗,又有“千”和“三”等非常工致的对仗,以是连行文的节奏都冲破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对仗不必考虑“构造”,无论是词组构造、句子构造,还是行文节奏造成的语义构造。当然,这属于比较高等的对仗技巧,初学者不易节制,利用不当也会涌现弄巧成拙的情形。
二十九种对
日本和尚空海曾著《文镜秘府论》一书,个中总结了中国唐代的对仗理论,归纳为“二十九种对”,个中写道:“余览沈、陆、王、元等诗格式等,出没不同。今弃其同者,撰其异者,都有二十九种对。”
“二十九种对”可以看作中国古代的对仗理论体系,个中包括:
正名对、隔句对、双拟对、联绵对、互成对、异类对、赋体对、双声对、叠韵对、回文对、意对、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临近对、交络对、当句对、含境对、背体对、偏对、双虚实对、假对、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总不对对。
这些对法之中,有一些是专用于写诗的,比如:“隔句对”是“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第二句与第四句对”;“总不对对”是“总不对之诗,如此作者,最为佳妙”。这些与对联的对仗规则无关,以下选取可借鉴的对法简而述之:
的名对:便是字字工致的对仗,“凡作文章,正正相对”“初学作文章,须作此对,然后学余对也”,比如“东圃青梅发;西园绿草开”“砌下花徐去;阶前絮缓来”。
互成对:可以理解为附近门类的字连用组词,“两字若高下句安之,名的名对;若两字一处用之,是名互成对”,比如“天地心间静;日月眼中明”“麟凤千年贵;金银一代荣”。
异类对:便是宽对,高下联门类相差较远,“非是的名对,异同比类”“其类不同,名为异对”,比如“天明净云外;山峻紫微中”“鸟飞随去影;花落逐摇风”。
双声对:声母相同,比如“年夜方气弥壮;淋漓兴未衰”,“年夜方”“淋漓”即是双声对。
叠韵对:韵母相同,比如“徘徊夜月满;肃穆晓风清”,“徘徊”“肃穆”即是叠韵对。
意对:对仗比“异类对”更宽,介于对与不对的边缘,但是意思连贯,“事意相因,文理无爽”,比如“客子河梁携手去;西山秋色上衣来”。
平对:“平常之对,故曰平对”,比如“云对雪,雨对风,宿鸟对鸣虫”,和的名对类似。
奇对:“既非平常,是为奇对”“出奇而对,故谓之奇对”,比如“陈轸”对“曾参”、“马颊河”对“熊耳山”,每字都是工对(“轸”“参”为星宿名,“马”“熊”为动物,“颊”“耳”为形体),但与的名对、平对照拟,更加出其不虞。
字对:也该当属于工对的一种,但字义转借相对非常明显,“不用义对,但取字为对也”“字对者,谓义别字对”,比如“何用金扉敞;终醉石崇家”“行李淹吾舅;诛茅问老翁”。
声对:借声相对,比如“彤驺初惊路;白简未含霜”,“路”借其声“露”与“霜”形成工对,又如“初蝉韵高柳;密茑挂深松”,“茑”借其声“鸟”与“蝉”形成工对。
侧对:借单形的一部分进行对仗,比如“冯翊”对“龙首”,本来是很宽的对仗,但“冯”的右边是“马”,与“龙”同属动物,“翊”的右边是“羽”,与“首”同属形体,“谓字义俱别,形体半同”。
交络对:为了不以对害意,有时可以改变高下联对仗的位置,比如“大江流昼夜;西北有高楼”,实在因此“大江”对“高楼”、“昼夜”对“西北”,又如“裙拖六幅湘江水;髻耸巫山一段云”,实在因此“六幅”对“一段”、“湘江”对“巫山”。
当句对:便是自对,在诗中的运用大体类似于“互成对”,但高下联的对仗更宽一些,比如“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在对联中,自对的运用非常广泛,不仅限于一句之间,常常会在长联中利用几个分句的自对,技法也更加丰富,详见《对联创作中自对的运用》一文。
偏对:大概便是不工致的对仗,与“意对”类似,“全其文彩,不求至切”“但天然语,今虽虚亦对实”。比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春豫过灵沼,云旗出凤城。”
双虚实对:虚字与实字进行对仗,“此对当句义了,不同互成”,比如“故人云雨散;空山来往疏”,“云”“雨”为实字,“往”“来”为虚字。
切侧对:便是对仗在工宽之间,似工非工、似宽非宽,“精异粗同”。比如“浮钟宵响彻;飞镜晓光斜”,粗看以“浮”对“飞”、“钟”对“镜”十分工致,但是“浮钟”为钟声,“飞镜”为月,一虚一实,又似宽对。
双声侧对:便是原来不对仗的两个词由于都是“双声”,以是可以看为难刁难仗,“谓字义别,双声来对”。比如“花明金谷树;叶映首山薇”,“金谷”和“首山”都是双声,以是可以对仗(古汉语中“金”为“居音”切,“谷”为“古祿”切,都是“见”母,属于双声)。这个例子是“二十九种对”所举,实在举得并不好,由于“金谷”原来就可以对“首山”,但我也想不出什么好例子,作者的意思大概是“大地”可以对“波折”,二者虽然不对仗,但是都是双声词,以是可以相对。
叠韵侧对:便是原来不对仗的两个词由于都是“叠韵”,以是可以看为难刁难仗,“谓字义别,声名叠韵对”。比如“平生披黼帐;窈窕步花庭”,“平生”和“窈窕”本来对仗不工,但由于都是叠韵,以是可以相对。
不为古人讳,空海和尚的“二十九种对”博采而未精研,比如意对和偏对相似、互成对和当句对相似、奇对和字对相似,又如侧对、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等也难免不免牵强。虽然如此,仔细研究“二十九种对”仍旧是不失落为一种探索古人对仗法则的主要手段。
常见的对仗方法
在对“二十九种对”归纳总结的根本上,梳理研究古人的对仗办法,再拓展一些对联中常用的对仗技法,即可大概勾勒出适于初学者学习的对仗方法,所谓“与古为新,与时俱进”。
工对
工对哀求选择门类相同或附近的字进行对仗。古代对韵中有大量的工对,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工对是对联创作的根本,在不影响表意的条件下,打磨对仗使其愈发精工是非常主要的事情。当然,在实际创作中,很难每字皆求精工,那么选择几个字着力考虑就会起到画龙点睛的浸染。一样平常情形下,颜色、动物、植物、数字、方位等处的精工对仗是非常抓人眼球的。比如:
西涧草堂(韩梦周)
苦处数茎白发;
生涯一片青山。
石钟山昭忠祠内船厅(曾国藩)
拍岸涌惊涛,辽海月明闻鹤语;
回澜凭砥柱,沧江云卧有龙吟。
通州河楼(程德润)
高处不胜寒,溯沙鸟风帆,七十二沽丁字水;
夕阳无限好,对燕云蓟树,百千万叠米家山。
宽对
不能知足门类相同或附近的对仗,就要归入宽对的行列。宽对之中也有工宽之别,有的宽对仅仅知足“以实对实,以虚对虚”,有些乃至连这个哀求的知足不了。比如古人联语中有“到此且停双不借;几人来作小游仙”之语,便是很宽泛的对仗。
有些对联工宽交杂,既有精妙的工对,也有险些可以看作失落对之处。这种工与宽的交杂利用,每每会将读者的把稳力吸引到“工”的地方而忽略“宽”的地方。比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凤”和“犀”是动物、“双”和“一”是数字,这是极工之处,以是便让认忽略了“翼”和“通”对仗的宽泛。这种对法在数字、方位等处尤为明显,比如:
杭州府贡院(阮元)
下笔千言,正桂子喷鼻香时,槐花黄后;
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
嘉善新安会馆(江峰青)
绿水界城隈,同人卜筑北郊,葺旧日亭台,扫径未妨留薜荔;
黄山正晴雪,有客飞杯东渡,问故乡春信,来时曾否见梅花。
正对、反对、流水对
古人云“正对为劣,反对为优,流水对最难”,这种说法难免不免极度,该当是为了表达一种追求个性、自然的对仗态度。正对便是两句表达相同的意思,或表达内容向同一方向延伸,比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反对是自己和自己抬杠,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表意,比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流水对则是顺承而下,让两句成为一个不可切割的整体,比如“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一样平常情形下,绝大多数对仗是正对,用了“有”“无”、“是”“非”这种反义词的对仗每每是反对,而加入虚字表顺接或转乘的时候就很可能成为流水对了。实在,这三种对法无需分得太细,由于没有一种对法是天然优于其他的,也没有必要特意强调利用某种对法,统统都该当以符合自己的表达须要为条件。
自对
自对应是从律诗中的互成对发展而来,即在一句之中利用同门类的字或词,而高下句之间的对仗则较为宽泛。比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由单句对仗的诗到了多句对仗的对联,互成对的技法也更加丰富,一样平常将一联之内各分句之间的对仗叫作“当句对”。
自对的手腕多样,也是对联对仗的一种非常主要的技法。究其缘故原由,可能是由于对联要突出“对仗美”的特点,但是对仗有时也会造成行文板滞,而且中长联也会淡化高下联之间的对仗美。为了突出对仗美,也为了增加联语的变革,古人联作便非常重视自对。
自对种类很多,难以逐一列举,大略来说,便是一联之间形成句间相对之后,高下联相同位置可以不再对仗,乃至连重字不重字也不用考虑。很多人不理解对仗的技法和规则,大略地以原始朴素的对仗标准判断某副联对仗的工宽乃至是否对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以下举几个当句自对的例子,可以自行归纳自对的方法:
江心寺(王十朋)
青山横郭,白水绕城,孤屿大江双塔院;
初日芙蓉,晚风杨柳,一楼千古两墨客。
寿沈仲复(俞樾)
以玉堂客作金山主人,旌节将移,且为第一泉小住;
歌鹤南飞和大江东去,茱萸未老,好补重九节清游。
岳武穆祠(王澄川)
为臣去世忠,为子去世孝,大丈大当如此矣;
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小朝廷岂求活耶。
挽林则徐(左宗棠)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沉。
借对
借对是利用汉字的音、形、义等特点,假借对仗。最常见的借对是借义对,即某字在词中或句中的意思无法与对句形成对仗,但此字另有他义,借他义形成工致对仗。我们所举的例子中,“马谡”对“羊昙”、“楼边”对“月上”、“行李”对“诛茅”等,都属于借对。再举一个范例的例子:“曲中白雪”对“直上青云”,“曲”借“波折”之义与“直”相对,“中”对“上”则是“上”借了方位之义,“白雪”本是曲名,也是拆成“白”和“雪”与“青”和“云”分别相对。“曲中”对“直上”是非常范例的借对,“白雪”对“青云”也有借对的要素在个中。
借音对和借形对每每捆绑在一起,由于汉字的音与形总是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沧海”与“蓝田”虽然可以成对,但“沧”借音同形似之“苍”字,和“蓝”同属颜色,对仗便更加风雅了。也有原来极其宽泛,但借对之后便工致许多的对仗,比如“次第寻书函;呼儿检赠诗”,“第”借“弟”与“儿”对仗。当然,也有字形不类纯挚借音的对仗,比如“丹陛祥烟灭,皇闱杀气横”,“皇”借“黄”转为颜色与“丹”相对。
借对不是随便借的,不然天下险些无不可成对者。利用借对一定要看重“文趣”,不可过于牵强附会,而借对之后也该当与“原配”形成工对,不然只能弄巧成拙,难以让人感想熏染借对的风雅。
无情对
如果把工对和借对推到极致,就会形成近于笔墨游戏的无情对。无情对哀求高下联每个字都对仗极工致,但高下联的意思全不干系。比如著名的“三星白兰地;五月黄梅天”,每个字都对仗工致,但高下联毫无关系。
听说,无情对源于张之洞的陶然亭雅集,曾以“树已千寻休纵斧”求对无情对。曾有一人对以“萧何三策已安刘”,“萧”借植物义对“树”,“刘”借兵器义对“斧”。此句符合无情对的标准,但高下联都很文雅,未能推倒极致,于是另有人对以“果真一点不相关”。“果”借为“果实”,“纵”借为“纵然”,“干”借为“干戚”,字字精工,一雅一俗,可谓妙绝。
还有一些字字工对而意思干系的对联,比如“孙行者”对“祖冲之”。“祖”“孙”为人伦,“行”“冲”皆表移动,“者”“之”为虚字。这种对法也是将对仗的工致推到极致,虽然不是无情对,但是核心的要素是相同的。
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结语以上是一些常用的对联对仗技巧,各有千秋、各有所短,学联者不妨多方阅读,切不可偏执一端,以至于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此外,对仗还有很多避忌,比如重字、合掌等,这里就不赘述了,所谓“利用之妙,存乎齐心专心”是也。
作者:金锐
金锐,中国西席报文化周刊主编,中国楹联论坛实行站长,京社副社长,《诗刊》2018陈子昂青年诗词奖得主,第四届中国楹联莲华奖金奖。担当数十次海内外诗词、对联赛事评委,诗词对联作品悬挂于鹳雀楼、黄鹤楼等全国数十处景区。曾在东方卫视“绝对中国”节目中降服来自全国各地选手得到“联王”称号,在中心电视台“机警过人”节目中降服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