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候,米芾在江淮发运司做官,总要乘船,由于满船字画,就挂个牌子,说这是米家书画船。后来大家都以为这很浪漫,不断作诗作文表彰此情此景。傅申师长西席把稳到这个征象,曾经写文章谈过江南文人在水上行旅与创作、鉴赏的各类情态,解释它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一个有生命的典故。不过傅文因此董其昌的字画活动为中央,详于艺术而略于文学,详于明而略于宋元及晚世,于是我想连续作些补充。
首先该说,米芾的影响一定很大。江南多水不自宋时始,在他之前,文人们必定已经习气了在船上欣赏与创作,只是未曾想到此事与彼物可以牵连在一起。在他之后,大家以为“字画船”适可而止,于是这个词儿在一百五十年间风靡开来,至南宋已很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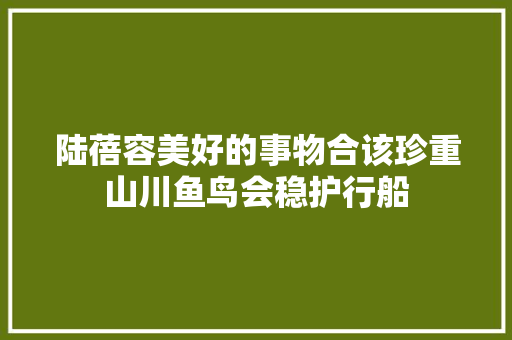
最出名的一例可谓马首是瞻。周密(1232—1298)《齐东野语》“子固类元章”条,记载宗室子弟赵孟坚(1199—1264)的行迹,说他能书善画又雅有收藏,喜好乘着船,带着藏品到处游览。船上堆得了无空隙,只留一席之地,聊供起卧。周围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当代的米家书画船。一次他到访西湖,薄暮停舟,以为面前风光恰如古人名画,就高兴得大喊大叫;又一次遇风翻船,藏品遭厄,他浑身湿透地站在浅水中,抓着五字不损本《兰亭序》不撒手。米芾那种颠劲儿,也真是庶几得之。
周密晚生三十年,已慨叹赵孟坚风骚难再得。实在赵氏前后,仍有一批墨客频频写到字画船,个中两位是江湖派的代表人物。刘克庄(1187—1269)从前闲废,晚登高位。七十九岁退休在家时,曾作《次韵竹溪题达卿后坡》诗,歌咏侄儿刘求志的园林。诗颇不佳,徒然堆砌典故,而“箪瓢斋颇奢颜巷,字画船堪埒米家”一句,却涌现了两处实景:因与“箪瓢斋”相对,此处的“字画船”可能不是泛指,而是后坡中一处真实所在。刘氏家在福建莆田,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却也背山面海,有水乡平原风光。那么大胆假设,在这建筑在“寿溪之上”的园林里,“字画船”,或是一座临水的石舫,倒未必能游到江河湖海间。
与刘氏齐名者,尚有戴复古(1167—1248),年齿较长,生平未仕,是真正随处为家的人。其诗有晚唐风味,闲闲读来,见他自家乡黄岩出门谋食,曾在淮上,又过湘中,小船儿上凌驾路,生过病,看过岸边村落民辛劳谋生。行旅无聊而孤苦,生存困难,又不得不常以诗句干谒公卿。看花饮酒已是难得的美事,字画清福从未听闻。纵然如此,碰着朋友生活不快意,他还是写出浪漫的作品来表达关心。《墨客玉屑》引《复兴词话》,赞颂戴氏填词俊秀,举例云:
姚雪篷名镛,进士出身,曾守赣州,后贬衡阳。戴氏当时身在福建,曾经“度梅岭,涉西江”,亲自到衡山去慰问他。小词虽仅存一句,却也自然姿媚,让人以为美好的事物合该珍惜,山川鱼鸟会稳护行船。
[宋]赵伯驹《莲舟月牙图》(局部)
人生各类境遇说来也很大略,无非是承平岁月求田问舍,板荡之世泛宅浮家。刘、戴两位笔下的字画船,后来都有发展。南宋之末,先有真正在小船上欣赏字画的杭州人仇远(1247—1326)。他在元朝生活的韶光还更久些,曾于大德年间出任教职。从诗集来看,其人既不热衷于高位,也并不厌恨这足以糊口的微官,长于掌握感情,能享受沉着的日常生活,但故国之思无法去怀。
他与艺术很有缘分,鉴赏过许多名画,书法作品也流传至今;喜好这个典故,并不虞外。在任时岁暮搬家,曾有“官闲空绾文章印,水浅难移字画船”之句,全是写实;而末句则说“人生聚散如凫雁,纵目江湖万里天”,搬家之际,想起许多老朋友散在江湖。
与朋侪在家乡西湖上泛舟时所作七律,含义就更明显些:
斜堤高柳绿连天,且系闲人字画船。
花事已空三月后,湖光还似十年前。
洛阳园囿惟诗在,江左英雄托酒传。
亦欲扣舷歌小海,胆怯沙上白鸥眠。
湖光依旧,江山易姓,北宋繁华早已渺远,南渡以来复兴诸将也都空余传说。他也想敲着船舷,唱一首怀念忠烈的古歌,却知道时势所迫,无能为力。诗文字画都是销忧之具,宋亡前一年,他作有《自书诗卷》,录自作七言律诗三十八首,忧生念乱之情就跃然纸上。
后有元明诸贤题跋,生于和平年代的晚辈俞希鲁评语最恰切:
严格说来,元代国祚不长,和平不过短短几十年。却真有一位绅士杨维桢(1296—1370),又建起“字画船亭”。杨氏中年之际,眼看起复无望,遂于至正六年(1346)由杭州搬家苏州,教馆谋生,为期大约三年。这段韶光他彷佛家境宽裕,生活也很愉快:诗简往还,扁舟泛览,友朋音信不绝。张雨、顾瑛、郯韶、郑元祐,这些玉山雅集圈子里的文人都曾题咏杨氏园亭。郑诗有“草玄心苦意如何,舣岸舟轻不动波”之句,说亭畔小舟轻泊,不起波浪。又云“想见后堂凉月白,彭宣肠断雪童谣”,彷佛寓所相称宽裕,不徒一屋而已。文献足征,其地位置还大概可知,约在今公民路与干将路交界处,地铁乐桥站东南一带,至今繁华未歇。
中国古人常常怀想前辈,入明诸贤难忘元末风骚。建文永乐期间有一位学者龚诩,是顾瑛的昆山小老乡,曾专门写诗凭吊玉山草堂故址。那时草堂已不存,空留满地荒烟蔓草,文期酒会都如一梦。他对当日盛况作出想象,说是“花时不绝笙歌宴,门柳常维字画船”。由于雅集中人多能艺事,用典虽是泛指,却也自然恰切,并不使人生嫌。
实在明初政坛气氛很是肃杀,江南更迭经战乱与征敛,读书人没有什么好日子。典故虽传,风气几绝,至少今存文献中很少看到艺术家飘荡在山水间。倒是一位历经五朝的重臣黄淮,在那时写出《字画船记》。黄氏永嘉人,生平数度起落,宣德二年(1427)乞休,乡居二十余年而卒。他是洪武年间的进士,永乐时入阁,半生驰骛,北马乘惯而南船久违。归乡之后重泛云水,两子念其年迈,协力造了一条新船。“板上覆以蔽风雨,牖两傍以便不雅观览,与客同泛,可布十余席。中设小榻,独往可以备燕息。后辟行厨,可以供茗饮。”与古代山水画中常见的文人小舟比起来,这设置相称豪华,险些不相称了,可还是以米家旧称来命名。他谦称自己不是收藏家,不过“儒者出入必以字画具”,情由朴实,船再大也理直气壮。
成化、弘治往后,文献丰富,到了我们更易想象的时期。苏州日渐繁华,吴门画家崛起,徽商关心艺术,杭州成了随处颂扬的旅游胜地。江南各地之间水路交通不断发达,字画船划来荡去,习认为常,以至于字画著录《清河字画舫》,略变其称以为书名。
典故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小船儿游进画中。本日还能间接看到苏州韩世能(1528—1598)的藏品目录,个中有一件元人作《米家书画船图》。不知作者,又无详情,可靠程度不得而知。再晚几十年,米万钟(1570—1628)生。他酷爱奇石,善于书法,也能绘画,在晚明的艺术史上自有一席之地。其人原籍陕西,幼年寄籍京师,是彻底的北方人士,到南方做过高官。
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集》中收有一首七言律诗,《米仲诏书画船卷即席题》。两人既然同时,那诗题就很好理解:某次聚会中,米万钟作《字画船卷》,胡氏当场题咏。全篇意思清楚,两个对句都恰切,既说“中流荷芰藏仙客,极浦蒹葭望美人”,又云“经卷喷鼻香炉晨独倚,笔床茶灶午相亲”,可以确信画上是一艘真正的船。
指明这点很有必要。有些字画文献称米万钟为米芾之裔,他也确实到镇江修过“祖坟”。或者是太敬爱先人,他把字画船的观点发挥到极致——是的,如你所想,其家园林里也有同名建筑。当他丁父忧居京之时,曾在苑西建筑湛园。苑西也便是禁苑之西,今所谓西城根,与景山三海相去不远,位置上佳,风景秀美。据其自记,园中建筑不多,彼此呼应,于花径竹林之间错落:
以“字画船”命名的临水建筑,可能是第一次涌如今北方,因此值得详细征引。此外,还要征引一幅画儿: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米氏《行书七言诗句轴》,引首钤“字画船”印。稍作检索可知,米氏许多作品上都钤有这枚印章。书风、石癖之外,恐怕这也是向五百年前先人致敬的行为之一。
米万钟与董其昌同时。翻过这一页,晚明的故事大体结束。字画船游到清初,涵义或许有奇妙的变革。创作、鉴赏并行的情形稍觉少见,它彷佛与文人收藏活动越来越干系。康熙年间,《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1648—1718)颇负盛名。他有一种收藏目录《享金簿》,传闻清钞本完全无缺,尚在广东,可惜未曾旁观。但孔氏把稳字画的事实却在文集中表露无遗。《湖海集》收入书函数卷,有不少书信寄给了善于画画的朋友们。
他向龚贤求画,说“求教诸件,皆望随意挥洒,大小纵横无之不可,譬之造物者因物赋形,而飞潜动植总无有不是处耳”,非常客气,也尊重画家意愿。得到作品之后,更有一种志得意满之态,赞颂绘画是医俗的良方:
本来没有字画的船,可以被人瞩目,一跃成为字画船,这当然是一种讨巧的修辞。至于本来就装满字画的船,就更名副实在。有一次,高士奇(1645—1704)带着一堆家藏珍密从浙江平湖出发,坐船进京再去做官,在苏州停泊,即是所谓“今年奉召北赴阙,字画船泊胥江滨”。这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事,当日宋荦(1634—1713)摆了酒宴请他,遂得登船欣赏各种名迹。
那时高士奇才知道,宋家还没有一卷董其昌。这位坐着字画船南北巡游的艺术家留下不少作品,我历数过清初诸家著录中的晚明名迹,董其昌一个人可以占到半壁江山。那一天,高氏把自己收藏的董氏《江山秋霁》长卷送给宋荦,这幅画号称仿黄公望,而构造、笔墨都很紧实,自家面貌明显。
总体来说,康熙朝是士人从事收藏活动的好时期。自那往后,藏品向宫廷流动,士林风气日渐变革,雅俗的界线不复如此分明。晚明江南藏家曾管带着字画游走贩卖的商船也叫字画船,清中期往后,这类材料复又现身,但读来已似平凡记述,氤氲水气飘散无踪。
有两位常熟士人可以为证。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张大镛(1770—1838)记一件恽寿平的《天池石壁》,说,戊子年(1828)有人把它装在字画船上拿来求售,于是自己花了“青蚨四万”买下。这是一个非常诚恳的记载,全然侧重于价钱。半世纪后,光绪三年(1877)十月,翁同龢(1830—1904)得假还乡,转往上海。某日买书之后,到“二马路字画船常卖家”去看画儿,花四十四元买了“石谷小帧、麓台矮幅”,彷佛意犹未尽。越日重访字画船,又花了二十二元买得一件吴历,自称“极费力矣”。
我先狐疑这开在“二马路”上的字画船,难不成只是店名?后来查到这便是本日的九江路,路尽头正对滚滚黄浦江。
(本文摘自《字画船边》,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字画船》)
【毛边本+笺纸】《字画船边》(赠作者陆蓓容题写笺纸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