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弗成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弗成焉,可谓远也已矣。”
【注释】
▲明:明智,明辨是非。
▲谮[zèn]:谗言,挑拨离间的话。浸润之谮,逐步浸润过来使人不易察觉的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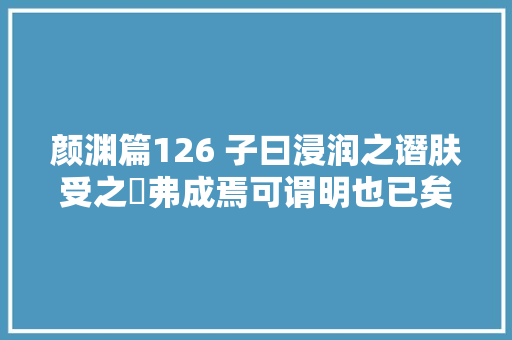
▲愬[sù]:同“诉”,控诉、埋怨;诋毁、诬告。肤受之愬,让人有如切肤之痛的诋毁。
▲远:有远见。“远”是“明”的更高境界。朱熹《论语集注》:“远则明之至也。”
【译文】
子张问若何才能明辨是非。孔子说:“让人难以察觉的谗言,有如切肤之痛的诋毁,对你不起浸染,可以称作明辨是非了。让人难以察觉的谗言,有如切肤之痛的诋毁,对你不起浸染,可以称为有远见了。”
【学而思】
参读《颜渊篇》12.10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去世。既欲其生,又欲其去世,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知识扩展】
《荀子·致仕篇》:“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夫是之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译文】广泛地听取见地、创造隐居的贤士、显扬贤明的人、使奸邪退却、选拔引用贤良之士的方法:对结党营私、相互勾结之人的吹捧,君子不屈服;对残害贤良、横加罪名的诬陷,君子不采取;对猜忌、埋没贤才的人,君子不亲近;用钱财礼物进行贿赂的要求,君子禁绝许。凡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没有根据的辞吐、事情、计谋、赞誉,诉说等等,不是通过正当路子而是从四处传来的,君子对它们持慎重态度,听到了要明确分辨,确定它们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然后对它们作出惩罚或奖赏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履行。像这样,那么奸邪的辞吐、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情、奸邪的计谋、奸邪的赞誉、奸邪的诉说就没有敢来试探的了,忠实的辞吐、忠实的学说、忠实的事情、忠实的计谋、忠实的赞誉、忠实的诉说就都公开表达、通畅无阻,并起而供献于君主了。以上这些便是广泛地听取见地、创造隐居的贤士、显扬贤明的人、使奸邪退却、选拔引用贤良之士的方法。
《资治通鉴·随纪三·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弟子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辩。”问止怨,曰:“不争。”通尝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削。”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囮[é]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囮去媒,谗佞远矣。”大业末,卒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
【译文】王通的弟子贾琼问王通如何平息诋毁,王通说:“不去争辩。”贾琼问如何制止怨恨,王通说:“不去辩论。”王通曾声称:“没有罪过可赦免的国家,其刑法必定公允;苛捐杂税的国家,其财力必定削弱。”又说:“听到诋毁就发怒的人随意马虎中了进谗言者的圈套,听到夸奖就高兴的人随意马虎为阿谀奉承的人所利用。如果去掉这些毛病,谗言奸佞就会阔别而去。”大业末年,王通在家去世,他的弟子追赠他为“文中子。”
注:王通,字仲淹,唐朝墨客王勃的祖父。王通在黄河、汾水之间设馆传授教化,远比来此求学者达一千余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程之、薛收、温大雅等都是他的徒弟,而这些人都是唐初的元勋,时称“河汾门下”。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资治通鉴·唐纪八·唐太宗贞不雅观二年(公元628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作甚而明,作甚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huān dōu]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甚至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
【译文】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见地,便是明,偏听偏信,便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讯问民间疾苦,以是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以是共工、鲧、驩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害;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以是君主长于听取各方面见地,则亲贵大臣就无法壅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其略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虽制敕交行,而声实舛谬[chuǎn miù],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而弃之。”又曰:“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
”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以是分也。明主则不然。受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
”又曰:“夫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陛下方兴崇至德,大布新政,请统统撤除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上览而善之。
【译文】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议论时政,疏文的大意是:“隋炀帝自恃聪慧过人,不肯为时政多费脑筋,虽然他颁发的制敕数不胜数,但言行之间却相差甚远,口说尧、舜之言,身行桀、纣之事,末了终于丧失落了全体天下。”他还说:“隋朝天子放肆自己的希望以至于亡国灭家,本朝太宗天子抑制自己的希望以至于国家繁荣昌盛,希望陛下能够从中慎重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他还说:“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不是喜好忠实正派之士,讨厌奸佞邪恶之徒的,但是事实上却是忠实正派之士常常被疏远,奸佞邪恶之徒常常被宠幸,以至于到了国亡身危的地步还不知缘故原由所在,这是为什么呢?真正的缘故原由在于忠实正派之士大多不惜触犯帝王的旨意,而奸佞邪恶之徒却大多屈服帝王的邪念,长期触犯帝王旨意就会使帝王产生讨厌之心,长期屈服帝王邪念也会使帝王产生爱怜之意,这便是亲疏以是产生的缘故。圣明的帝王与此相反,他们喜好敢于触犯自己旨意的臣子,为的是得到忠正贤良之士;讨厌一味屈服自己的人,为的是撤除身边的奸佞邪恶之徒,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造诣太宗天子的太平功业,又有什么困难呢!
”他又说:“法律条文贵在简明扼要而能禁止奸邪,刑罚贵在轻缓而且行之有效。目前正是陛下彰明德教、除旧布新的时候,希望能将所有细文苛法尽行拔除,不要在臣下的眇小过失落上琐屑较量。对臣下的眇小过失落不去计较就能屏除啰嗦苛刻的法律,对重大的罪过不使漏网就能制止邪恶,陛下如果能够使法律简明而难以违反,刑罚宽缓而能够制止犯罪,那么就可以称得上是善政了。”唐玄宗读完他的奏疏之后,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议很好。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贞不雅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落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旁边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相互弹劾,率以险诐[bì]相倾覆。及宋璟为相,欲复贞不雅观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译文】贞不雅观期间曾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须有谏官、史官随同,如有过失落则及时匡正,无论善恶均记录在册;诸司奏事均在正衙,御史弹劾百官时,必须头戴獬豸冠,对着天子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奏表;以是大臣无法蒙蔽君主,小臣也无从进谗行恶。到了许敬宗、李义府执政期间,朝政多出自私门,官员奏事大多是等仪仗撤下后,屏退旁边,在天子御坐之前秘密进行的,监察御史和待制官只是远远侍立以期待奏事的大臣退下;谏官和史官也是随天子仪仗一同退出的,至于仪仗撤下往后发生的事,则无从得知。武则天以严法掌握臣下,谏官和御史可以仅凭传闻弹劾大臣,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之间也可以相互弹劾,致使者下大多以邪谄不正的手段相互陷害。宋璟做宰相往后,想规复贞不雅观期间的制度。戊申(十二日),唐玄宗发布制命:“从今往后,凡事如果不是必须保密的,一律对仗奏闻,史官也要按贞不雅观时的旧例加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