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波澜壮阔的生平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而他所表现出的伟大人格与社会良心,直至本日仍熠熠生辉。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性情光鲜,形象饱满,可亲可敬,堪称人间间的空想人格,他留给众人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
1101年夏,苏东坡走到他人生的尽头。
维琳方丈靠他耳边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大概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好友钱世雄对他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这时苏东坡留下他人生的末了一句话给这个天下:“勉强想就错了。”
苏东坡的人生中见佛性,有道风,但从他末了的话中我们能够知道,他彷佛又没有一种彻底的崇奉。我的理解,崇奉在于让人的生命得到解脱,而苏东坡,他的人生一如浮舟,偶有所系,终属于汪洋;一如清风,或有羁绊,终归于天地;一如明月,时为云遮,终系于星空。已经如此洒脱,亲近宗教,却不拘泥于崇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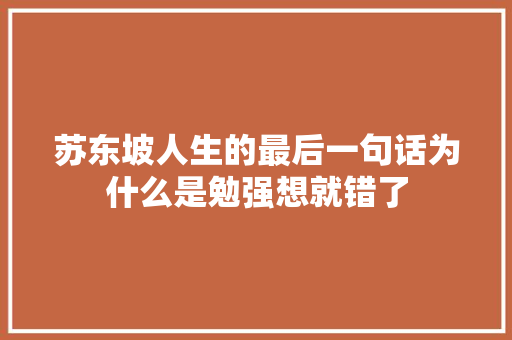
“勉强想就错了。”人生中处处勉强又有什么意思?唯此,才能够在顺境中斗志昂扬,在困境中随遇而安。生活中不是短缺情趣,而是短缺有趣的心灵。
林语堂写苏东坡,便是两个有趣灵魂的相遇。
林语堂
他写是由于他热爱苏东坡。在他的《国学拾遗》中,他这样评价:“庄子是中国最主要的作家;经由一千四百多年之后,才有一位可以和他比较的天才,苏东坡。”
1936年林语堂百口赴美,他身边撤除多少精选的排印周详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我旅居外洋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他写也是由于自己喜好,“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由,只因此此为乐而已。”于是,1936年赴美后,他就开始构思为苏东坡做传,书名为“TheGay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可直译为“快乐的天才——苏东坡的生活和时期”,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苏东坡传》。
林语堂被称为诙谐大师,但他却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Humour音译为中文的诙谐,从而使诙谐一词在中国迅速盛行开来。林语堂在自己的《八十自叙》中说:“并不是由于我是最高级的诙谐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诙谐则极为缺少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呼唤大家把稳诙谐的主要的人罢了。”他对苏东坡的评价之一,便是“假道学的反对派”。“诙谐是一种人生的不雅观点,一种搪塞人生的方法。诙谐没有旁的,只是聪慧之刀的一晃。”他确实从苏东坡的人生中创造了生命的诙谐和快乐。
林语堂在媒介中这样描述苏东坡——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庶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天子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溜达者,是墨客,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大概还不敷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大概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统统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小儿百姓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聪慧,兼有鸽子的温顺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墨客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百里挑一,不可多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苏东坡的人生舆图
苏东坡热爱生活,譬如在黄州时,他开垦东坡,种稻,植桑,脸晒得黢黑,和渔樵为伍,改编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在田间敲着牛角和农夫歌唱,偶尔喝醉,在无数个夜晚有山中明月、江上清风作伴,吟咏于天地之间。或许这个伟大的心灵本就属于野外自然。离开黄州后,拜会住在金陵的王安石。王安石劝他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可以终老。湖州太守殷勤备至,帮他在太湖左岸的宜兴物色到一块良田,他一见爱慕,在一则条记中写道:“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者,殆是前缘。”阳羡便是本日的宜兴。
苏东坡《归去来兮辞》
后来苏东坡又被贬海南岛。归时他依然选择回到宜兴。他的朋友邵民瞻替他物色了一栋屋子,花了五百缗钱,听说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搬入新居后的一个夜晚,东坡和邵民瞻在月光下闲步,途经一个村落庄,听到一位老妇人哭得很悲哀。他就推门进去,问老太太为什么这么哀伤?老太太说:“我家有一栋屋子,已相传百年,一贯保存到现在。但是我的儿子不孝顺,把这所宅子卖给了别人。我本日搬到这里,上百年的老屋子,一下子失落去,怎么能不心痛呢?”
东坡也为她感到难过,问她的老屋子在哪里,原来竟是东坡用五百缗买到的那一栋屋子!
于是东坡再三安慰老太太,并且逐步对她说:“您的屋子是被我买了,您不必太难过,我该当将这屋子还给您。”
于是他拿来屋契,在老太太面前烧掉,还叫她儿子第二天带母亲回老屋去,彷佛他也没讨回买房的五百缗钱。百口则回到毗陵,借顾塘桥孙氏的屋子暂住。
“东坡卜居”之事,很令人惊叹,使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心境,也不知该如何置评。他人生中的这件事,很像是他生平任性的一个注脚。任性而为,便是“不勉强”,自己不勉强,也不要去勉强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性而为,就不会想得失落了。一个人若患得患失落,又何来活气盎然的生活?
苏东坡仕途浮沉不定,生活却活气盎然,缘故原由不外有三:一是他生命中丰裕的浩然之气,这让他有一处心灵的安顿之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二是诗名动天下,身在庙堂心处江湖,人生如浮萍,随波逐流,到哪里都有朋友,他不寂寞;其三便是他的“不勉强”。就像他在《定风波》中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缓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贯在追随不雅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有时成形,昙花一现而已。
苏东坡已去世,他的名字只是一个影象,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