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为“犯人”,初期住在官舍,后被逐出。在城南“污池之侧桄榔树下”筑了几间泥房住。到了这等田地,东坡洒脱依旧,很快和当地土著打成一片。
有一天他在黎族兄弟家里饮酒,醉后迷了路,问“我家在哪里?”事实上,问也白问,由于人已经醉了,自己走回去吧,却又迷了路。终于复苏些了,想起来以牛栏为定位,以牛屎为线索,踉踉跄跄回了家。事后作诗一首:
半醉半醒问诸黎,竹刺藤稍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纪晓岚评价这首诗,认为“牛矢(屎)”也太俗了。王文诰回嘴说,这是偏见。《左传》写过“马矢”,《史记》写廉颇“一饭三遗矢”,都是据事直书,未尝以“矢”字为秽。
后来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里说:“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东花满蹊’诗,念古人胸次洒脱旷远,毫无残存,何其大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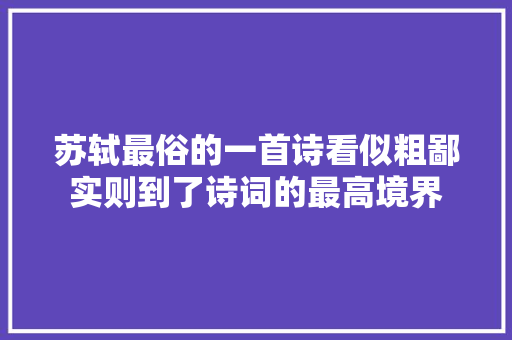
为什么曾国藩叹他们境界大呢?
苏轼、陆游、杜甫的这三句诗,都是极俗的。苏轼诗中写牛屎,陆、杜则以“赵家庄”、“黄四娘”等世俗的地名人名入诗,然而细细品读,一股醇和悠远的乡野之气迎面而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墨客对草根文化充满原谅与热爱......都能在反复的吟读中逐渐地荡漾开来。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落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落舍舟步归》陆游
黄四外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清闲娇莺正好啼。——《江畔独步寻花》杜甫
曾国藩从中读出的“胸次洒脱旷远,毫无残存”,指的是墨客在写下这些诗句时心灵的纯净与通透,他们纯粹是为眼中的美好景象所冲动,便虔诚地将其记录了下来。
没有过多地去思考这些粗秽之物,俚俗之名会对自己的诗、自己的个人形象造成什么负面影响,结果无意中以大俗之物抵达了大雅的境界。
古人云,“诗言志”,“文如其人”,但有的人每每由于知道这样,以是在写诗作文前就已经失落却了平常心,被该若何在诗中塑造自己的形象扰乱了心志,把对自身的考虑放在了比诗更加主要的地步。
于是心中就有了残存,诗文的格局、气韵和境界就不免逼仄、滞碍与局促起来。只有抛却了这统统,只想着诗歌,而不去多想自己,纯粹的诗歌才会如清泉般汩汩涌出,且连绵不绝。
统统都是由于怀着小儿百姓之心,统统都是由于了无机心,以是便得了艺术的真髓,以是便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佳作妙句变得俯拾皆是,不求自来。哪怕明明看似是冲着大俗去的,哪怕明明是满口的俗话,却由于内心的澄澈空明,反倒轻而易举就超越了表面的俗,而踏入了别人苦求不得的大雅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