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唐代著名诗僧。唐肃宗至德年间(约公元756年),皎然结识来湖州避安史之乱的陆羽,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四十多年的淄素之交。皎然交游甚广,与陆羽、颜真卿、韦应物、卢幼平、于頔等文人墨客交往唱和,留下了随处颂扬的诗文轶事。
在皎然存世的470首诗作中,关于茶人茶事的约有28首,是唐代茶诗数量第三多的墨客,仅次于64首的白居易和38首的贯休。他的茶诗,大部分因此茶会友、往来酬唱,有的是采茶制茶、品茗悟禅,有的是借茶抒怀、以诗明志、弘扬茶道。皎然的茶诗首次提出了茶道之说,对后世的茶文化具有主要影响。
一、淄素之交——茶圣陆羽的终生密友
皎然有12首诗记载了与陆羽交往酬唱的过程。有趣的是,他在不同期间,写了三首寻访陆羽不遇的诗,这些诗的共同点,便是场景感强,把想见不得见的惆怅与失落落表达得生动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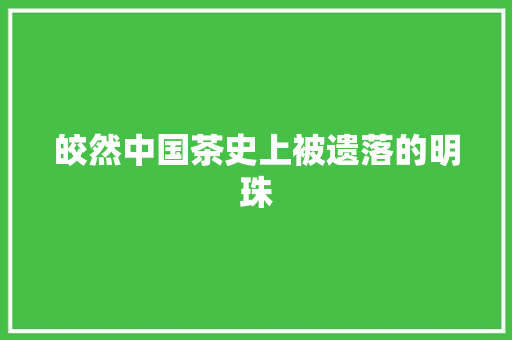
寻陆鸿渐不遇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宣布山中去,归时逐日斜。
这首诗约作于唐肃宗上元初(约760年)秋日,陆羽到湖州后,先借住妙喜寺僧舍,后结庐于苕溪之滨,门前种桑麻,编竹篱,篱下种菊,尚未着花。皎然前往探访,扣门不应,讯问邻居得知,陆羽进山采茶,每天太阳落山时才回家。一幅隐士进山采茶、安居乡间的景象。次年(761年)陆羽《茶经》初稿脱稿,可见此处正是陆羽撰写《茶经》之所。
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
远客殊未归,我来几惆怅。
叩关一日不见人,绕屋寒花笑相向。
寒花寂寂遍荒阡,柳色萧萧愁暮蝉。
行人无数不相识,独立云阳古驿边。
凤翅山中思本寺,鱼竿村落口望归船。
归船不见见寒烟,离心远水共悠然。
异日相期那可定,闲僧著处即经年。
皎然的第二次寻访不遇,是在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陆羽时年30岁),陆羽避袁晁兵乱,移居丹阳茅山。皎然在陆羽暂住的村落口苦苦等待返航的归船,久别盼相逢,在驿舍门外徘徊不舍拜别,可以看出皎然与陆羽之间的分外情意。
陆羽与皎然品茗论道
访陆处士羽
太湖东西路,吴主古山前。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
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
这是皎然第三次寻访不遇,皎然徘徊在驿舍前,当看到天上飞鸿,更加期盼陆羽归来。猜想陆羽外出,究竟是品春茶,还是汲春泉,或是独钓湖上?
皎然写与陆羽交往最早的一首诗作于759年,他把陆羽和韦卓比作陶渊明和谢灵运,乃至由于认识了他们,贯串衔接识他人的兴趣都没有了。可见皎然初识陆羽时的一见如故。
赠韦卓陆羽
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
不欲多相识,逢人
从各个期间皎然的诗作中,可以看到皎然对陆羽的至心欣赏和朴拙友情,两人修茶禅于一体,友情延续了四十多年,去世后先后归葬于湖州杼山妙喜寺。寺旁有皎然塔和陆羽墓,唐朝德清籍墨客孟郊在《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一诗中有“杼山砖塔禅,竟陵广宵翁”。妙喜寺既是他们初识、开始交往的地方,也是归葬安息之所,不愧是淄素忘年之交。
二、劝茶抑酒——品茗之风的早期传播者
皎然的茶诗中,有三首为劝茶抑酒之作。第一首《九日与陆处士饮茶》,记述的是重阳节之际,两位老友独坐僧院,欣赏篱下黄菊,饮菊花茶,谈茶参佛。
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喷鼻香。
皎然通过此诗,对世俗饮酒之风进行规劝,提到用菊花泡茶之独特芳香。此诗也是菊花茶悠久历史的有力证据,早在唐朝时已有重阳节饮菊花茶习俗,恰好契合桐乡等浙北地区有栽种杭白菊的传统。
送李丞使宣州
结驷何翩翩,落叶暗寒渚。
梦里春谷泉,愁中洞庭雨。
聊持剡山茗,以代宜城醑。
古时僧人在迎送酬唱中以茶代酒,既方便了社交,又守持了佛教戒律。《送李丞使宣州》中的宜城醑是当时名酒,剡山茗便是越州茶,系唐时名茶,陆羽《茶经》有“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之说。皎然在其他诗词中也有多次提及剡茗、剡溪茗,如《送许丞还洛阳》有“剡茗情来亦好斟,空门一别肯沾襟”。如《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有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便是一首劝茶歌,也是皎然的代表作。他在与湖州刺史崔石的交往中,感慨“此物清高世莫知,众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他引用东晋官员毕卓酗酒夜宿酒窖误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饮酒诗两个典故,以及崔石酒后高歌惊扰他人,调侃饮酒的危害性,夸奖饮茶有修身养性、得道羽化之功效。
陆羽烹茗图
唐朝正处于民族大领悟之际,饮酒之风盛行。品茗饮茶的风气,自然与饮酒相抵触,彼时常常发生品茶与饮酒的辩论。《茶酒论》是一篇创造于敦煌的唐朝变文,用拟人手腕展开了一场茶酒争功的大辩论。茶者以“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名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自诩,酒者以“自古至今,茶贱酒贵单醪投河,三军告醉。君王饮之,叫呼万岁。群臣饮之,赐卿无畏。和去世定生,神明歆气。酒食向人,终无恶意。有酒有令,仁义礼智”还击。四个半回合的你来我往,不分胜负。末了,水出来裁决,“茶不得水,作何容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米曲干吃,损人肠胃。茶片干吃,只砺破喉咙。万物须水,五谷之宗”,希望:茶与酒“从今往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可见,唐朝时,品茶之风兴起,与饮酒之习形成相互补充。
三、亦茶亦禅——以茶修身的实践者
皎然茶诗中有三首记述了采茶、制茶、煮茶的方法。皎然作为杼山妙喜寺方丈,寺产有茶山,采茶制茶都是寺院必备之事。特殊是与陆羽保持了四十多年的交往,谈茶论茗都是家常便饭。因此,皎然谙熟茶事,十分正常。
茶圣陆羽
顾渚行寄裴方舟
我有云泉邻渚山,山中茶事颇干系。
鶗鴂鸣时芳草去世,山家渐欲收茶子。
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
由来惯采无近远,阴岭长兮阳崖浅。
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
吴婉携笼上翠微,蒙蒙喷鼻香刺罥春衣。
迷山乍被落花乱,度水时惊啼鸟飞。
家园不远乘露摘,归时露彩犹滴沥。
初看怕出欺玉英,更取煎来胜金液。
昨夜西峰雨色过,朝寻新茗复如何。
女宫露涩青芽老,尧市人稀紫笋多。
紫笋青芽谁得识,日暮采之长太息。
清泠真人待子元,贮此芳香思何极。
这是皎然茶诗中记录茶事最详尽的一首诗,对采茶籽(鶗鴂鸣时芳草去世)、采茶叶(伯劳飞日芳草滋)、采茶机遇(家园不远乘露摘,归时露彩犹滴沥)、煮茶(更取煎来胜金液)等茶事技艺,做了详细描述。
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
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
文火喷鼻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
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
皎然在这首诗中交代了采茶韶光(露采北山芽)、煮茶(文火喷鼻香偏胜)、水品(寒泉味转嘉)、泡茶(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等采茶、制茶、品茶等技艺。
在皎然的茶诗中,除了描述采茶、制茶等茶艺之外,还有一些诗作着重表现品茗饮茶的高野孤寂、清净修省、高山流水、琴瑟和鸣的精神境界。如《陪卢判官水堂夜宴》中的“爱君高野意,烹茗钓沦涟”,展示了一个钓翁烹茗垂钓、独钓荡漾等形象,颇有姜太公钓鱼之境界。从《湖南草堂读书招李少府》中的“药院常无客,茶樽独对余”,可以看到一位客居寺院的隐者,在斜阳里独对茶樽的孤寂画面。《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的“识妙聆细泉,悟深涤清茗”,展示了在潺潺流水旁,禅师聆听叮咚之妙,在清茶一杯中体悟人生哲理的画面。《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各垂赠二十韵 今以一章用酬两作》的“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发论教可垂,正文言不朽”,则是在明月之夜,三两好友相聚禅房,窗外月光如水,品茗饮茶,爱慕互换禅修之得。通过《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 汤衡 海上人饮茶赋》中的“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可以看到在月末之夜,一群志趣相投的文人,传花饮茶,吟诗作赋,素绢题诗,相互唱和,通宵达旦的场景。
饮茶歌送郑容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
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
霜皇帝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
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
日上喷鼻香炉情未毕,醉踏虎溪云,高歌送君出。
陆羽品茗图
皎然在这首茶诗中,把茶饮视作修炼得道的必备阶段,饮茶既可以去除疾病(祛我疾),还可以肃清忧闷(荡忧栗),乃至可以羽化登仙(生羽翼)。把饮茶之人比作丹丘神仙,可以永生不老。可见,皎然对茶之喜好,对饮茶之风的全力推动。
四、茶道之源——茶道理论的创始者
陆羽的代表作《茶经》,皎然的代表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的代表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这三篇诗文是茶史上的经典诗文。皎然在茶史上的贡献,一方面记录了与茶圣陆羽的交往过程,成为主要的茶史资料;另一方面率先提出了茶道观点,并对茶道的境界做了三个层次归纳。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喷鼻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众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的这首诗先提出了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等茶饮的三重境界,还首次提出了茶道观点(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此诗约作于785年,比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提出“七碗茶”的七重境界早了28年。
卢仝也是茶史上的精彩人物,被后人尊为茶仙,生于769年,比皎然小约49岁。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的“七碗”,与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的“三饮”具有显著的传承和发展。“三饮”与“七碗”,都是从饮茶的感官功效,递进到精神升华。皎然的“一饮涤昏寐”,可以对应卢仝的“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皎然的“再饮清我神”,可以对应卢仝的“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五碗肌骨清”。皎然的“三饮便得道”,对应卢仝的“六碗通仙灵”、“七碗清风生”。皎然的“一饮”、“再饮”,与卢仝的“一至五碗”,属于品茗饮茶在感官层面的体验;皎然的“三饮”与卢仝的“六至七碗”,属于精神层面的得道、通灵等体验。在饮茶体验的表述上,两者也非常相似,皎然用了“情来朗爽满天地”、“忽如飞雨洒轻尘”的比拟手腕,卢仝则用了“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等表述,形象普通。
宋-刘松年《卢仝烹茶图卷》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唐·卢仝)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东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交且不奢。
至尊之馀合王公,何事便到隐士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笔墨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
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劳!
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卢仝以这首俗称《七碗茶歌》,赢得了茶仙之美誉。在日本,卢仝被尊为“煎茶道”师祖。日本江户期间“煎茶道”的创始人高游自称是“卢仝正流达摩宗第四十五代传人”,在他的《梅山种茶谱略》一书中写道:“茶种于神农,至唐陆羽著经,卢仝作歌,遍布海内外,而后风骚之士吟诗作赋之时无不品茶。”因此,卢仝也被称为茶道之祖。
实际上,皎然才是茶道的创始者,对茶道的形成做出了首创性贡献。卢仝所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七碗茶”七重境界,是对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三饮”境界的发展、深化和继续,是中国茶道文化的主要内涵。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很多茶事茶史来不及记录,就在兵燹战火和朝代变迁中泯没了。我们通过茶史探寻可以创造,皎然作为茶道创始者,对茶道观点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首创性浸染。恰如他的出家人身份,皎然高野孤寂,与世无争。可以说,皎然是茶史上一颗遗落的明珠,我们应铭记皎然大师的历史贡献。谨以一首小诗,致敬皎然大师:
皎然颂
众人皆知陆鸿渐,茶经茶圣叹六羡。
卢仝两腋生清风,七碗茶仙何翩翩。
唯独寂寞释皎然,淄素交羽四十载。
苕溪唱和啜三饮,后世莫忘茶道源。
(原载于《桐乡作家》2022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