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也叫移觉,是在描述客不雅观事物时,用形象的措辞使觉得转移,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平分歧觉得相互沟通、交错,彼此挪移转换,不分界线。譬如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的博识莫测的武功:乾坤大挪移。
在通感中,颜色彷佛会有温度,声音彷佛会有形象,冷暖彷佛会有重量。通感便是让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平分歧觉得间进行沟通,达到意想不到、超乎平凡的功效。
说一个最普通的例子,老人们常说:你耳朵瘸了吗?!
我想大家对这句话都不陌生,这里就利用了通感的修辞手腕,耳朵,本是听觉器官,而瘸,是肢体觉得,这种不直说“聋“而说”瘸“的手腕,便是奥妙的通感。
通感在古诗中的表现手腕是多样化的,有以形声的觉得转换,如汤显祖《牡丹亭》中的两句唱词:“声声燕语明如剪,呖呖莺歌溜的圆。”个中燕语、莺歌都诉诸听觉,而“剪”是器物,“圆”用于形状,都属于视觉范围,怎么”燕语“会象”剪“,”莺歌“会成”圆“呢?原来人们可以从”剪“的形状得出锐利、轻快的遐想,从”圆“的形态上得到珠圆玉润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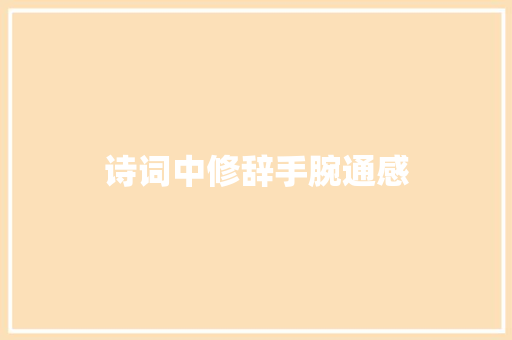
当然还有视觉与听觉相互转换的。”鸟抛软语丸丸落“该句将听觉转化为视觉的感想熏染,将鸟儿活泼、动听而流畅的叫声,通过珠丸的抛落尽显出来。读后,那珠丸抛落时清脆的声音,尤然在耳,而珠丸落的那种视觉形态与节奏感,也跃然面前,叩动心弦。
王维的《过喷鼻香积寺》,个中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一联,泉声,源于耳;咽,则来源于其他感官。日色,为视觉;冷,则属于触觉。墨客把视觉、听觉与触觉等相互沟通,属于通感。杜牧《秋夕》里”银烛秋光冷画屏“一句,秋光,是视觉,冷,是触觉,这里把视觉与触觉相通,属于通感。
通感,是古诗词中比较觉见的一种修辞手腕。作为诗词爱好者,不可不知。关于通感的例子很多很多,不再逐一 举例,以上这些,是对通感的一些初步认识,希望对初学者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