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是《佳人》全诗的情绪基调,只是有写实与寄托的不同理解。杜甫《佳人》作于乾元二年,诗云:“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屠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唐诗解》云:“此诗叙事真切,疑当时实有是人。然其自况之意,盖亦不浅。”虽寄托与实写之说各有其情由,然杜甫笔下“佳人”确为被“夫婿轻薄”、只能“零落依草木”之悲惨形象,此是历代评论家的共识。《唐诗品汇》云“似悲似诉”,《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吴山民语曰:“‘世情’二语,人情万端,可叹,‘夫婿’以下六语,写情至此,直可痛哭。”《唐诗快》说:“题只‘佳人’二字耳,初未尝云‘叹佳人’‘惜佳人’也。”首句下题“只此二语,令人凄然欲泪”。直到近代刘师培亦有:“杜甫诗中,有《绝代有佳人》一首,尤为悲惨……读此诗者,虽千载以下,尚为之有余悲,况于身受者乎?盖处伦理专制之世,女子所受之惨,固有不可胜言者。是诗所言,特其一端耳。此婚姻以是当自由也。”此虽是顺时期潮流为女性发声之言,但“悲惨”二字洵为杜诗之情绪出发点,后人对杜甫《佳人》诗意的文学审美接管与批评,不出其情可悲之意。
而图像阐释则倾向高洁情怀。宋人《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中的修竹、佳人确为杜诗中的核心意象,但二者相伴,兼之描摹的笔法神态等,无一不表达出一种趋于清雅的文人审美取向,与杜诗整体“悲”的情绪基调并不符合。换句话说,若上述二图之一未点出“天寒翠袖”之句,二者构图亦不相似,恐后人不会将其与杜甫《佳人》相联系。以《佳人》为原点,绘画对诗歌表意系统的阐释并未呈现线性的前后相继关系,而是另辟一层想象空间,构建出文人画细腻文雅的审美品位。宋张元幹跋《倚竹图》云:“《楚辞》凡称美人,与古乐府所谓《妾薄命》,盖皆君子伤时不遇,以自况也。好事者用少陵‘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使入图画。工则工矣,视‘小姑嫁彭郎’,抑何以异?”张元幹所见《倚竹图》是否为存世的两幅宋人佚名作品尚未可知,然其将杜甫“佳人”与《楚辞》、汉乐府中美人相类,是基于《楚辞》以来喷鼻香草美人喻君子不遇的传统,这也与杜墨客物出生之悲惨契合。但张见画之感想熏染与“小姑嫁彭郎”相同,不仅点明画意与杜诗诗意的相异,更进一步提示我们画中人物所指向的情绪维度,悲戚不敷,欣悦有余。这倒是与上文提及两幅佚名画作中人物优雅的神态符合,毕竟是待嫁之女。张元幹所见《倚竹图》很有可能便是《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对画作持否定态度的不止张元幹一人,宋袁文《瓮牖闲评》曾批评画家不懂诗:“古诗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来。’所谓佳人,乃贤人也,今画工竟作一妇人。彼纵不知诗,宁无一人以晓之耶!
”后《唐诗品汇》亦有云:“自言自誓,自持年夜方,修洁端丽,画所不能如,论所不能及。”在诗评家眼中,画家并不能领会杜诗深意,即便归天于手,诗中人物风神与气质也绝不是画作所能表达的。
《佳人》诗叙事身分较多,空间性较强的画面很难表现韶光维度下的事宜发展,无法表现诗意的丰富性和繁芜性,所谓“画不尽诗”。第一句“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与“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嫣然有韵,最堪入画。从张元幹、袁文评论可知,最晚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已有杜甫《佳人》诗意图。而另一则记载也是旁证:“宋时考画工,以‘万绿丛中一点红’为题。诸工摹景殆遍,一人独写‘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遂取状元。诗中画,画中诗,须得此意。”宋徽宗赵佶重视画院,模拟进士科出题取士,好以诗句为题,如“踏花归来马蹄喷鼻香”“深山藏古寺”等。《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很可能是个中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宋画院佳作。两幅图所本“万绿丛中一点红”诗句,当为概括王安石《咏石榴花》“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诗句。画师不近取介甫诗句,反远溯杜甫,本身便是故意味的表达。“万绿丛”即“修竹”,“一点红”指什么?有人牵强指为女子的红唇,显然与万绿丛的大背景不合。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央位置两位骑马女子,一位绿襦红裙,一位红襦绿裙。此画为宋人所摹,可知其效仿推崇之意。绿襦即“翠袖”,红裙才是“一点红”。由此可见《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构思之精妙,无愧“状元”之誉。
从宋代这两幅杜甫《佳人》诗意图始,历代不乏以此为母本的绘画作品,个中还有绘画大家的摹写。元赵孟頫有《天寒翠袖图》,姚鼐有诗《赵承旨天寒翠袖图》,明仇英《修竹仕女图》与《竹林仕女图》画面类似,添婢女在侧,以合“侍婢卖珠还”意。由宋画院状元之作,到元大家赵孟頫,再到明仇英,“天寒翠袖”诗意图备受字画名家青睐。及至清代,乾隆年间姜恭寿《扬州慢·和月三题西田弟天寒翠袖图》,范捷《扬州慢·题姜在经天寒翠袖图》,嘉庆年间乐钧《玉漏迟·天寒翠袖图》,三首词皆以图内容为依托,描写了佳人孤苦悲惨,竹边伶仃之景。个中,金农的一幅水墨纸本《天寒翠袖图》格外引人把稳,对《天寒翠袖图》母本的承接是创造性的,不画佳人,只保留修竹意象,有其人风骨傲气之写照。金农之后,近代绘画名家潘振镛有《竹林仕女图》,徐悲鸿有《天寒翠袖图》,但都不改母本之基本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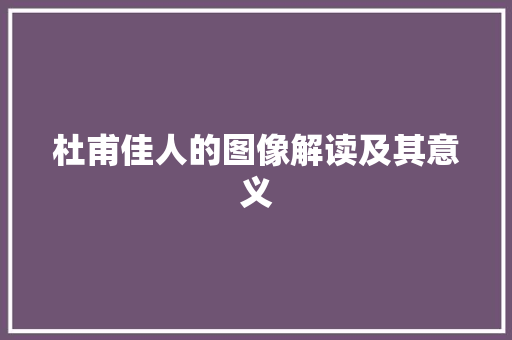
稽核“天寒翠袖”诗意图的流变,其经历了从内廷到民间,从宫廷画师到文人墨客,从命题制作到朋侪酬唱的转变。宋代画院考试中题写杜甫《佳人》诗句而一举夺魁,既是杜诗之魅力,也是画师之巧构,诗画领悟在此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后被元代字画界领袖赵孟頫所承,更强化了其在艺术权力空间中的地位。及至仇英,虽未影响宫廷艺术,但亦在民间文人话语圈层中得到一席之地,并为后世所不断演绎。有清一代,已成为文人赋词题画的主要载体。金农的另类演绎虽属文人雅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天寒翠袖”诗意图的影响。实际上,这种打破性的改造,已经完成了从继承诗意到诗意增殖再到解构诗意的过程,这也是绘画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自我化表达。至此,原来颇受文学批评界所轻视之“天寒翠袖”诗意图,以其传播范围之广泛、传承主体之有名、递变韶光之久远而逆转了其于诗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打破了诗歌的限定,完成了自我建构,奠定了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故意味的是,后世对杜甫《佳人》诗意再阐释中,除了较为常见的诗文评外,少有基于《佳人》的文学再创作,绘画作品反倒是延绵不断。从文学本位的态度看,诸如《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只管在意义还原层面未对杜甫诗有所加持,但其却成为《佳人》传播路径中不得忽略的一环。而不少环绕画作的评论乃至辩论,无论对画是褒是贬,都从客不雅观上匆匆成了对杜诗的更多关注。比如清代周中孚就批评袁文:“愚谓画工盖本少陵《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谓佳人,乃妇人也,非不知古诗而误作者。袁氏谬相讥评,亦当令画工失落笑。”于是,“天寒翠袖”诗意图不断被摹写从而形成典范的同时,杜甫《佳人》也随之逐步经典化,而没有首位题写“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画师,也无法造诣画作地位。二者的互动,正是古代艺术发生发展过程中诗画互斥又相融的绝佳范例,也正是如此,才形成古代艺术文明丰富又饶有意见意义的生态景不雅观。
杜甫《佳人》的图像传播映射着诗、画间的强弱势关系转换,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画师题“天寒翠袖”诗句始,已有借“诗”之“势”的意图,至于后来摒弃“佳人”形象,只写“翠竹”物象,仍未分开诗的框架。画家能表现诗之旨义并不随意马虎,佚名宋画虽另辟路子挖掘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主旨,却未能关注到诗句中一真切动作“倚”以及其与“修竹”的位置关系。
(作者:戴一菲,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