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是八句,以是起承转合可以分别由首联、颔联、颈联、尾联来完成,可以娓娓道来,做到从容不迫。个中的波澜不须要太大,精彩之处一样平常表示在中间两联上,大开大阖,紧张以铺陈为主。比如温庭筠的《苏武庙》“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比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比如杜甫的《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都是如此。这些铺陈,不一定都以气势取胜,但却以气韵取胜。出句和对句之间的开合、跳荡,或绵绵荡荡,或触目惊心。而绝句是不须要,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绝句则不然,绝句的章法千变万化,但主线是不可短缺的,起承转合也是不可短缺的。因其只有四句,故而这个过程只能由四句分别来完成,其构培养必须显得特殊紧凑,而字数少,腾挪的空间小,常常使人或失落之于光滑油滑,或空洞无物,或陈词谰言,或肤浅而不深刻,或庸俗而没有内涵……凡此各类,每每都是绝句之弊,难以战胜。这就哀求我们思维更加严密,手腕特殊老道,遣词造句尤其精髓精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
那么,如何“起、承、转、结”呢?古人履历,“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革,功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绝句的篇幅短小,开端一样平常不能迂回曲折,或随意铺排,而应直入本题,从靠近诗的主旨着笔,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怀,平平道来,从容承接。“转”不仅是一样平常意义的迁移转变,在绝句里,由人的活动到景物状况,由景物状况到人物行动或思想活动,由别人行动到自己行动、见闻,由过去的人事到如今的情景,由现在的情景想象到将来的情景,由面前情景到产生的抱负,由阐述自己的爱憎到解释爱憎的缘故原由等等,都可以是转,转常日在第三句,但也有分外的情形。
一样平常说来,绝句的写作,后两句比前两句更主要,第三句尤为主要,“七绝(五绝略同)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示,则神韵自出。”第三句是转舵处,舵转好了,方向对了,船便顺流而下,胜利地到达终点。“转”要在前两句的根本上转出新路,拓出新意、深意,常日是转的弯子较大,角度越新,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人猜想之中,诗就越能动人。第三句的转,为了起拉出、铺垫、反激、强调等浸染,古人常常用下列词:不、莫、独、更、如、若、何、谁、纵、欲、愿、今、至今、昔、遥知、早知、须知、谁知等等,大家可以从前人诗歌中找到很多用上述词做转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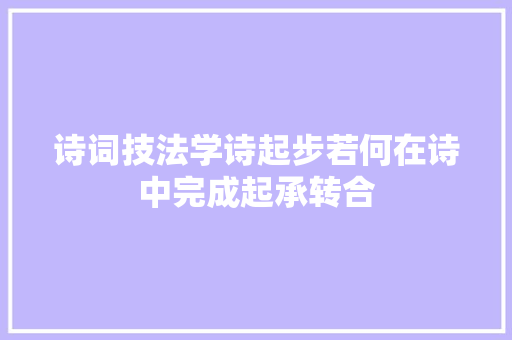
第四句的结,每每是诗歌最精彩处,是作者画龙点睛之笔,结句一好,全诗尽活,顿然生辉,结句应如撞钟,余韵袅袅,绕梁不绝,要做到“语绝而意不绝”、“言已尽而意无穷”,它紧密的承接第三句,又或隐或现的照料前两句。绝句的结一样平常有三种情形,其一以理结,而纯粹以理结的每每不易动人,以是多数是伴随抒怀、议论,寓理于事;其二因此情结,由景及情,或是情的深化;其三因此景结,情寓景中,则神韵自出。绝句写作,贵语浅情深;意不深则薄,语不浅则晦。元人杨载说:“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清人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面远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
绝句的精彩之处,更多的表示在整体的构思上。起承转合之间,短短的四句话,要交代完全作者的写作内容、目的、意义。由于文体小,不可能写的那么详细,但也必须交代明白,这就须要很深的驾御措辞的能力和奥妙的构思。绝句必须在精妙构思的根本之上,给人留下足够的回味。想写的内容当然是须要写出来的,但要在很短的笔墨上精心设计安排,取材、剪裁颇费脑筋。写细了,会摧残浪费蹂躏笔墨。写粗了,又可能交代不清。因此,必须捉住最精彩的一点展开。绝句之绝,就要表示在墨客的思力上。没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构思,是不可能出经典之作的。
绝句的章法固然也有很多的方法,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平起、顺承、跳转、妙合。
平起,便是开始的时候只管即便心情沉着,不要一下笔就风起云涌。那样每每会后继乏力。只要捉住问题的症结,轻轻地开了头就可以了。
顺承,和律诗一样,便是只管即便承接的自然,缓缓地把感情向上推。
跳转,便是要只管即便使迁移转变之笔荡开,造就波澜。
妙合,好比抖包袱。尾句一出,中央亮明了,使人面前一亮,然后拍桌赞叹。
我们以杜牧的《赤壁》为例来解释一下。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我们知道,赤壁是个古沙场。自古写这个题材的很多,但我以为杜牧的这一首与浩瀚的同题材作品不同,有着极其经典奥妙的构思。起句交代作品所描写事宜的起因,是由于捡到一块废铁,这是一块埋藏于沙土下面的折断了的戟,是一种武器。承接句进一步交代说,自己回家去洗濯打磨,认出是古时留下的。至于是什么时候的东西,作者没有讲。但由于题目里交代了“赤壁”二字,我们知道是三国期间的。这样,就顺便扣上了赤壁古沙场这样的题。第三句迁移转变,便是范例的跳转,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假设,如果东风不帮助周郎的话(会怎么样呢)?尾句合的甚为故意思,作者不说战役的结局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避重就轻地说二乔的命运。关于赤壁之战的各类说法,我们不用在这里详加陈述,二乔的结局在这里代指了战役的结局,这是诗这种文体所特有的方法。这里不仅有象征,而且有假设。全诗的技巧也紧张表示在这里。
须要把稳的是这里的跳转。东风句的涌现,在我们初读此诗的时候,你会以为很溘然。我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东风与废戟的关系,彷佛八竿子也打不着。而当我们读完末了一句的时候,才明白它的妙用。这便是迁移转变的妙处,这便是波澜。从捡拾废戟而磨洗,因磨洗而认前朝,进而想到东风,于是假设,末了妙结,这之间包含了作者的奥妙构思,令人叹服。
读者可能会问,写这样大的题材,当然可以做到波澜壮阔。如果是小的题材呢?实在,诗的技巧就在于作者的构思上,是墨客思力的表示。小的题材一样可以尽起波澜,关键在于作者如何把握。比如杜牧的绝句《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起句紧扣题目,由于是过华清宫,因而从长安入手便是很平的起笔,一点也不溘然。回望的,是绣成堆,风景幽美。
山顶千门次第开。纳入墨客眼帘的,不仅仅是风景,还是山顶的一道道的门,它们依次打开。当然,这不是真的看见,而是一种想象。杜牧过华清宫旧址,过去的事情早已经成为历史。作为咏史篇,这里的事情是透过历史的印记而想象出来的。这里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也不乏夸年夜的妙用。比如千门就肯定不是真的有一千座门,而是一种夸年夜。但这个夸年夜不是全篇的技巧,而是修辞。由于它只对这一句起浸染。
一骑尘凡妃子笑,迁移转变的也很新奇。回望、千门开、妃子笑,这三者之间实在是没有什么联系。但结尾一出,联系就出来了。
无人知是荔枝来。原来是在说荔枝。这依次打开的千门,那么秩序井然,是为了把通报情报的千里驿站变为运送荔枝的特快专递。理解荔枝以及这段历史的人,就知道这个中的厉害关系了。尤其是那个“笑”字,使我们不得不想起“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故事。两个妃子的“笑”虽然详细缘故原由不同,却又有着极其相似的一壁。这里的讽刺意义是巨大的,这也表示了诗的艺术力量。
来源:诗画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