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写到胡适讽刺毛泽东的《沁园春》,很多同学在评论区留言:胡适懂什么诗?他的文学水平究竟有多高?
胡适是中国当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牛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揭橥《文学改良刍议》,主见用口语文代替文言文,振聋发聩。与此同时,《新青年》上刊登了胡适八首“平白易读”的口语诗,这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口语诗。节选两首。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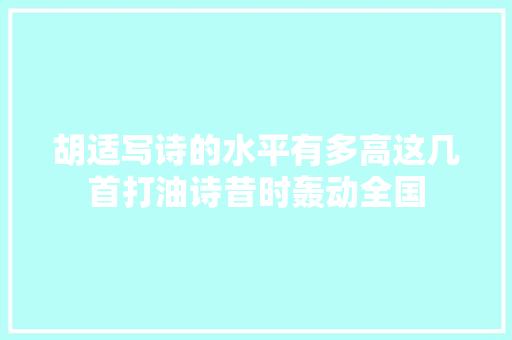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风在吹》:
风在吹,雪在飞,
老鸦冒着风雪归。
飞不前,也要飞,
饿坏孩儿娘的罪。
这两首口语诗,以本日的眼力看太过浅近,不是妥妥的打油诗吗?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属于中国当代口语诗的开山之作,意义非凡,一时引起全国轰动。在当代文学史上,《蝴蝶》被称为中国第一首新诗,胡适也被称为百年新诗第一人。
胡适有名度最高的一首诗,是创造于1920年的《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日到,移花供在家,明年东风回,祝汝满盆花。
后来,这首诗被台湾的陈贤德和张弼修正并配曲,改名为《兰花草》,一度作为“台湾校园歌曲”在内地广为传唱。这首小诗,清新朴实,琅琅上口,最最少比赵丽华的“梨花体”、贾浅浅的“尿尿体”好得太多。
什么是诗?首先,诗要朴拙。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天真。”也便是说,内容和情绪要真实,不玩虚的。其次,诗要美。比如声韵之美、节奏之美、意境之美,分开了这些艺术形式,不能叫诗。
胡适的口语诗,这两点都能大致做到,不过,限于天赋和格局,他确实没有一首传世的精良作品。
当年,胡适提倡口语文,引起了一个国学大师黄侃的反感,流传下来几个有趣的故事。
黄侃与胡适同在北大当教授,此君学问大,脾气也大,每次上课前都要先骂一通胡适,才正式讲课。有次,他在上课时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胡适的太太去世了,他的家人拍电报:‘你的太太去世了!
赶紧回来啊!
’长达11字,而文言文则仅需四个字:‘妻丧速归’,可以省一大半电报费。”同学们哄堂大笑。
黄侃像
胡适听说这件事后,也在教室上做了反击。他对学生说,行政院有位朋友约请他去做行政院秘书,他不愿从政,让大家代他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学生们纷纭拟稿,胡适选出了一则最简练的电报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然后笑着说:“实在,用口语文只须五个字“干不了,感激。”同学们拍手叫绝。
为了遍及口语文,胡适还写过一首妙趣横生的打油诗:“笔墨没有雅俗,却有去世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纭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上吊,今人吊颈;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胡适是一个思想启蒙式的人物,文学确实非其强项,一代学术大师钱穆曾评价:“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至少不是纯洁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