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阐明方法是措辞笔墨阐明方法在法律范畴上的详细运用,与其他领域的阐明方法有相通之处。正如有学者所言,亚当夏娃的二人间界不须要措辞,更不须要笔墨。措辞、笔墨自其产生那天就产生了须要如何阐明的问题,进而会因阐明产生问题,故而又引发了许多让人痛楚、让人欢快的故事。“郢书燕说”确实可能是个俏丽的缺点;夏娃有时候肯定会认为,亚当的“阐明便是掩饰笼罩,掩饰笼罩便是事实”。“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我之以是产生要批评该剧的想法,最主要的缘故原由,是我在之前已经读了原著。
剧中,反派对贺知章名篇《咏柳》所作的阐明,可谓神来之笔,我之前还真没想过这首诗还可以如此阐明,这一伏笔,也将引出正反两派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将表示在两派对唐律的阐明方法上。《长安十二时辰》第十八集一开始,李必骑马行走在街上,小孩正在吟诵安在朝(贺知章)的名篇《咏柳》。李必在贺府问安在朝:“老师的咏新柳,为何要用裁、剪刀这样锐利之词?”安在朝说:“你也听出来了,哼哼,大家都听出来了,贤人以为,我是为太子作的,对贤人不满的讨伐檄文,说此诗是在责备贤人裁剪太子同党。但太子愈挫愈勇,反而追随者众,其势已成高树大才。”李必回答道:“老师诗文并无此意,是有些人恶意解读,贤人偏爱老师才华,一定是不信的。”
《咏柳》中能否读出影射贤人的意思?如果按照同时期的文学理论来阐明,确实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玉树”在很多诗歌中,确可以指代宫中瑰宝,如陈后主名篇《玉树后庭花》中的“玉树”便是此意。玉,又可以引申为“国之重器、朝廷大宝”,喻指太子、皇子,也未尝不可。《康熙王朝》中,收复金厦之战大败,明珠差人给萨木尔送了一柄玉快意,啥也不说,萨木尔一想,就深知个中含义,立时写折子为大阿哥顶罪。“东风”在同时期的多首诗中,都被认为是在喻指“君王”。如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东风拂槛露华浓”,诗中的“东风”就公认是在暗喻君王的恩典膏泽,使花容人面倍见精神;王之涣《凉州词》中的“东风不度玉门关”,明代杨慎就认为该句含有讽刺之意,其在所著《升庵诗话》中言:“此诗言恩典膏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王之涣写玉门关那里没有东风,是借自然来暗喻安居于繁华帝都的最高统治者不体恤民情,置远出玉门关防守边疆的士兵于不顾;白居易《杨柳枝词》中的“一树东风千万枝”与“永丰西角荒园里”相对应,诗中的“东风”也被公认是在喻指君王恩典膏泽。
“人生识字忧患始”,笔者认为,正是为了减少这种措辞、笔墨肆意阐明带来的问题(或为垄断对措辞、笔墨的阐明),人类逐渐对阐明的方法进行了规范,制订出多少的笔墨阐明规则。一样平常认为,近代西方阐明学,始于对《圣经》的阐明,后来逐渐发展出文学、法律等领域的阐明方法。西方对措辞、笔墨阐明的方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三种基本不雅观点。一种是文本主义阐明方法,一种是原旨主义阐明方法,进而自然还会产生第三种折衷主义阐明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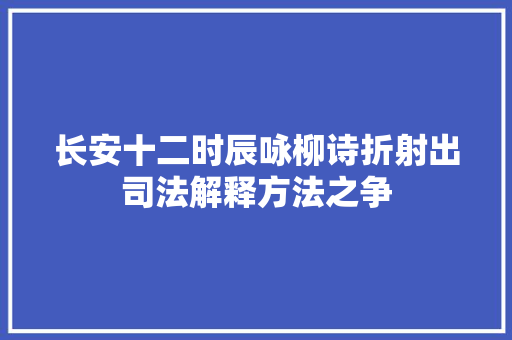
文本主义阐明方法认为,“含义彷佛便是这么可以从笔墨中冒出来的, 触动了我们的心智。我们很随意马虎得出结论,意义是笔墨中所包含的;只要负责阅读,作者注入笔墨的含义就会在我们的心目中再现出来。”因此,文本主义阐明被当做解读文本的基本方法,并成为阐明方法的首选。依照文本主义的阐明方法,当然会产生好多问题,比如常见的法律适用中关于知假买假是不是“消费者”的争议。
为办理文本主义阐明方法所带来的问题,产生了“探求立法者或准立法者于制订法律时所作的代价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的原旨主义阐明方法。但是,也正如西方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以是为,一部作品产生后便是独立的文本,和作者无关。一部法律产生之后,又如何探究立法者的意图,并使法律的阐明为立法者所掌握,这是一个天下级的难题。拿破仑制订《法国民法典》,意图禁止对法典进行任何形式的阐明,不给法官留下阐明法律的空间,讯断成了“法律严格的复印”,法官不能有任何自己的判断和裁量,只能做“发布法律措辞的哑巴”。但是,《法国民法典》问世不久便有人作出注释,拿破仑闻之抛书叹日“嗟乎,朕之法典已废矣”。
与西方法律阐明方法及流派相对应,我国古代也产生了类似的阐明方法及流派。笔者斗胆认为,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措辞、笔墨阐明方法,起源于对龟甲蓍草占卜的阐明。《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武王想吊民伐罪,占卜出来的兆却是不吉的,足见,对灼龟占卜中裂纹走向所预示休咎的解读,是有约定俗成的可以遵照的阐明方法的,按照这个阐明方法,确实是“不吉”,因此,“群公尽惧”。姜太公一时没有想出改变阐明结论的成体系的崭新的阐明方法,因此,才会推蓍蹈龟曰“枯骨去世草,何知而凶?”,太公彊之劝武王曰:“当为则为,当不为则不为,何祈于一方朽物”?武王於是遂行。春秋战国之后,在对《礼记》、《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注释中,我国逐渐形成了流派甚多的经学家,终极形成了心学、理学两大流派,个人鄙见,这些派别辩论的出发点,也是基于对文本的不同阐明方法。
回归本剧,正反两派对《唐律疏议》的阐明争议,除了夺权、三司会审等戏外,集中表示在依照《唐律疏议》对张小敬能否免去世的问题上。张小敬犯了不义之罪,属常赦不免之罪(亲王在这点上有重大技能疏漏,依照《唐律疏议》规定,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及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才构成不义,剧中张小敬只杀了个从八品的万年县县尉,自然不构成不义,如果该当安排张小敬杀万年县县令,县尉是他铁哥们,在审讯中一贯护着他,他才没去世在牢中,并被石友徐宾救出,这样的故事才圆满)。
张小敬能否通过救长安来立功赎罪,反派们依照严格的文本阐明主义,给他的答案是“不可能”,由于按照《唐律疏议》,虽然“八议”里有“议功”的规定,能斩将搴旗,摧锋万里,或率众归化,宁济一时,匡救困难,铭功太常者,若犯去世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定宸衷,曹司不敢与专。张小敬如能拯救长安,确属立大功,但是,张小敬是已经议定的去世囚,等待秋后问斩,纵然犯罪后再立功,依照《唐律疏议》“八议”的规定,并不能减轻或免除惩罚。
端正(也包括骑墙派代表元载)自然也知道依照《唐律疏议》“八议”的规定,并不能减轻或免除张小敬已经剖断的刑事惩罚,但是,他们基于原旨主义的阐明方法,认为张小敬如能在十二时辰里拯救长安,自然属于“毫不服从、不忘初心”的典范,当然可以比照“八议”,奏请贤人予以特赦,故而给出了张小敬能免去世的答案,当然,只是“可能”,并不是“一定”。他们所依据的是《唐律疏议》中特赦的规定:如有特奉鸿恩,总蒙原放,非常之断,人主专之,爵命并合如初,不同赦、降之限。其有会虑減罪,计与会降不殊,当免之科,须同降法;虑若全免,还从特放之例。当然,特赦之所以是特赦,自然因其极为稀缺。贤人乾纲独断,臣下自然不敢妄测圣意。值得把稳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虽无特赦的条款,但也有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条款,但是,由于案多人少等缘故原由的存在,很多刑事案件,并未启动这一近乎被遗忘的制度,直至许霆案发生,才让"大众年夜众知晓这一制度。
法律阐明的方法论,本身难以分出利害,也正如苏力老师所言,“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只管作出了各类努力,以求创造一种理解、阐明法律的方法,然而我看不出在通过法律阐明而得到更确定的法律这个问题上人类有多少进步;如果有进步,那也只是人们描述自己理解、阐明法律的过程上的进步(而这只是一种利用笔墨上的进步),以及人们对这些过程的在某种程度上的自觉”。
跳出阐明方法本身,从权力分配机制上看,能否阐明法律,以及持何种阐明主义,确实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笔者自揣能力有限,不再就此展开。单从剧中看,文本主义阐明方法信奉者林九郎的政治空想,是想和贤人一起,构建一个“贤人垂拱,以法治天下”的新大唐,“君,以相为盾,以守为攻,无为而治。至此,无对无错,无功无过,无善无恶”,当然也就包含要杜绝贤人以立法者的面孔涌现,用特赦来改变他主修的《唐律疏议》的政治局势,让我唐直接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而太子一党则认为,右相代政属反宾为主,“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天下大柄,不可假人”。以此看来,太子党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执拗派。当然,关于右相代政一事,在《资治通鉴》中并无右相如何表态的记载,亲王在这里属于脑补历史,按照文本主义阐明方法,不属“历史虚无主义”,不属架空历史的违规之举。本剧和本文都权作一时谈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