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寒
小寒,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俗话说“小寒胜大寒”,按节气来讲,“三九寒冬”正是在小寒时节。
“小寒日,数九寒冬至此盛。苍松翠柏迎霜雪。”“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平凡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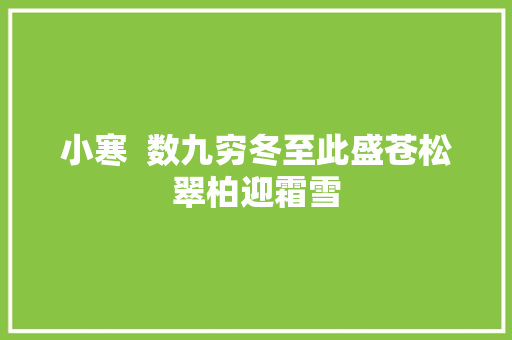
岁寒三友松、竹、梅。松柏以其苍翠,在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日子歌唱着生命的华章。江南苏州邓 尉的四棵汉柏清、奇、古、怪,像是每年与我相会的老树仙,用它们的年轮丈量我一年里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的微小。而大理山林中的松,挺立俊秀, 千姿百态,直揽云霄,以枝干与针叶书写中国文民气中高洁、坚毅、刚毅刚烈的君子之风。
大 理 的 松
殷若衿
在大理拜访竹庵老师夫妻,叨扰了数日,我逐渐理解他们为什么钟情于大理,选择在大理隐居——这里不但山水开阔,亦是一座丰硕的花木宝藏。
与竹庵老师夫妻驱车去往沙溪的路上,最令我目光胶着的,还是山间的松,像极了宋画、元画里的松,挺立俊秀,千姿百态——董源画里的,郭熙画里的,赵孟画里的,倪瓒画里的,都可以寻摸到姿态与神韵有几分相似的松影。
大理的松 绘者:殷若衿
这天与竹庵老师夫妻同游大理沙溪石钟山石窟。走在山间石板古道上,劈面见到一棵横向成长的松树,好似游蛇蛟龙,横陈在我们面前,末梢探头望向天空,引得大家连连称奇,纷纭与奇松合影,或倚或立,不亦乐乎。
沿着石阶下到深谷,一起草木清丽,松石可人,劈面山峦叠翠如画屏。路上我和竹庵老师、文一老师聊起中国人面对自然山水和西方人态度的迥异。西方人彷佛把人与自然分隔、对立看待,攀岩越野,彷佛把自然中的险要山水作为一个被人类征服的工具。而中国人则崇尚天人合一,把自然山水纳入人文天下中,在山水中修造亭台楼阁,题壁凿刻,将建筑、文学、雕刻、书法、儒释道哲学等领悟为一体。题壁雕刻的笔墨,每过一些岁月,便被苔藓地衣覆盖淹没,后人又根据史料记载跋涉山间,探求发掘当年的题壁刻字,再拓印下来。竹庵老师与文一老师说,乾嘉年间有许多人在做这样的事。中国文脉的草蛇灰线,就这样在山水中延绵下来。
对待花草树木也一样,中国人险些不会把花草树木作为没有生命的装饰品,而是作为有情物、作为心腹去看待。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由植物而“兴”的诗篇。宋代以降,人们更授予花草树木人格化的美好品性,可以来不雅观照自己的内心。梅、兰、竹、菊,各有风致,而松柏,向来在中国文民气中被视为君子,有着高洁、坚毅、刚毅刚烈、孤直的秉性和品质。荀子有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李白曾说:“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青松或生于深谷,或生于绝壁,直上云霄揽风尘,多少年来,不知入了多少文人的诗、文人的画,被文人墨客用来抒发个人的精神境界。
我们参不雅观过南诏国石窟,走上山脊,一起又是好松相伴,有的挺直,有的虬曲,有的如孤鹤伫立,有的如鸾凤相伴。纵然生活在相同的自然环境里,每一棵树看上去仪态与性情都那么不同,让人很想拿起画笔,就地坐下来临摹一番这千姿百态的松。
竹庵老师说,松树沉默而虔诚地记录了发展过程中的境遇:阳光、水分、土壤的养分,和自然无常的侵袭如虫嗑、风摧、雷击、鸟兽的侵蚀……进而终极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形态。遇见它们,我只想虔诚虔诚地去记录去描摹,没有一点想要人为造作去重塑的想法。
师自然,师造化。自然,是最难呈现的状态。我想这也是中国人对待自然始终保持着敬畏心的缘故原由之一。
[松针茶]
到野外采集三米高以上松树的松针,用软布蘸可去油腻的洗涤剂,包起松针仔细洗濯。将洗净的松针切(剪)成三段,放入热水瓶里,突入开水,焖泡半小时即可饮用。
文章选摘自殷若衿新书《草木有情》
冬至|孔子后裔与红豆杉
霜降 | 深秋已至,醉白池赏菊
秋风起,满陇桂雨 | 秋分
请准备好一本消夏的书:草木有情,人间清欢